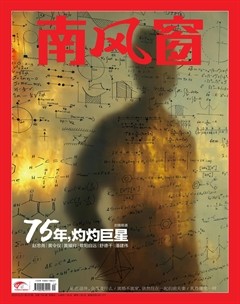西方人对当代社会的感受似乎已经被一种绝望情绪主控:资本主义不仅是西方唯一可行的政治经济系统,如今就连给它想象一个合乎逻辑的替代选择也不可能了。
然而2020年以来,当代西方左翼思想家们看到了不同的迹象。他们一方面主张在数字革命之后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倒退,一方面将这种倒退解释为资本主义被取代或者消亡的一种可能,由此形成了技术封建主义思潮。
法国经济学家塞德里克·迪朗2020年的论著《技术封建主义》今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借助这本书,我们会看到当代西方左翼思想家正在如何想象资本主义的终结。
本书开头讲述了一个发生在1990年的插曲:美国特勤局持搜查令闯进一家位于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的小公司,查获了一份名为《赛博朋克》的手稿。手稿的作者、游戏设计师洛伊德·布兰肯希普,设想了一个反乌托邦的游戏世界,在那里,富可敌国的巨型企业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力量,就像封建领主一样,对其控制下的空间和居住其中的个体行使权力。
迪朗发现,当代社会图景与这个游戏设定有某种相似:数字技术和智能算法不仅带来了生活的深刻变革,更创造出新的统治形式和管理制度,造成社会“巨大的倒退”。迪朗认为,这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再封建化”。例如,硅谷的科技新贵就像中世纪的封建领主一样,通过垄断数字资源,向平民(用户)收取租金,从而捕获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大多数利润;需要为公共资源支付租金的平民,则被置于类似农奴的地位。
公共空间的消失
迪朗发现,2000年之前,名列前茅的公司多是石化、零售和金融集团,20年之后,无论是榜单上的名字还是人们对“大公司”的想象,都被高科技公司替换了。苹果、微软、亚马逊、谷歌、脸书……这些科技公司只用了极短的时间就从“硅谷新贵”成为当下经济秩序的主导者。
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
数字革命之后,技术产权和用户数据作为无形资产,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生产的最重要要素。然而由于掌握产权和数据的人是社会中的极少数,科技不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一般智力”,而是经过科技巨头的垄断,成为具有稀缺性的技术特权。这种稀缺性让产权的出租成为可能。
对于“手机成瘾症”,技术封建主义提供了崭新视角:那不是成瘾,而是一种新的奴役手段。
科技公司的获利方式,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的逻辑,而与封建主义有相似之处:科技寡头通过数字圈地抢占网络空间,将我们的日常生活引入数字平台,攫取用户数据,再向用户收取租金,就像封建主对农奴做的那样。
数字科技的发展,让无形资产更深地嵌入我们的社会生活和经济体制。数字平台、软件服务已经呈现出“基础设施化”的趋势,很多打工人可能一时半会没法想象这个场景:假如现在微软公司从地球上彻底消失,你要用什么给客户讲解PPT——PowerPoint。首先,你要怎么解释这是一种什么东西?
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遭到了“数字殖民”。工作依赖于办公系统,出行依赖于优步/滴滴,用餐依赖于外卖软件,从地铁口出来到公司那一小段距离,则依赖于共享单车软件。至于那些尚未被数字化的需求,就成了互联网初创企业津津乐道的“风口”。
以社交媒体为例,这个经过数字转化后的公共空间并不是免费的。如果我们想进入一个广泛的平等的交流空间,我们需要向一个特定的人(或者组织)缴纳入场费。在外卖平台、通信软件、社交媒体上缴纳租金的农奴,换取的是在技术的许诺诞生之前,原本无门槛属于我们的生活空间。
在越来越多的便利店、餐馆,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图景:店员的职责不再是满足我们的需求,而是教会我们如何使用点菜机和自动收银机——那些显然正在试图替代他们的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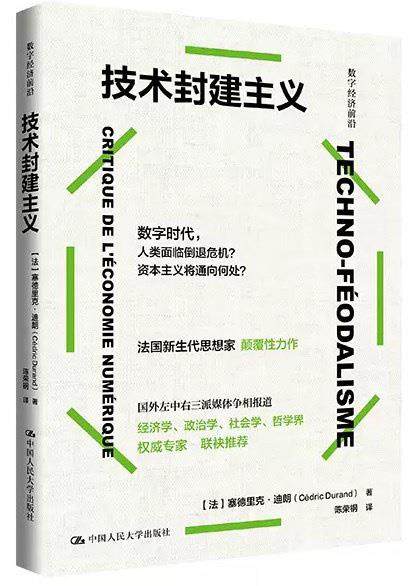
齐泽克认为,“这就把我们这些用户置于向作为封建主的公共资源所有者支付租金的农奴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