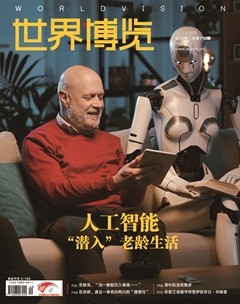人类学家在研究文化现象时,对于儿童的世界总是谨慎又谨慎。其一,作为有良知的田野工作者,在面对未成年研究对象时,很难推测他们的回答和反应是否受到自己或陪同的大人的影响和压力;其二,儿童很容易混淆自身与世界,不一定能感知到自身之外的世界和正在自己看不见的地方发生的没有自己参与的事情。或者说,儿童很多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自己创造和感受到的世界并不完整。同时,在研究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的时候,儿童往往被认为并不是非常关键的参与者。结果就是,虽然以儿童世界作为观察对象的人类学研究并不少,但研究者总是感觉只有相关的同行会关心自己的成果。但有些例外出现在语言人类学和符号人类学界,特别是在近年来对拟生世界(animation,这里的含义是用非生命物体通过表演模拟生命世界)的研究中,人类学家们渐渐对儿童文化有了更多的关注。
其实,人类学家们在反思结构主义叙事的时候,也希望跳出所谓“客观理性的世界”这种认知,看到人们在实践看似清晰的结构和规律时自发的、富有创造力的行动,如何改变了这些结构本身,如何改变了建筑在这些结构之上的社会,又如何改变了自身。笔者的好友、语言人类学家梅根·巴克(Meghanne Barker)在她持续多年的哈萨克斯坦木偶剧院和孤儿院研究中,就勇敢地挑战了关于儿童文化的人类学研究。
她在哈萨克斯坦的田野调查从2011年进行到2018年,在孤儿院进行了多年参与式观察,与孩子们成了好朋友,却又不去窥探他们在各自人生中的选择。她听他们讲了很多很多故事,却从不对他们讲故事。她观看他们的演出和游戏,饱含热情与理解,却从不让他们看到自己的眼泪和深情。多年来,她与本地人一起观看木偶剧院的演出,看到为儿童做的表演怎样超然于政治叙事之外,塑造了一个亲密与充满爱意的空间。在总结自己的研究时她写道:儿童的文化应该作为公共文化被看到,而不是作为私密的世界被隐藏。
“即兴”表演的孩子们
把梅根研究的木偶剧院和孤儿院联系起来的,是契诃夫写的一个小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