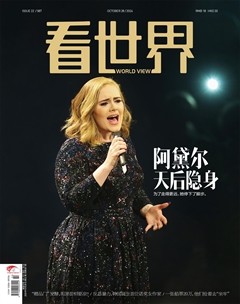“好委屈啊。”
一位生命行至晚年的女性回忆起自己大半生的婚姻生活,作此感慨。这名女性的名字叫张赞英,生平年龄不详,籍贯家庭不详。她是知名植物画家曾孝濂的妻子。
新一期《十三邀》节目里,许知远采访曾孝濂,顺带采访了张赞英。与大画家在采访里阔论的植物生命哲学与人文艺术不同,张赞英所言,尽是世俗的委屈和怨气:与曾孝濂结婚后,为了丈夫的事业,她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梦想与事业。几十年来,张赞英替丈夫操持一切,负担下家里的大小事务,牺牲奉献了一辈子。如果还有下辈子,她只想走自己的路。
在依附着名人丈夫顺带的采访里,张赞英终于有机会说出自己的心声。没有一个知名媒体人和作家,会去采访一个不知名的女性。采访张赞英,以及几个月前另一期《十三邀》采访许倬云的妻子曼丽,都是“大师”的顺带。
古今中外,不少“大师”“名家”甚至是伟人背后,都站着一个沉默的妻子。为大作家托尔斯泰默默付出和忍受一生的妻子索尼娅在自己的日记里哀叹:“生活在世上真是艰难、痛苦。长久的斗争,紧张地处理家里家外的事务,教育子女,出版书籍,管理属于子女的产业,照顾丈夫,维持家庭平衡,所有这些事情都使我疲惫不堪。”
这些“非凡”背后的女性,处于凝视焦点之外,人们掷向她们的眼光,和她们的丈夫看待她们的方式一样,多的是感谢和感动。可这两种情感,都只承认了她们在婚姻内的价值,而非对个人价值本身的肯定。生命已至晚年,当她们回望婚姻,也许漫长一生也感受过幸福,但唯独不能否认对自己的歉疚。
若重来一次,重要的不是她们是否还会选择婚姻,更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无论选择哪条路,都可能留下后悔?
接过脏纸巾的人
曾孝濂,1939年出生于云南威信,中国知名植物科学家、《中国植物志》插图作者,已发表插画2000余幅,被誉为“中国植物画第一人”。
在无数媒体采访与名人对他的评价里,最常见到的表述,是类似“一生只做一件事”“从一而终”“为生命立传”等赞誉。光环背后,可能是经年累月的韧性、艰苦与意志力,也可能还有一个沉默的女人。
“文革”时期,张赞英插队到云南,在中国科学院云南植物所认识了曾孝濂。70年代中后期,张赞英争取到一个机会,到北京林业大学去念书。然而,四年学习过后,由于家庭缘故,她最终还是咬牙决定回到昆明,回到丈夫和孩子身边。
往后几十年,为了成全丈夫曾孝濂在植物所的工作,张赞英几乎完全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和抱负。她自觉承担起所有家务和照护工作,独自处理生活里一件件大大小小的危机与琐事。
晚年,曾孝濂当然也意识到妻子为自己这一生作出的奉献与牺牲,他觉得自己“实在幸运”,会口头上对妻子说“我就是靠你了”。
记者回忆了采访时的更多细节:“曾孝濂的夫人张赞英始终以一种极为沉静和耐心的态度在照护曾孝濂:一天三次提醒他下楼吃饭,给他剥橘子、倒水、泡咖啡,转达外界发来的每一封邮件和每一条信息。曾孝濂也早已习惯这种全方位的照护,从食堂走出来,自己忘了扔掉的纸巾也会递给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