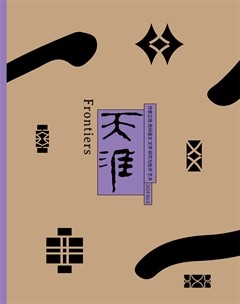一
2022年,一本名为《谈心:与林青霞一起走过的十八年》的书,在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同时出版,作者金圣华,写她和大明星林青霞的友谊,以及彼此间关于阅读、写作、生活的心得体会。坊间肯定更熟悉明星,但在翻译领域,金圣华是学术界的名教授,远非“明星”可比。金圣华是法国巴黎索邦大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的翻译系教授、荣誉院士及翻译学荣休讲座教授,另一社会职务是香港翻译学会荣休会长、荣誉会士。金圣华曾两度担任香港翻译学会的会长,为推动香港翻译工作做出了贡献。
按传统说部习惯,谈金圣华教授,算是“楔子”,为了引出香港翻译学会。2021年是香港翻译学会成立五十周年,因为疫情,学会举办了多场线上的系列讲座,在东亚地区颇具影响。五十年间,香港翻译学会一直活跃在香港文化领域,促进与翻译、语言和跨文化的交流。
倒退五十年,时维1971年10月6日,香港翻译学会成立,这是香港唯一的翻译学者和翻译专业人士组织,定期出版会刊《译讯》及学术期刊《翻译季刊》,出版翻译论文集及专著共十余种,设立了两个翻译奖学金。
查阅文献,关于香港翻译学会的历史,有这样一段描述:“1971年10月6日,‘香港翻译学会有限公司’在香港正式注册成立。七个月前,七位会员Louis Cha,T. C. Lai,Meng Ma,Stephen C. Soong,Alex H-H Sun,Philip S. Y. Sun和Siu-Kit Wong作为发起人,召开成立大会,旨在香港成立一个非营利的学术团体,以促进与中文翻译有关的标准、交流、出版和研究。这些发起人,包括六位杰出学者和一位著名武侠小说作家兼报纸出版家,他们秉持的坚定信念,铭刻于学会章程中。”
熟悉金庸生平的人,会立刻反应过来,Louis Cha,正是金庸的英文名字,其他六位,分别为:赖恬昌、马蒙、宋淇、孙鸿辉、孙绍英及黄兆杰,皆为香港地区著名的学者和翻译家。
香港传播学奠基人余也鲁,亦是翻译家、出版家,洵为香江学林翘楚,曾出版《余也鲁日记:夜记香港百天》一书,其阅历既丰,交游又广,在日记里写了不少香江学界的掌故,特别提到香港翻译学会成立,并言学会之发起宣言,即由金庸起草。岁月嬗递,文字难觅,不知昔日金庸怎样说明香港翻译学会的成立缘由,或许上面这段文字有可能就来自于金庸最初起草的宣言。对于七位发起人所秉持的信念,他们这样阐释:
提高翻译水准,协助中文及其他语言的翻译培训,鼓励学者投身重要著作的汉语和其他语种翻译,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促进文化交流,并以此目的:
(一)召开学会会议;
(二)出版书籍或期刊,赞助翻译方面的研究,举办专题会议和从事符合本会宗旨的其他活动;
(三)印刷、出版、出售、出借或分发本会会刊或报告。
金庸与其他六位学者相比,似乎距离翻译这个职业有些远,但寻觅金庸的早年经历,他对翻译一直情有独钟,这是不争的事实。金庸的一生除了写有武侠小说、新闻评论,还留下了大量翻译作品,可惜湮没在武侠和新闻两大光环下。
二
1945年2月20日,已是抗日战争的后期,一份《太平洋杂志》在大后方重庆创刊出版,封面上标注由太平洋出版社发行,社址在重庆弹子石大有巷四号,印刷为警声合作社印刷部,其地址为弹子石大佛段六十一号,二者相距不远。这份杂志非常短命,仅出版一期,创刊号亦即终刊号。
《太平洋杂志》有64页,内容包括时事、学术、文艺、翻译等文章,颇为充实,很能迎合不同读者的口味。这本杂志的编辑是查良镛,发行为张凤来。
1944年,金庸二十岁,因有游历外国的想法,遂产生了当外交官的理想,就读于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中央政治学校是国民党“党立的最高学府”,其前身是中央党务学校。这年上半年,大一学期结束,金庸的学习成绩名列全校第一,但到了秋天,他却不得不离开学校。他回忆这段往事时曾对严家炎教授说:“抗战后期我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念外交系,那个学校国民党控制很严,国民党特务学生把很多人看做‘异党分子’,甚至还乱打人。我因为不满意这种状况,学校当局就勒令我退学。”
失学的金庸想到了表兄蒋复璁。蒋复璁是海宁硖石人,军事家蒋百里的侄子,1940年,任国立中央图书馆的首任馆长。通过蒋复璁的关系,金庸进了国立中央图书馆阅览组工作,名义是干事,具体工作是登记借书和还书,上班时间为每天下午两点到晚上十点。这份工作薪水不高,仅够糊口,但在管理图书的同时,给了年轻的金庸一个大量阅读的机会,他集中读了大量西方小说,包括英文原著《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今译《艾凡赫》),并英法文互参读了《侠隐记》(今译《三个火枪手》)、《基度山恩仇记》(今译《基督山伯爵》)。
图书馆的工作任务不重,颇具生意头脑的金庸,萌发了办一份杂志的念头,他后来在《太平洋杂志》创刊号的“编后记”里,谈到了创办初衷:
我们在重庆,外埠的友人常会写信来说:“希望寄一些新的刊物给我们吧!”但寄什么给他们好呢?重庆好的刊物很多,但未必正合他们的需要。学政治经济的要一些资料;学文学的想看些最新的作品;学科学的想知道世界上科学进步到了什么地步。生活太无聊的要求些刺激;生活太紧张的人要求得到解脱。我们想到,应该有一本刊物能普遍地满足这种需要。于是我们着手筹备了,希望这是一本范围极广的刊物,希望这是一本能适合大众需要的刊物。
金庸对读者市场的需求极为敏锐。1939年12月,他十五岁,因同学张凤来、马胡蓥都有弟妹要投考初中,但找不到合适的参考书,于是搜集材料给他们作为参考。在此基础上,金庸编辑了《献给投考初中者》一书,于1940年5月出版,这是他的第一本书,问世一年,印刷20次,销量10万册,带来了丰厚的报酬,直到1949年3月,南光书店还在出版《献给投考初中者》,可见此书的长销程度。金庸若干年后回忆往事,对池田大作说:“我创办《明报》而得到成功,大概就源于这种洞悉读者心理的直觉能力。”
金庸觉察到读者的需求,于是拉上张凤来等三位同学,想要办一份杂志。穷学生哪里有钱,只能四处告借,筹措经费,所得不过杯水车薪。杂志最大的支出是印刷费,金庸后来找到重庆大东书局的老板,勉强答应赊账印刷一期。
重庆当时流行美国杂志《大西洋月刊》,这是一本文学和文化评论杂志,1857年11月创刊,至今仍在出版,在美国颇具影响力。据说,当年宋美龄很喜欢这本杂志,经常翻阅。金庸蹭了这个热度,为自己这本杂志取了个相似的刊名——《太平洋杂志》。
三
一期杂志需要的内容不少,作为新刊,稿源是个问题,但是从创刊号目录上的13篇文章来看,有《齐格菲防线大战记》《意大利投降内幕》这样关注世界战事的译文,也有《飞弹之谜》《最近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科普文章,还有文学类的《少年彼得的烦恼》《安娜与星罗王》等小说、散文等,做到了普遍满足读者的需要。金庸还以笔名“查理”发表了长篇小说《如花年华》首章,占了7页,约有9000字,这或许是金庸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可惜未完。
杂志中的文章以译文为主,目录上的译者除了“查理”,还有段一象、良莹、张捷、贾鼎治、王人秋、俞淬、马玮等。这其中,贾鼎治是中国现当代翻译家,1925年出生,新中国成立后任新华通讯社国际部译审,当时年少,正在重庆。其他翻译者的名字无从可考,考虑到金庸在中央图书馆的便利条件,以及出刊的紧迫时间,推测这些翻译者大多是金庸自己,他为了让读者感觉本刊实力强大,供稿者甚众,换了不同的“马甲”,《太平洋杂志》可称金庸最早的“译文集”。金庸利用国立中央图书馆的丰富资料,每天得空就翻译,下班后,又带着《英汉词典》,赶到同处两路口地区的美军俱乐部,抢译新到的外国报刊上的文章。他以查理为笔名,在“发刊词”里宣示了办刊的宗旨——传播知识,传播真、善、美:
一本理想的综合刊物,应该能够传播广博的知识,报道正确的消息,培养人们高尚的艺术兴趣与丰富的幽默感。真理、善良、美丽,都是十分宝贵的东西,为了要获得这些,几千年来不知道有多少人尽了终生的努力,甚至牺牲了生命。我们这本杂志,就是集拢这些美丽的东西献给你。渺小的蜜蜂从各种花朵里制出蜜来,我们希望这蜜是甜的。
愿望是美好的。《太平洋杂志》虽投读者所好,首印三千册,上市不久就销售一空,这给了金庸莫大鼓舞,他积极筹备第二期,结果因纸价飞涨,印刷方不肯继续赊账,理想输给了现实,杂志就此寿终正寝。
在杂志的最后一页,还有金庸为自己打的“广告”,除了杂志,他还要雄心勃勃出版翻译丛书,起手就是两套重量书:
一是大仲马《基度山伯爵》的全译本:
本社新书预告
世界文学不朽巨著
基度山伯爵(全译本)
大仲马原作
查良镛译
大仲马最精采(原文如此)之杰作,西洋流传最广之小说。
史蒂文孙说:“此书极度迷人,没有人能看了第一章而不一口气看到末一章。”
每个西洋人都知道基度山伯爵就像中国人知道关公和贾宝玉。
书中包含了一切使人兴奋的情节:爱情、战争、决斗、阴谋、复仇、报恩、越狱、自杀、假死、发疯、复辟、退位、党争、强盗、绑票、偷窃、结婚、得宝、炫富、化装、暗杀、航海、覆舟、纵火、赛马、比枪……
(原文如此)有:全身疯瘫用眼睛说话的老人。
为了儿子而毒杀四人的美妇。
与父亲信仰相反,活埋自己儿子的法官。
拿女儿当生意经的银行家……
译文流畅,语句美丽。
本书第一册在印刷中第一册实价二百五十元
欢迎预约及批销预约八折
出书后,预约者优先寄奉批销六五折
二是英文选集:
二十世纪英文选
俞杨等选编
1.所选各篇均为二十世纪之杰作,现代人应读现代英文。
2.作家为英美第一流文豪,如萧伯纳,拉斯金,威尔斯,马克吐温,高尔斯华绥,罗素,哈代,辛克莱,贾克伦敦,巴蕾,吉卜林等。
3.每作家选一代表作,自一文可窥见一文豪之作风。
4.每篇题材各个不同,抒情,议论,描写叙述等均有。
5.每篇长短相仿,均系精短可资背诵。
6.文首附有作家小传,及该文之地位。
7.篇末详细注释生字,难句,用于自修教科均极适宜。
从这两份书籍预告来看,金庸深谙读者的心理。我们今天关于文学,总有“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分野,文学的体裁愈加固化,评论家们对文学的价值,总有一种自信,认为“纯文学”在时间面前更具优势,“通俗文学”意味着流行一时,“纯文学”则更能永恒。可若真放在时间背景下考察,这个观点颇可商榷。雨果诞生两百周年时,法国的报章上有“谁还在阅读雨果”的疑问,但我绝不会怀疑,与他同一年出生的大仲马依然会有读者群。
《基度山伯爵》的广告中,金庸使用了极为吸引人眼球的词语,也可见他已经下定决心翻译这部长篇小说。若读者不想读长篇,金庸亦很贴心,备有《二十世纪英文选》,著名作家的短篇作品,一次可以读完,还能用于背诵和学习。
金庸翻译的《基度山伯爵》计划出版多少册,无从可考,但第一册售价250元,价格不菲。当时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月薪560元,金庸的月薪仅有50元左右。抗战时期,民国政府发行的货币恶性通胀,重庆物价到抗战后期上涨了1560多倍。居住在重庆的老舍曾回忆,起初四川的东西便宜,“一角钱买十个很大的烧饼,一个铜板买一束鲜桂圆”,但从1940年起,物价几乎一天一倍的天天上涨。作家张恨水提到他初到重庆时肉价两角一斤,五年后肉价暴涨到三四十元一斤,他要同时创作七部小说,写小说的过程中还不时发表散文、杂文、评论等,以换取稿费养活一家人。
同期比较,一册《基度山伯爵》的文字量不会太少,可以推测金庸已完成了相当数量的译文,而他的生活境遇也可想而知。如果《太平洋杂志》能有后来《明报》的命运,金庸大抵第一部出版的小说就是翻译作品了,但时代和命运交织在一起,没有那么多“如果”。金庸彷徨无计之时,巧遇一位熟人,让他决定从国立中央图书馆辞职,就此离开了重庆。
四
1942年夏,金庸从衢州中学毕业,江浙沦陷,他前赴重庆报考大学,一路行经浙、赣、粤、桂、湘五省,至湖南时路费罄尽,正好中学同学王铎安的哥哥王侃在湘西泸溪办湖光农场,金庸遂寄居农场。湖光农场主要种植油桐树和油茶树,还建了苗圃,培育油桐树苗,金庸在这里半工半学,直到1943年夏,才考取中央政治学校。
1945年的春天,《太平洋杂志》第二期夭折,金庸对前途更为迷惘,恰好王侃来重庆办事,二人重逢,他再度邀请金庸帮他经营农场,重要的是,许诺如果经营有方,油桐树栽植成功后,将会资助金庸出国,这个条件让金庸颇为心动,便答应了下来。4月19日,金庸从国立中央图书馆离职,与当时已从中央大学休学的高中同学余兆文一道前往湘西农场。
湖南大学于1938年内迁至辰溪县,距离农场不远,金庸便想借读湖大,重续学业,于1945年8月8日,写信给湖南大学校长胡庶毕:“学生原籍浙江海宁……恳请先生准予在贵校借读以成生负笈后方之志……如蒙允许,生愿受严格之编级试验,或请准予暂在四年级第一学期试读,如成绩不及格可即予开除,但求能赐予一求学机会……自知所请于贵校规定或有未合,惟请先生体念陷区学生环境之特殊、情况之艰苦,准予通融借读或试读……”并备言自己为了求学,千里辗转,突破日军防线的艰辛经历。金庸言辞虽切,但校方未予通融,胡庶华校长于18日按有关规定签字批复:“关于借读需向教部请求分处,本校不能直接收容。”回绝了金庸的请求。
金庸多年后回忆自己寄居湘西的经历,称“那是在自己最穷困潦倒的时候”,彼时之失意,溢于言表。《笑傲江湖》中令狐冲抓青蛙吃等等细节,即是当时他饥饿的真实经历。如此困境,陪伴金庸的还是翻译。他从重庆离开时,带了一箱书,多为外文书籍,也许就是他准备编选《二十世纪英文选》的书籍原本,他在农场开始试译《诗经》,并计划编写一本《牛津袖珍字典》,可惜都未能完成。
湘西闭塞,抗战胜利的消息稍晚才传到金庸耳中,由于王侃的一再挽留,他直至1946年6月才离开湖南回到浙江。
金庸后来在和池田大作对谈时说:“我在1946年夏天就参加新闻工作,最初是在杭州的《东南日报》做记者兼收录英语国际新闻广播。”杭州《东南日报》于1927年3月12日创刊,1937年2月1日社址迁至杭州众安桥畔,大楼五层,是当时杭州的地标性建筑。《东南日报》是浙江地区有名大报,新中国成立后并入浙江日报社。不过进入东南日报社的时间,金庸记忆有误。浙江档案馆馆藏有东南日报社的全宗档案,其中有职工登记表、金庸签下的“东南日报社职工保证书”以及离开报社时的“辞呈”。按照职工登记表记载,他进社日期是“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亦即是1946年11月22日,介绍人是陈向平。
陈向平又名陈增善,1909年出生,1926年在宝山县立师范读书时就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抗战全面爆发后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陈向平担任《东南日报》副刊《笔垒》主编,1941年,陈向平从来稿中发现一篇散文《一事能狂便少年》,读后深为赞赏。这篇稿子出自正在读高中的金庸之手,二人相识后,结成了忘年交。金庸早期的一些散文多发于《笔垒》副刊。
《东南日报》分“云和版”与“南平版”,抗战胜利后,“云和版”回杭州出版,“南平版”则迁上海为总社。1946年,金庸回到家乡浙江海宁,风尘困顿,已无法继续求学,他想起陈向平,遂写了一封信:“……陈老师,还记得良镛载于《笔垒》的文章《一事能狂便少年》……良镛在湘西油茶农场年余,发展未果,故回浙江家中闲待。战争流离尚已结束,良镛思虑再三,欲在杭州谋一职糊口……”
陈向平接信后,向杭州《东南日报》总编辑汪远涵推荐了查良镛。汪远涵是浙江温州人,毕业于复旦大学,1939年和陈向平一同进入《东南日报》工作,从编辑一路做到总编辑。金庸初到编辑部,说是外勤记者,汪远涵给他安排的任务却是“翻译”,按“东南日报社职工保证书”上提供的说法“兹保证查良镛在贵社任记者兼收英文广播,工作服务期内,确能遵守社方一切规章,听从调度,谨慎奉公……”这份工作实则就是收听外国电台的英语广播,选择可用的翻译。金庸偶尔也会翻译一些英文报纸上的短文,以备报纸缺稿时使用。报社没有录音设备,这种国际新闻稿全靠直接收听后翻译,金庸晚上八点开始工作,边听边记,最后凭借记忆全文译出。
五
进入《东南日报》不久,1946年12月5日,金庸即在《东南日报》第三版上发表《英国最近的外交政策——艾德礼表示支持联合国》,这是金庸翻译伦敦《泰晤士报》记者斯蒂特的一篇稿子,署名“查良镛”。金庸出色的翻译水平,给汪远涵留下很好的印象。1988年,汪远涵与金庸通信时还提到这件事,印象深刻:“上海总社的陈向平先生介绍你来杭,做这份收听和翻译的工作……陈向平询问过你在《东南日报》的境况,我说你英文水平相当高,行文流利,下笔似不假思索,翻译特好。”
同学余兆文来杭州,对金庸的工作非常震惊:“外国电台广播,说话那么快,又只说一遍,无法核对,能听懂就已经很不错了,你怎么还能逐字逐句把它们直译下来?”金庸则解释:“一般说来,每段时间,国际上也只有那么几件大事,又多是有来龙去脉的,有连续性。必要时,写下有关的时间、地点、人名、数字,再注意听听有什么新的发展,总是八九不离十,不会有太大差错。”足见金庸在翻译上的功力和严谨态度。
金庸在《东南日报》工作不到一年,在这期间作为外勤记者写了些访问文章,还在《东南日报》副刊《东南风》和《东南周末》主持“信不信由你”“咪咪博士答客问”栏目,其他主要是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