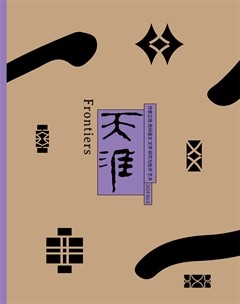茶与禅,一直相生相伴,如同孪生兄弟——名山名寺,必出好茶,必有名茶。诸多名寺的附近,常常辟有茶园,最初种茶品茶的,也是僧人。陆羽《茶经》说:“杭州钱塘天竺、灵隐二寺产茶。”西湖龙井,传说是南北朝诗人谢灵运在天竺寺翻译佛经时,从佛教天台宗发祥地天台山将茶种带去了杭州。宋代时,灵隐寺大和尚辩才法师退居老龙井,在狮峰山麓开山培植成龙井茶。杭州灵隐寺佛茶,种植和制作者也是寺院的僧人和居士。四川雅安的蒙山茶,相传由西汉时蒙山甘露寺禅师吴理真所栽,称为“仙茶”;庐山云雾茶,传为晋代名僧慧远在东林寺所植;江苏洞庭山碧螺春茶,传为北宋洞庭山水月院山僧所植,它还有另一个名称,叫做“水月茶”。除此之外,武夷山天心观的大龙袍、徽州的松萝茶、云南大理的感通茶、浙江余杭的径山茶、浙江景宁的惠明茶、天台山的罗汉供茶、雁荡山的毛峰茶等,都产于寺院。安溪铁观音“重如铁,美如观音”,其名来自佛经,与佛教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君山银针产于湖南岳阳君山,最初也由僧人种植;惠明茶因浙江惠明寺而得名……至于普陀佛茶,因产于普陀山,最初是僧侣献佛、待客用的,干脆以“佛”命名了。
茶,三分芳香,七分幽香;禅也如是。凡曲径通幽处,皆可达禅。西湖龙井也好,灵隐佛茶也好,形状扁平,颜色翠绿,习性清爽;一经冲泡,香气四溢,经久不散,不仅有养气颐神、明目聪耳之功能,还有着清心寡欲、淡泊宁静之效果。后者,有些暗合佛教“明心见性”之真谛。
船子和尚曾有诗云:“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这一首诗,有清风明月之境界。船子和尚,原名德诚,遂宁人,生活在唐中晚期,隐居华亭时,师从药山惟俨禅师,常乘小船往来松江朱泾间,以钓鱼度日。这一首诗,写的就是船子和尚以钓鱼之好悟天地至理——一轮明月,一叶扁舟,天心枝满,吾心皎洁。
大道相通,法门无二,船子和尚钓鱼能开悟,更何况饮茶乎?
一个著名的禅宗公案,据说来自日本明治时代的南隐禅师——一位学者向南隐禅师请教禅的智慧,南隐不回答,只是给学者倒茶。学者示意杯子满了,南隐仍不停,继续倒水。学者忍不住说:“师父啊,茶已经满了,都溢出了!”南隐笑眯眯地说:“如果你不把自己那杯茶倒空了,叫我怎么跟你讲禅呢?”
这个著名的场景,演绎了一场高级趣味:禅,于悄无声息中,如茶水般散发着沁人心脾的味道。有人说故事跟茶无关,茶只是道具,换成水也可以。我以为不是这样,若只是水,诗意减弱,禅意缺少,更缺少智慧的高级感和玄妙感。高级和低级趣味怎么区分?若带来智力开启,是高级趣味;若带来感官反应的,则属于低级趣味。或者,能开拓边界导向无限的,属于高级快乐;凡缩小边界导向有限的,属于低级快乐。故事有些玄妙,却在阐述一种道理:在无限面前,有限反而是一种累赘,或者是一种阻碍。
“禅”是什么?莫衷一是,各说其道。从本质上说,是“清净”的外部与清净的“内心”,也可称为“菩提心”之间的共融共振。“清净”很重要,若污浊的环境和思维,一定无禅;必须是极致的“清净”,才能让“禅”悄然降临。没有清静,没有洁净,一派油腻,一派功利,必定无“禅”。
“禅”是悄然的,是天造地设的,是一种境,也是一种场。它还应具有某种启迪性,带有某种“神示”,不生硬也不功利。“禅”初起的一瞬间,外部是清静的,内部也是清静的;物器是清净的,人心也应是清净的——禅起如光,如洁净的云和风,一切都活了过来。“禅”还是一种通感,不可说,不好说,只能试着用文字来接近,用比喻来明白。文字不是“禅”,却可以试着去理解和明白“禅”。
“禅”与“定”,一般而言,如影随形,难分难舍。“禅定”二字,有着玄机:隽永为“禅”,心不乱为“定”。“禅”为什么让人亲切?因为本质上是真实的,有内容的,是“有限”融入“无限”。中国传统社会,农耕文化占据主流,总体上是实在朴素的风格,孔子质朴,孟子耿直。自汉儒之后,不免虚伪作假、装腔作势、不懂装懂。科举充满功利,教育则是拉长着脸,日日填鸭似地灌输,让学习者根本没有主观能动性。相比之下,“禅”因为真实生动有内容有诗意,能让授与学之间默契呼应,心津荡漾。
中国传统社会也好,传统教育也好,是一个深色的背景,低沉肃穆。“禅”,是一种激活,如一朵无形的花朵,顺应天时地利人和,“啪”地一下绽放。
茶道让生活艺术化,也让人生哲思化。中国文化的主流是儒家,目标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殊不知在此目标之前,须有“正心诚意”。“修齐治平”好办,只要跟着圣人的倡导亦步亦趋往前走就是;“正心诚意”就比较难了,要求追溯,要直面“心”——“心”是什么?是一个问题。“心”何在?又是一个问题。一个接一个的形而上问题,是最难以面对和捕捉的。自唐末后,儒家将“正心、诚意、修身”与茶道结合起来,是借鉴了佛家的做法——之前寺院的坐禅也好,悟道也好,不管是否借助于茶,目的都是“正心诚意”。宋儒的主流是孔孟之道,加入道和禅的成分,“三教”融合,成为了程朱理学。到了王阳明之时,“正心诚意”最后得以突破——以融合了儒释道的“致良知”,完成了这一个使命,使得儒家这一提倡有了革命性的突破。
宋朝之所以在智力上有极大的开拓和上升,文化风格上有着整体的幽深和雅致,茶起着无形的作用——茶是机缘,是暗示,也是培育。茶道还是释放,让人坠入艺术和人生的通感之中——喝茶者可以从天青色的瓷杯、琥珀色的茶水,静谧、缓慢而优雅的过程中,受到美的启迪,打发无聊,填充寂寞和孤独,进而感觉孔子的温润、老子的旷达、释迦牟尼优雅的智慧,悟彻到生命的无限与广博。
什么是“禅”?只要细细地品尝茶的滋味就明白了,那种无法捕捉的空灵,难以表述的甘和苦,难以言喻的身心茶合一状态,就是“禅”。在现场情境的导引下,身、心、灵全面打开,全面融合在一起。这时候整体的感觉,是超越语言的——心有灵犀一点通,语言和文字达不到的地方,禅和意境,已在那里微笑、凝视、等待、拥抱了。
人,若能明白有存在超越语言文字之上,若能明白语言和文字的缺陷,竭力让思维和感觉抵达语言文字的边际。智慧也好,神通也好,必定随之产生。陶渊明诗“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就是这个意思。
多说一句:音乐上的休止符,中国画的空白,数学上的零,哲学上的无……都是彼此的边界。人以边际为警醒,以手指月,便有更广阔的想象空间。
茶与禅,是东方文化的“双生花”。它们一起生——茶饮诞生的年代,也是禅诞生的年代;也一起长——有茶即有禅,有禅即有茶,二者不可分。如此过程,跟佛教所云“戒、定、慧”无二。也因此,茶与禅结合得尤为紧密。很多公案,无头无脑,让人看得不知所云。为什么会如此?问得没段位,一看就不是“明白”之人。回答之人懒得“鸡同鸭讲”,或者随便回答,或者胡乱回答,王顾左右而言他,自然也形成“公案”。理解禅的故事,不能从字面意思去理解,而是要深入到文字之外的语境。
诸多禅宗故事,记录的是语言的表面意思,至于深层次的意思,必须得根据情境,苦思冥想慢慢悟。
所谓禅意,从语言的角度来说,就是将意义隐藏在语言文字之外,否定语言的“桥梁性”。
禅,不相信语言和文字,也不怀疑语言和文字。语言和文字很奇妙,怀疑它,反而有好的语言,也有好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