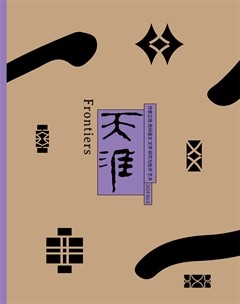从1988年到2024年,一晃,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已走过36个年头。从尘封已久的笔记中整理这篇文稿时,在海南生活与工作的诸多画面便接二连三在脑海里涌现与叠映。且让我有选择性地把一些青春飞扬在海南岛上的场景,用文字的形式定格下来。
我从湘西来
大学毕业,正值十万人才下海南的高峰时期。各大报刊和电视,常透露出“种子炒熟了,丢在海南的土地上都能发芽”的消息。不愿在湖南西部沅陵老家做教师的我,趁着这股热潮,带上毕业证和发表的一些文字类作品,再收拾几件衣物,一路经历汽车、火车和海轮的颠簸南下赶海。
海轮从广东湛江抵达海口秀英码头后,一辆中巴把我和一位同行的乡友带到海口市得胜沙路。下车后看到一座连着一座的破旧西式骑楼和窄小的街道,以及街道上三五成群戴棕叶斗笠、讲海南普通话和脚蹬三轮拉客的车夫,周身不觉一凉。现实与想象中的差距竟是如此之大,曾一直被我向往的海口竟然会是这个样子!
我们找到一家小旅馆住了下来。晚上走在街上,因为缺电没有路灯,做生意的人家各自在门口摆台柴油发电机发电照明,“突突突突”的发电机声此起彼伏,把忽明忽灭的海口远远近近地连成一体。
几天后我们决定去三亚看看。长途汽车在不宽的破旧公路上左摇右晃努力前行。依着窗口,我看见公路两旁的荒凉,以及一畦畦长在路边的菠萝、香蕉,还有一片片高高瘦瘦的椰子林与橡胶林。
在天涯海角的海边,我们邂逅了许多闯海青年。有的在岸边临时搭建的简易餐馆打工,有的穿行在游客中推销报纸和旅游地图。他们尽管被强烈的紫外线把脸面和手脚晒得黑里透红,却个个目光如炬,在强烈的阳光下透出坚定与执著。这样的情形只得让我们返回海口,暂住在海南省燃化公司招待所,然后满大街去看招聘广告。招待所的饭菜很便宜,每顿只需一元五角。饭是白米饭,菜是一条约五寸长的油炸小海鱼和素炒空心菜,每餐如此。
我上岛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海南信息报》做记者,报社位于海口市龙华路义兴街的一座四层小楼上。门口有张木质方凳,凳子上竖着块靠墙的塑料牌子,上面是“海南信息报社”几个黑底大字。报社只有一间房子,是内外套间,里面住人,外面办公。设有记者部、编辑部、公关部、广告部、信息部等,除记者部和编辑部,其它都是经营部门,被人承包后在报社外租房办公。我在记者部负责新闻采写,第一次外采的稿件是《海南茶叶市场走笔》。稿件写成后署上“本报记者阿里”给一位在海南报界工作的乡友过目,他说稿件写得不错,不过对署名提出异议。他觉得我刚来海南,必须打自己的名声,不能使用笔名。
此后,我基本上用真名发稿。
连同报社,并不宽敞的四楼一共有五家单位。其中有三家贸易公司和一家湖南老乡开设的小型缝纫社。为解决吃饭问题,大家合伙请了位川籍女厨师做饭,每餐一荤一素一汤,收费三元。汤多为不放油的冬瓜海螺汤,海螺很小。饭后,我们总爱舀上一勺倒在饭碗里慢慢剥食,味道鲜美。
听杨隆灼讲上岛的故事
当时报社住着我、杨隆灼和叶星。叶星是湖北人,性格内向,话语不多,以前在《海南工商动态》杂志做编辑,两天前才跳槽到了这里。杨隆灼是福建南平人,每到晚上,他总爱换一身很夸张的宽大短装,坐在椅子上聊一些自己的故事和海口见闻。海口天热,我们都不愿睡在里屋的床上,临睡前把办公桌拼揍起来,然后窗户洞开,直挺挺地躺在办公桌上入睡。
杨隆灼在报社信息部工作,承包人未给他安排住处,他每晚都步行来这边和我们搭铺。他在部门负责收集、发布房地产出租、出售信息,一旦成交,就抽取提成作为工资。但海口的生意也并不好做,到部门半个月,只成交了一笔朋友的租房生意,拿了五十元提成。
不过,他初上海岛的故事,颇具传奇色彩。
高中毕业那年,没考上大学的他,与在县林业局工作的父亲大吵一架后借了几百块钱到了海南。上岛第一天,他去找旅社。这家说五元,那家说十元,他带的钱不多,不敢乱花。好在海口天热气温高,许多住不起旅店的闯海人带着草席在海口汽车总站前坪以地当床,席地而卧,他也跟着如此。第二天醒后去找工作,别人告诉他有文凭的可以去人才交流中心碰碰运气,没文凭的只能走街串巷看贴在墙壁上的“招聘启事”。他徒步走了好几条街巷,抄下了十几个招聘单位的地址,可去了之后总是被人拒之门外。某晚躺在草席上仰望星空想出路,装在口袋里的那本抄满招聘单位地址的小本子突然间给了他启示:每天有那么多人来海南求职,何不办一份招聘报!于是他每天出门收集贴在街头巷尾的招聘信息,回来整理归类后找打印社打印出来,起名《海南招聘报》,自己带到海口新港码头或秀英码头兜售,每份五元。
后来,他还以扣文凭、交押金的方式招聘了两名员工。一名守在新港码头卖报,一名守在秀英码头卖报,他则专门负责收集和汇编招聘信息。
可惜好景不长。一天,他在收集信息的途中被拦住检查暂住证,因提供不出相关证件被提溜起衣领塞进一辆闷罐卡车带走,押送出岛。半个月前,他才想尽办法从湛江乘私人渔船偷渡上岛,应聘到现在的部门。
杨隆灼的故事,惊险中也给了我希望:海南是个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宽松之地。相信会有那么一天,而且注定有那么一天,自己不会两手空空地回家!
有苦有乐的闯海时光
不同的身世,共同的追求,让上岛月余的我有了一帮来自天南海北的朋友。大家白天在各自的报刊社工作,晚饭之后,就从四面八方聚在一起逛街聊天,抑或骑着二三十元买来的旧单车去海边游泳。
那时的单位大多没有食堂,为解决不去饭馆吃饭的问题,我们在龙舌坡的民居中找到一块长满杂草的废旧宅基地。大家动手清理出一块场地,从附近搬来几块石头垒成石灶和石凳,再一起出钱到小商店里买来厨具和碗筷,一个简易的露天伙房宣告建成。傍晚,我们去龙舌坡农贸市场买回猪肉、海鱼、蔬菜、粮油和白酒,然后分工负责。某某拾柴、某某煮饭、某某做菜、某某收拾锅碗瓢盆。入夜,我和来自江西的老龙、四川的刚子、湖南常德的阿文等朋友围坐在沸腾的铁锅旁大声说话、大块吃肉、大口喝酒。那种酒喝干,再斟满,今夜不醉不还的情形,刻骨铭心。夜色在我们带着醉意的欢声笑语中越来越浓,我们每个人都像寻仇似的,把脖子、脸和双眼喝得血红。
之后,每一个不下雨的黄昏,都有过往行人瞥一眼我们几个在空地上生火做饭的闯海青年,与同行者笑着议论几句,然后低头走自己的路。捡柴回来的阿文,常会抱起从老家带来的桃木吉他坐在大石头上,面朝下沉的夕阳和满天红霞动情地弹唱一些流行歌曲,为这幅苦并快乐着的画面配上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