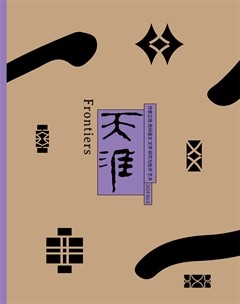每年初夏,家里总是要清理一批旧衣服出去。扔旧衣服之前,妻子总是让“一辈子穷怕了”的我“把把关”。
这样的把关,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新衣服要进衣橱,旧衣服必须让位。开始的时候,我会摸上一遍,假装检查口袋里是否有遗漏的纸币。这几年,“把关”的借口都没有了,但我还会用目光把就要扔出去的旧衣服迅速“摸”一遍,那件在北京被偷的新夹克衫又出现了。
为什么我总是不能忘记那件新夹克衫?
真的因为我是穷怕了吗?
新夹克衫的故事起自1991年4月,中风瘫痪两年的父亲能拄着拐杖走路了,我决定给自己圆一次北京梦,长这么大了,还没有去过北京,实在太渴望了。
为了北京之行,我做了许多准备。买一张去北京的火车票。向单位请假。买新夹克衫——我的衣服都太旧了。
请假问题最先解决:调课加星期天。火车票的问题,是写信请在南京读研究生的师范同学帮忙购买的。
新夹克衫得去县城买,去县城不通汽车,需要乘船:上午去,下午回。百货公司的夹克衫式样老套,我就去了城北拱极台边的自由市场。拱极台边原是有桃花的,说是孔尚任在这里完成了《桃花扇》。但那年春天是没有桃花的,连桃树都没有。只有服装摊位构成的城北自由市场,商品都从南边进货,那时候,“南边”就代表时髦。
我到达自由市场的时候正是中午,没有多少顾客。我走了一趟,又回走了一趟,没有发现我能穿的夹克衫。
正失望中,我被一个烫了卷发的男摊主逮住了。
“你不试一试,哪里晓得自己穿哪件?”
卷发摊主说的是一口城里人的话,在说城里话的人面前,我有不由自主的自卑感。
热情洋溢的卷发摊主给我推荐了许多时髦夹克衫。怎么试,怎么别扭,卷发摊主竟然也认同这种“别扭”,因为尺码都显得大。
我的个子又实在太小了,又瘦又小。
再小的尺码,都“担”不起来。
“担”这个词,是我们老家的话,很形象,把衣服当成担子,因为太瘦小了,真的“担”不起来,尤其是肩那边,松垮得很。
卷发摊主让我耐心等待,他继续找。终于,他从衣服堆捉到一件灰黄色的夹克衫,很安静的灰黄,是我喜欢的颜色。更加神奇的是,我瘦弱的肩膀是能够“担”得住这件夹克衫的。
“太像齐秦了!”
卷发摊主说完了这话,怕我怀疑,又补了一句。
“小一码的齐秦。你肯定喜欢齐秦!”
我还没有接话呢,卷发摊主就主动给我下了定论。
因为有了“小齐秦”这顶高帽,我连价钱都没有跟卷发摊主还,就买下来了,花掉了整整一个月的工资。
回到学校,同事说这件夹克衫不错,但还是太贵了,问我为什么不还价啊?城北自由市场那里商品的价钱,都是“拦腰对半砍”,意思是还到摊主叫价的四分之一。
我没有跟同事说有关齐秦的对话,反正那几天,我在学习英语的录音机里,播放的都是齐秦的带子。
想一想吧,深夜在宿舍,我穿着新夹克衫,听着《狼》:“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听着《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我内心也跟着唱,想象着北京之行,想象中的天安门的光彩似乎真的照亮了我。
接下来,我穿着这件新夹克衫挤火车。那些年,火车站的黄牛太多了,我的同学排了队,也只能买到一张南京到北京的无座票。晚上8点上车,第二天下午3点抵达,全程时长大约是十九个小时。
无座的火车之夜特别难熬,南京航空学院的一位应届毕业生主动和我商量,让我和他一起背靠背席地而坐,这样我们就相互有了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