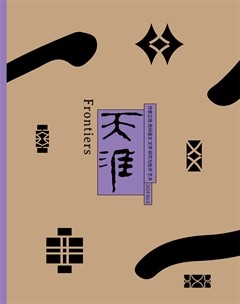历史影像,此处特指在一定的历史期内具有典型意义或代表性的摄影作品;其特点是与当下存在时空隔阂和观念落差,内涵由时间积淀而成的丰厚思想。优秀的历史影像,传播时间长,流布面广,影响深远。本文旨在揭示这些作品在传播过程中所彰显的中国形象、时代特征以及社会思潮,与影像内在的结构、肌理及其特殊的价值生成机制之间,存在的紧密又隐秘的关联。
依据时间的轴线,试将中国的历史影像大致分为四个部分,其间体现的中国形象和时代特征也各有分别。
一是他者的偏见。即:早期由西方来华摄影师承担的对于中国的拍摄,以及由他们所主导的中国形象在西方的传播。二是朴素的呈现。即:中国本土摄影师群体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崛起以及随之介入的影像传播,改变了此前那种一味由偏见主宰的局面。三是虚化与美化。即:1930年代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宣传摄影中的虚化和美化成为一个显著的特征,中国摄影的规制得以确立并在战后漫长的制度沿袭。四是图像自信。自1980年代初至整个的1990年代,中国摄影在政治气候的改善中获得了艺术上的观念突破,摄影的社会功能与艺术价值发生了巨变,摄影基于现实、历史和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批判精神在创作中获得相当程度的认可,借助摄影,人们看到了一个自信的中国。
他者的偏见
摄影技术的滞后、传播渠道的偏狭,使得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形象的对外影像传播,基本由西方和日本来的摄影师主导并肆意发挥。因而,对于绝大多数的被相机眷顾的中国人而言,他们只是被动成了“在西方的中国人”,是作为符号化的中国人形象。他们不了解自己的照片与平常镜子中观看到的自己,有着怎样的分别,也不了解图像中的自己到底被他人做了何种解释。更不清楚,照片这种可以流动观看且长期保存的身份与心灵的替代物,被异域人群的反复观看与凝视,到底意味着什么。
《钦差大臣耆英》由法国摄影师于勒·埃及尔拍摄,在众多出版物上,这幅照片被标注为“中国的第一张照片”,其中关系十分微妙。1844年8月15日,于勒·埃及尔以访华贸易使团代表的身份到达澳门,甫抵中国的前几周他忙于草拟条约,直到10月14日才有时间利用随身带来的达盖尔银版相机,拍摄澳门的街景以及南湾的风景。法兰西是紧随英美之后叩开近代中国大门的征服者,埃及尔此行,正是以征服者的身份参与中法《黄埔条约》的签订,摄影是这个法国海关督察在工作之余的爱好。他要求陌生的中国人摆出一些他认为理想的姿势接受他的拍摄,“行人对我的要求非常配合,他们是世界上最友好的人”。十天后的10月24日,中法《黄埔条约》签订仪式在黄埔港阿吉默特号战舰上举行,埃及尔拍摄了签约后的合影纪念照,其中有清廷钦差大臣耆英,法方的法国公使拉萼尼、海军上将、第一秘书以及翻译等五人,深色的背景、凝重的影调,只有人物的脸部和衬衫、白裤泛出一些亮色;除了后排两人面目不清外,前排三位中法人物的姿态,十分贴切地以其个人身份诠释了各自的国家处境和形象。征服者的姿态充分暴露了他们高傲与轻慢。与耆英并列的法国公使交叉着双腿,双手拢在胸前,目光并不看镜头,而是尖利地射向右侧远处不确定的目标,预示着他理当所得并有更为宏大的追求;紧挨公使的海军上将,以半坐半站、看着别扭而他自己觉得舒服的姿势,侧靠于公使,他的目光与公使一样射向同一角度的远方;他白色的长裤愈加明晰地揭示了他内心的倨傲——他岔开了右腿,并高高踏在旁边的物件上。摄影在瞬间获取了人物的神态表情,却在本质上记录了人们隐秘、真实的内心。
埃及尔在日记中说明,他在拍摄了这幅合影之后又为耆英拍摄了单人肖像——所谓的“中国的第一张照片”。在时序上,如果必须认定“中国的第一张照片”,即便忽略他在10月14日开始拍摄的那些“世界上最友好的(中国)人”,也应该是签约时的这一张合影,并且也更具代表性意义——摄影术随着入侵者的脚步一起来到了中国。
在大众传媒业尚未兴起,在摄影介入公共事务的传播与表态之前,亦即摄影的媒介价值尚未显现之时,摄影的身份,限于民间的角色——纵然是高官政要的肖像,也只具备小众欣赏的意义。埃及尔表明当时他将耆英的个人肖像赠送给了照片的主人,但耆英本人极难有将其保留至今的可能,合理的解释是由其依据当时外国要员来华的交往惯例,将其“作为外交礼仪的纪念品”赠送给西人之后,西人作为特殊之礼收藏多年,再由西方重新传播至中国。照片由西向东的回流,显然不会遵从其历史价值和图像意义大小的标准,而是更充分地挖掘图像内部可能潜隐的传播价值。作为最早接受西人拍摄的中国人的肖像,又具清廷大员的身份特征,加之其特殊情境下木讷呆滞的神态表情,符合西方人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模样的想象。——耆英在此前两年已经代表清廷分别与英美签订了《南京条约》《望厦条约》,作为“卖国条约的熟手”,来自京城皇宫的命令、外敌的武力恫吓、民众的施压以及个人内心的抗争,似乎都反映到了他的表情上,他谦卑、怯弱,略有些不安地正眼平视着摄影师,那种隐忍、屈辱和麻木,恰当地象征了快门释放那一刻的中国。木讷呆滞的神态表情,符合西方人对于落后中国和中国人模样的期望与想象;而后世国人接纳晚清这位“卖国贼”的肖像,又迎合、坐实了后人对于前朝“腐朽没落”的政权及其官员的形象的心理预期。
历史中人,每一个都具有相对独立的精神世界,但只有将图像中人,与其所处的政治、社会、文化等等大的环境作立体的、连贯的审视,才能获得对于作品的整体性阐释。
官方主流的意识形态,同样会在民间占据一定的分量。在1860年代,美国人弥尔顿·米勒借他在中国开设的照相馆,拍摄过大量体现中国符号的照片,并在西方传播。《中国妇女在观看立体照片》是一幅匠心之作,他希望传递出一种新事物在古老中国的妇女心理上产生的好奇与震荡,但是这幅图像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中国人的形象在十九世纪末的西方依然是保守和封闭的象征,女性尤甚;而中国女性对摄影术成果的欣赏,旨在表达摄影术以及随之而来的西方科技与文明在征服东方、征服中国的依据。
三名站立的妇女,都将视线集中在居中站立的一名妇女手中的立体照片上。手持照片的妇女,目光俯视,表情略显不以为然状,显然她已经细细观看过照片中的图像细节(至少摄影师期望表达这样的信息)。距离立体照片最近的妇女,身体微倾,目光尤为专注,表情也最为丰富,显然(或者显示)她是首次观看,也符合一个人对神奇之物初次相见时的情绪反映。最左侧的一位女子,她看到的立体图像之清晰度不如前一位,但是她保持着距离的观看,也说明了压抑的好奇心,神情之中已经有了图像赋予她心理的愉悦感。最值得关注的是最右侧的女子,她单单坐着,并且直视镜头、直视着摄影师,直视照片的观看者(更确切地说是斜睨),她神色冷峻,眼睛里充满了疑惑和不满。她的情绪、状态与她的三位同伴格格不入,坐着的姿态又显示出她对整个局面的主宰。她是否观看过或者知晓正在被观看的那幅立体照片的内容?答案是肯定的,同时也表明了她对于立体照片以及照片中所反映的内容、包括对摄影术这门新技艺的不满。她的表情令观看者感觉到某种不适,但与她的同伴相比,她更具一种个性主导下的冷艳之美。这是弥尔顿·米勒拍摄于他的照相馆内的大量肖像中的一幅(花格子地毯是他作品的个性化标记),被摄者很显然是受其之邀并经过了指导,然而视觉观看的印象,颇似四名女子的私人情趣被一名不顾礼仪的摄影师冒犯后,突然抢拍下来的结果。他为何做如此的摆布和设计?他传达出来的这些信息,又期望说明怎样的问题?那是1860年前后的中国,摄影已经进入到广州等通商口岸主要城市的官商家庭。这四名中国妇女披着头巾的装束,显示她们的出身并非豪门,但也并非一般家庭的贫弱女子。最左侧那名女子手持雨伞的动作,似乎泄露摄影师的秘密:他在努力营造这样一个风雨途中的小憩、偶尔发现摄影术而引发各色人等诸多不同反应的情景,旨在说明并不与社会事务密切接触的、深闺中的中国妇女,初见立体照片时的复杂又微妙的心理。
摄影作为新事物和妇女作为最封闭的中国人群体,在这幅照片中得到了最切实的反映。观看,以双重套取的方式,进入到了视觉之下的心灵世界。但图像的解读远未止步于此。我们可以将这张照片图解为摄影术初入中土时国人心理反应的见证:喜爱、疑惧、神往,也有些许对于外人的惊惧、冷漠以及不愿意被打搅的反感。冷眼看向镜头的女子,以唯一的坐姿出现在画面中,虽然不居中,虽然不以体积之大以示其重,但坐姿已经将一切陈规都做了勾销——在人群体,唯一的坐姿者对于群体的站姿者具有姿态语言上的主宰——她才是最重要的意见表达者。依据图像结构中“左轻右重”的理论,她恰恰又是处于“最重”的右下方,她的态度与观点,于是就成为整幅图像的主要表达:中国的落后与封闭,她对于摄影术以及西方文明的厌恶与拒绝。这也是始终倚重于文化渊源之厚实的中国人,在初始接触西方现代文明时,具有典型性意义的表情。
百姓的表情,并非无足轻重的散点思维,特定情境下的呈现,倒是可以以最真切的姿态语言,折射出具有时代性特征的历史内涵。
这个时代的拍摄者大部分属于西方来华的异域摄影师,国人面对此一“奇技淫巧”的戒惧,自然而然,所以在最初的摄影图像中,呆滞、木讷、愚钝、守旧、压抑,这种种表现,既是照相术在当时无法用高速快门凝结生动表情的技术所限,所以需要被摄者自觉凝固并保持某一种僵硬的表情所致,又有着特定的社会气候施加于普通人从内心到外表的普遍特征这一因素使然。
偏见不一定来自主观故意,也有长期的来自文化上的歧视、科学与技术发展上的优越感以及信息不对称所致的误读。
朴素的呈现
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本土零星出现的摄影师渐渐走出照相馆,以官商友伴的方式介入中国形象的制造与传播,且逐步形成了一个以身份建立的群体;至此,中外两股力量,承担了中国影像的摄制与传播。直观而真实的中国和中国人,以朴素的方式出现了,中西间的观念融通也就此产生。
《李鸿章与格兰特》出自广东籍摄影家梁时泰之手。1871年后他先后在香港、上海、天津开设照相馆,并以其精湛技艺获得了清政府委托的多件大宗拍摄业务,这其中就有修建铁路、筹备海军等数项新政措施的拍摄,他还曾经为光绪帝的父亲醇亲王奕譞检阅北洋水师拍摄了实况。1879年应邀专门为到访的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和满清重臣李鸿章会面拍摄合影,则是他摄影生涯中一项重要的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