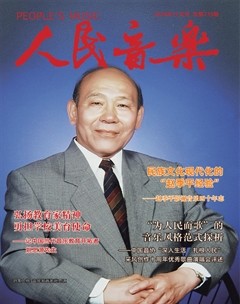2024 年, 是赵季平投身影视音乐创作的第四十个年头。笔者重温了他四十年来创作的大部分影视音乐,再一次真切感受到这些作品在中华民族文化现代化进程中走出了一条既独具个人特质与属性,又有着广泛启示意义的路径,本文称之为民族文化现代化的“赵季平经验”。
一、赵季平经验形成的时空机缘:从延安传统到民族复兴
无论从作品呈现, 还是从其所处的时空方位,都可以判定,赵季平的影视音乐几乎必然地会成为民族文化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一)从时间线索来看,赵季平是衔接并贯通了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初期、新时期,再到新世纪、新时代的一位作曲家。
赵季平出生于1945 年, 他的父辈就是延安时期的那一代艺术家譹訛, 其父赵望云先生虽身未在延安,践行的却是典型的延安文艺路线,早在三四十年代,就在多地农村采风,并完成了在当时轰动画坛的西北写生,建国后,又与从延安来的石鲁先生等一批画家,以“一手伸向生活,一手伸向传统”的理念,创立了“长安画派”,将延安文艺传统发挥到了极致。这些艺术实践对赵季平产生了直接影响。因此他在多次采访中都说, 深入生活是他的家传,采风是他的家风。
从赵季平的成长历程来看,他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后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譺訛、陕西省歌舞剧院工作,这些机构及其代表人都是从延安延续下来的践行延安文艺传统的代表性机构, 因此可以说,赵季平是在延安文艺传统中成长起来的艺术家。他的音乐创作正是从延安传统出发,经历了从新时期到新世纪的不断深化, 延伸到民族复兴的新时代的。他一步步践行音乐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将中华民族古老的声音融入现代化的宏大交响之中。
(二)从空间方位来看,赵季平成长于中国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和延安文艺传统的富集之地西安。
作为赵季平生活与创作空间的古都西安,不仅是延安文艺传统的主要践行之地,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发祥地和传承地,更是作为中华文化根脉的礼乐文化的始源地。如此,从生活空间到工作空间,再到创作空间,赵季平所处的空间方位从根本上决定了他走上民族音乐现代化道路的必然性。
(三)以第五代导演、西部电影为代表的中国民族电影的崛起,为赵季平走上民族文化现代化道路提供了重要历史机遇。
以西安电影制片厂为策源地的第五代导演和西部电影,是在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和中华民族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时空起点上崛起的。
1984 年,由第五代导演的主要代表人陈凯歌担任导演,陕西籍电影人张艺谋担任摄像,西影张子良担任编剧,后来被认为是中国西部电影开山之作的《黄土地》,为赵季平提供了第一次“触电”的机会, 并由此打开了赵季平影视音乐洪流的闸门,也为中国民族电影开启了走向世界的音乐之路。赵季平凭借在影片讲述的中国人精神现代化的开端处,用现代意识激活的陕北民歌元素,让《黄土地》几乎成了一部西部音乐片。
赵季平长期蓄积的民族民间音乐的蓄水池一经开闸便喷涌而出,一泻千里。由此,绝大多数由第五代导演张艺谋、陈凯歌、何平等执导的影视剧,大都是在赵季平的音乐中走向世界的。如果将赵季平所作的五十多部影视音乐串接起来,我们可以听到的, 不仅是中国民族民间音乐走进现代文明的变奏,更是中华民族从各个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族群走向现代化的一部宏大的交响诗,其中包含着中华民族从苦难、封闭、蛮荒,走向开化、文明、复兴的精神历程。
二、“赵季平经验”的核心内涵
如果将赵季平经验置于中华民族文化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中来反思的话,至少有以下几点是值得深入总结的。
(一)坚持通过“深扎”感知和发掘民间音乐元素和民族文化基因
在赵季平的创作历程中,“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绝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他对待艺术、认识民族文化的基本态度和原则。他在多次访谈中都明确强调,不深入生活,不了解民生疾苦和老百姓的内心世界,就无法真正把握艺术的本质及其文化根源。从进入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起, 赵季平便开始从戏曲深入民间音乐,进而深入到更深层的民族文化土壤之中。他长期在陕西各地考察和学习秦腔、同州梆子、碗碗腔、眉户戏、花鼓戏、道情等地方曲种,以及陕南陕北民歌,后又扩展至全国其他省区的大量地方剧种、民歌和各种民族乐器。在大量考察中,他充分认识到民间生活是生长这些音乐的文化土壤, 是中国古老的民族文化的活态存在方式。因而在深入考察和学习地方音乐的同时,他还深入到各地百姓的生活中,去体察民生疾苦,结交底层劳动者,了解其生活方式和内心需求。他先后深入到中西部地区及江南多地的民间生活中,直到七十多岁了,还多次到四川青城山“隐居”,与那里的农民一起喝茶、摆龙门阵。当地农民已经成了他无话不说的知心朋友, 却不知道他是位大音乐家,直到在电视上看到他后,才抢着要退给他喝茶、买菜的钱。从其作品中的不同地区的民歌、戏曲元素来看,在他海量作品的背后,是远远大于创作本身的“深扎”的时间和精力。
“深扎”不仅让他深入到了各地民间音乐的细枝末节之中,更让他深入到了中国社会的根部和中华民族的灵魂深处。因而“深扎”是赵季平感知和发掘民族文化的主要途径,是其影视音乐创作的根基和起点。
(二)艺术是地方性的、意识是现代性的
赵季平的影视音乐表明,有生命力的艺术往往是地方性的。事实上,从来就没有哪种音乐天生就是世界性的, 即使被认为最具世界性的交响乐,也是源自欧洲的地方音乐。但同时,任何一种来自某个地方的音乐只要做到极致都有可能是世界性的。赵季平的几乎每部影视音乐作品都有着鲜明的地方音乐元素,甚至可以说这些作品给人们留下最真切印象的, 正是来自地方音乐中提纯的旋律和节奏。电视剧《乔家大院》中反复出现的那段晋剧特有的用呼胡和二股弦演奏的旋律,便是从晋剧中提纯出来的,而晋剧又是从源远流长的山西民歌以及山西人祖祖辈辈的民间生活中孕育出来的。因而从一种地方音乐中提纯出来的核心旋律和独特节奏,是一个地方民间生活和民族文化的结晶。正是这种民间音乐核心元素的提纯,构成了赵季平影视音乐的独特魅力。类似的情形还如京胡、京剧唱腔和锣镲鼓点之于《大宅门》,碗碗腔之于《秋菊打官司》,秦腔板胡和虎狼之吼之于《活着》等。这些独一无二的地方性声音一旦出现,便会让人们进入到那个地方的人、事、方言和情感状态之中。对于影视剧而言,这种声音所构成的是剧情和人物个性发生的语境;对于整部音乐作品而言, 这种声音是它的灵魂;而对于这种声音本身而言,它正是一个地方民间生活和民间文化的抽象和升华。赵季平的影视音乐正是用众多这样的声音抽象和升华出来的中华民族文化精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