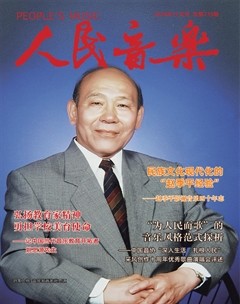找季平从未说过自己有什么音乐哲学。但他曾言及语言、绘画与音乐表达哲学命题的不同,以为要理解哲学,最合适是音乐,要与天地对话,有更大想象空间,音乐最好。为什么?抽象。抽象就能普遍。这便已是哲学思维。
音乐必与哲学相关,而有对立、转化、展开、衍生、分解、综合,理性与非理性、感性与非感性、逻辑与非逻辑、人生与价值等。无人则无哲学,亦无艺术,更无音乐;无情也无哲学,亦无人性,当然没有艺术;哲学穿透了声音,声音也穿透了哲学,作曲家哲学,更含在其声音组织———声况中。
一
“我是为音乐来的”,季平如是说。
这个“我”最需无伪天真,故其人格、心性、气质必浸入其创作中,而与他人发生音乐对话,展现出人本的深邃厚重、哲学上的主客关系。为什么季平的音乐能够有普遍性价值并被广泛接受? 在哲学上看,正在于其声音世界的人性本质:我就是你,你也是我,相互内在,相互进入、相互唱和,这便也是所谓人际间性,这个“间性”是相互镜像的,更因为声音的穿透力而深入人性本质,如中国哲人所颖悟到的,“其化人也速,入人也深”。如此,我们才可能理解作曲家笔下九儿悲切的声歌、蝶衣痛苦的戏文、秋菊坚韧的性格、荒诞旋涡里“活着”的福贵,大红灯笼下紧逼追促鬼气森森的复调女声,交响乐大写意里京胡的灵魂音声, 戏里戏外旷达又酸心的老腔,凄凉悲伤的洞箫曲,旷远萧索的筚篥声,含入了多少人的悲欢,多少世事人生! 再不要说他的那些古诗词歌曲,没有对人的理解,没有今人与古人的相互进入,何以能有这样优雅、细腻、深情的歌调?
有人说,他的音乐“至少影响了三代、超九亿人听过他的作品”。从哲学上说,作曲家与这九亿人有着相互进入、相互内在的超人际间性的关系,他们在情感、思想、生命的意义上相互证明着自己的人本价值,这是大写的生命精神,这也是中国哲学精神。音乐之不朽,作曲家之不朽,正在于“我-你-他”的相互进入,相互确证。当季平的创作歌曲被当成民歌,电影歌曲流行于街巷,器乐曲的旋律萦回于无数人的耳际,这便也有了生命共同体的意义和价值。其晚期器乐作品多有超越性、抽象性乃至于普遍性,让“英国人觉得这首作品是在讲述他们的故事,美国人觉得抽象化了他们的情感,贵州人觉得这就是我们地道的民歌流淌,陕北人觉得这就是我们的信天游”,表达的是超越性“大爱”主题,这是回归音乐、回归人自身,是人的自由精神的升华。
晚年的季平隐住在先辈留迹的道家圣山,以期亲接、亲嗅、亲吻父亲的灵魂。父亲内在于儿子,儿子进入了父亲。仿佛是他的协奏曲《庄周梦》,“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 ”这是一则关于他们父子相互进入而有灵魂对话的“梦”,这一梦便是一生。
人本,是赵季平音乐的底色。
二
人常言音乐缘情、多情、表情,中国艺术哲学则更强调情之所致必以理立, 无情则无人无艺术,无理也无人无艺术。情-理,对立而统一;理-情,统一而对立。涉及感性与理性,经验与灵感,以及超感性也超理性的边缘思维的神秘。如此,才可能有合适的声况,合理的情态。
情是动力,理是节制;情是归宿,理是内涵。
从“理”上说,季平明确说,“一种感性的东西,最后归结为理性”。我们细品他的音乐,无论是大型作品,还是应景小曲;无论是为戏剧舞蹈而作还是为影视配乐,他绝不做多余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