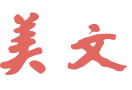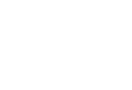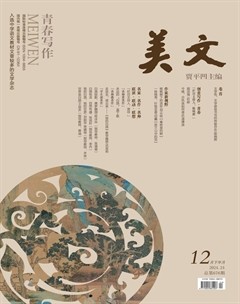这个中秋节,我和我家先生是在一棵古老的核桃树下度过的。
这是一棵一千三百岁的寿星树,矗立于秦岭南麓、洛水之源的洛南古城。树身雄浑粗壮,需四五个人牵手才能合围。离地一人高的位置,主干一分为三,三根粗细相当、并驾齐驱的巨杈,直冲云霄。然时光无情,许是虫害侵扰,致其中二杈已呈颓势,庞大的树枝梢头,仅有零星的枝叶在风中轻轻飘摇,末端皆有人工修剪治疗的痕迹,也有人工加持的拐杖支撑。
缀有绿叶的第三根枝杈,却出奇地繁茂。粗犷的枝干上,大大小小的枝条向四面八方伸展出去,枝又生枝,枝枝密生碧叶,共同编织出馒头形的树冠。从某个角度望去,茂密的树冠完全遮挡了身后的枯枝。叠翠的枝叶,以磅礴之力挥洒着生命的热情与活力。看起来整棵树丝毫没有老迈之感,仿佛它们并非一棵树,仿佛其他两个枝杈里的营养,都汇聚到了这里。
在单反镜头里,我看到了隐在枝叶间的核桃,一颗、两颗、无数颗,它居然还在结果子!并且,果实累累。先生说,这棵核桃树产量最高时可年产一千公斤。1980年全国干果考察团专家来此考察,这棵芳龄千年的核桃树因为树体高大、枝叶繁茂、产量高且稳,在全国罕见,被国家林业部确定为“中国核桃王”。
“瞧这‘核桃王’,不是民间传说,而是有官方认证的。它还是特级保护古树,是洛南核桃的地方名片。不过,在它眼里,所有的荣誉,只是身边往来穿梭的风吧,它的最高荣誉,其实是时间。”
先生的老家在商洛,从小在核桃树下长大,每每提及核桃树与核桃,言语中总弥漫着喜悦与深情。耳濡目染,结婚三十年,我也渐渐喜欢上了核桃。
记忆,沿核桃树溯流而上,回到我和先生相识的初期。
婆婆躺在蓝白格子的床单上,月白色的被子下,她的身体看上去很轻很小。
看见我和他进屋后,婆婆挣扎着起身,可终究没能如愿。她缓缓握住我的手,目不转睛地望着我,笑容逐渐爬满了脸庞。大约一分钟后,她把手伸进靠窗的一个布袋里,等她再次迟缓地将手挪动到我的手上时,我的掌心里,多了三枚核桃。
窗外,高大的核桃树,洒下斑驳的光影,枝叶间知了的声线又细又长。大暑天,房间里丝毫感觉不到热,与一百公里外的西安相比,似两个世界。
这是三十年前,我第一次去商洛见先生家人的场景。一个月后,婆婆离世。三枚核桃,将婆婆的爱封印,定格在那个夏日的午后。
大学毕业,我分配到西安一家研究所上班时,硕士毕业的他在所里上班已一年。周末,他常约我一起看电影、爬山、逛公园。等我俩确定恋爱关系时,才知道他的父亲已故去多年,母亲正瘫痪在床,已无法正常使用语言。他有一个哥哥,在铁路系统工作。其时,婆婆在老家由嫂子照料。
结婚后,逢年过节,我们都会回到这方院子里。
核桃树粗壮,枝探四方,树冠笼满了整个院子,甚至遮了西屋大半个屋顶。满院子的绿,像呼吸,令人舒坦宁静的呼吸。先生说自他有记忆起,这棵核桃树就在这里,是父亲还是爷爷栽的,他也说不清楚了。
这棵树很少生病,年年结核桃,核桃皮薄、仁饱、味香。
一种美味的生成,必有众多成因。先生老家地处秦岭商洛山区,光照足,雨量适,土地肥,完美契合了优质核桃生长的诸多条件。
婚后第一个春节,挨个走他家亲戚,每到一家,端出来招呼我们的糖果盘里,一定少不了核桃。有两家亲戚端出来的果盘里,只有核桃。
好多个傍晚,和先生在村子里转悠,碰到的最多的树,是核桃树,房前,屋后,河岸边,都能看到核桃树工整的奇数羽状叶子,还有,叶子上根根分明的平行叶脉。村子上方,始终氤氲着核桃树特有的气息。
去爬村子旁边的小山,遇到过核桃林,也遇到过很多散生的核桃树。
先生说,山里散生的核桃树,一般是喜鹊的杰作。喜鹊聪明,想吃核桃却鹐不破核桃壳,就先把核桃埋进山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