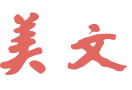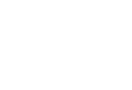男子不羁地盘坐在一块清凉的大石上,吐出:“女娃,今儿年芳十几?”
如玉一样温润的语调,如石一样顽固的形象。
说来又与你何干?心里暗自想着,哭笑皆不是。姑娘家是不能喜形于色的。
见男子摇了摇头,眉毛拧巴,再次开口:“未若同心言,一言和同解千结。”
女孩走近了些,一袭薄的青衫,以竹为友,以鹤为妻,蓄着盛唐诗人特有的胡须,眼中含着碎星子。
轻捏一壶酒,欲饮之。
男子竟是有些眼熟。她打量着他,她识出了他,韦左司。
女孩两步上前,小腿蹬着,手臂挥舞得张狂,指尖指向三郎,嘴里嘟囔。
“春潮带雨晚来急……”
“野渡无人……”左司回应的声音愈渐模糊,直至杳无声音。
她咕咚一声跌进了松林缭绕的原野,翠色的丛林将她环绕,针状的松尖扎进皮肤。
“舟自横”的景象未曾见到,也没有松针刺入肉身的疼痛。翻了个筋头,软滑得像是蜜熬出糖的溪流。原来——一觉醒来还在针织棉花被上。
此个女娃,乃江苏一人。可本地并不这么称呼少女,他们会叫姑娘——没有娃儿、丫头亲昵。
没有立即想到这点,的确是女孩的疏漏了。倾心唐诗也只因《滁州西涧》中的两句诗词、一段景致。
日暮黄昏,余晖懒懒洒泻。春雨下得散漫,缠绵悱恻,无所穷尽。西涧的水势兀地突增急湍,暴徒一般痴狂魔怔。
荒凉的原野上掺杂着凄苦月色,更加冷清萧条。世间万般无一可赏,终其一生百无聊赖。
山穷水尽之处,我徘徊,我流浪,我定睛看到一只乌篷小船。
柳暗花明下,无所谓波涛翻涌,唯有舟子悠闲地横斜在河面上,气定神闲。
反复玩味间她悟出了禅意。天机动,抚皱千年顽石。从江苏到陕西,驾车驱驰,车马劳顿,十一个小时,清晨到星夜,一路不尽变幻的风景。
女孩留恋那个水袖善舞的温婉都市,更向往步步回眸,流转千年,永不褪色的十三朝古都。
街道上有翻修的路,蓝铁板围着,车辆也因输水管道割裂了一半而堵塞不通。女孩的父亲面露愠色,积压火气,声音先变形:“这可要不得,节奏甚慢。这城市好到哪去,捞到了我姑娘?”
遥想填下志愿的那刻,思绪万千,如决堤之洪。
也许,一座城,可以埋下诗的香骨。仅此一见,擦肩百世。寂寞的生命咏叹,缓慢的唯美节奏,幽幽地铺开,直吟得地迥天远。独怜幽草涧边生,衣香人影太匆匆。能够遮蔽你真性的只有你自己罢了。
你是否还记得,那年花开的时节,我们相遇在这座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