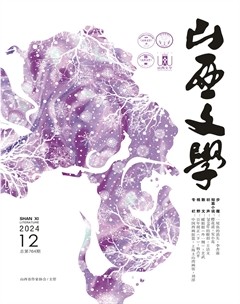去年八月中旬,突然接到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自报家门说他是中央电视台某个节目组的导演,想加我的微信方便联系。早在几个月前,忻州市委宣传部发来一个函件,内容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人类的记忆——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纪录片节目组近期将赴保德,指定要我参加拍摄。这是一个将要在央视中文国际频道首播的重点节目。如此重大的任务,让我这个向来一看到镜头就发怵的人很是紧张了一阵子。随后恰逢疫情肆虐,节目组未能成行,此事便搁置下来。没想到一晃过去大半年,节目组还是要来了。
这位导演姓祁,我称他祁导。祁导通过微信告知我说,他们这个节目组负责纪录片《人类的记忆——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系列之《长城》的摄制,从河北出发,一路拍过来,预计九月初抵达山西,问我是否有时间参加。在得到我肯定的回答后,紧接着他就和我沟通拍摄内容。节目的主题是长城,背后探讨的是长城对我们国家多民族统一的形成以及对民族精神的塑造,而走西口就是长城内外民族融合的例证。节目组让我前往杀虎口之类的关口拍摄一组镜头,同时希望我提供表达走西口文化的二人台、民歌,或者保德当地的饮食随着走西口和内蒙古相融合的一些风俗习惯。
大概是受到一些影视剧的影响,不少人片面认为“西口”就是专指杀虎口。其实,广义地说,“西口”泛指山西、陕西、河北、河南、甘肃等省长城上的各个关口,从任何一个关口走出去前往内蒙古,都可以说是走西口。现在正好遇到这样一个契机,我便把这个观点告诉了祁导,同时告诉他说,其实走西口最富代表性的是山西的河保偏(河曲、保德、偏关)三县和陕西的神府(神木、府谷、榆林、横山、靖边、定边)六县。因为走西口的本质就是逃荒谋生,地处黄土高原黄河两岸的晋西北和陕北历来分外贫穷,出于和内蒙古地土相连的便利条件,走西口高发于这一带是顺理成章之事。同时引以佐证:第一,“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这首家喻户晓的民谣说明河保偏一带的人一直是走西口的生力军;第二,二人台这种戏剧形式诞生于河曲,传统剧目《走西口》一直以河曲为正宗;第三,河曲话作为口里的“标准话”至今在口外盛行……尤其山西的河保偏人走西口要先渡过黄河,因此可以说这是一条“走西口”的黄金水道,也可以说是一道“水西口”。
可能是“水西口”的提法引起了祁导的极大兴趣,他闭口不再提邀请我前往杀虎口拍摄的事,饶有兴致地和我探讨起拍摄“水西口”的事来。我给他提供了一个采访对象,走西口的后人杨二喜先生。杨二喜祖籍保德,出生在内蒙古,改革开放后,凭借自己的艰苦奋斗创建了一家规模庞大的民营企业,是走西口后人中的佼佼者。因为一些渊源,我和他结为忘年交,一直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祁导听后,当即心念一动,一个拍摄计划冒了出来,即我从保德出发,沿着昔年的西口古道,“重走”一回西口路,去往内蒙古探访老乡杨二喜。这个计划和我的构想一拍即合。我随即打电话和杨二喜联系,在征得他的同意后,这个计划就基本敲定了。
九月一日中午,节目组人员驾车来到保德,下午就紧锣密鼓开始拍摄。当天的拍摄对象有两人,一位是我,另一位是陈秉荣。陈秉荣先生年逾八旬,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民俗专家,对走西口的历史了解很深,我在创作长篇历史小说《西口,西口》的时候没少参考他的研究成果。县委宣传部特地推荐他参加这个节目的拍摄。
下午三点,我来到县文化馆的民俗陈列厅,这是提前联系安排的拍摄地点。在这个充满文化气息的地方,我和节目组的人员会了面。祁导身形颀长高大,为人低调和蔼。他告诉我说,去年他接到这个节目后,就构想到了走西口这个内容,随后在网上发现我的《西口,西口》正在发行宣传,了解到这是一部结构宏大、史料翔实的书写走西口历史的文学作品,同时从作者简介里看到我是山西保德人,于是特意通过忻州市委宣传部邀请我参与拍摄。接下来他给我介绍了节目组的其他成员,其中有第二导演李导和摄影师司老师,一行共五人。
节目组的人员忙忙碌碌,不大工夫就把场景布置好了。陈秉荣先生还没来,于是决定先拍我。我在镜头前坐下来试镜。所有的人都在忙着做最后的准备,只有李导无事人一样坐在我的面前,和我聊开了闲话。李导刚刚三十来岁,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是这个节目组最健谈的一个人。因为是闲聊,我也不怎么拘谨。我们聊着保德的历史建制、地理环境,最后聊到沿着县城流过的黄河。我不假思索地告诉他说,过去保德的黄河河床宽阔,水流汹涌,可谓声势浩大,后来在上游建起几座大坝,水流得到控制,水位不断下降,以至在两岸出现了滩涂。现在咱们所处的位置,三十年前就是河道的中央……过去,黄河上没有桥梁,两岸人往来全靠木船摆渡,走西口的人也必须乘船渡过黄河,才能踏上西口路……
不一会儿准备就绪,拍摄正式开始,祁导接替李导坐在我的侧对面,以采访的形式向我提问。祁导的问题分为若干个,不外乎就是走西口的起因、过程和结果。这些问题,我在创作《西口,西口》时就仔细研究过,这些天按照拍摄要求又重新组织了一篇腹稿,加上刚才李导和我闲聊,让我几乎已经适应了这种问答形式,因此回答起来也算比较顺畅。归纳一下,内容大致如下:清朝建立后,随着一段时间的休养发展,中原地区人口迅速增长,土地兼并严重,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再加上自然灾害频发,民不聊生。山西、陕西、河北、河南、甘肃等省的贫民被迫无奈,纷纷跨过长城,走出口外,进入内蒙古地区谋生。一代又一代的汉人前赴后继奔赴口外,主要从事农耕生产和手工业生产,也有部分从事商业贸易。他们的足迹遍及鄂尔多斯、乌兰察布、巴彦淖尔和呼和浩特、包头等内蒙古中西部地区,最远的向西可达新疆,向北可达当时中俄边境的恰克图。其中有人春去秋回,有人扎根落户。经过三百多年的延续,逐渐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移民队伍。有资料显示,仅在口外定居的河保偏三县走西口的后人,总数就和现在三县的人口相当甚或超过更多。走西口融合了汉族的农耕文化与蒙古族的游牧文化,改变了内蒙古地区单一的经济社会结构,打通了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的经济和文化通道,带动了北部地区的繁荣发展,推动了汉族和蒙古族两个民族长远的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