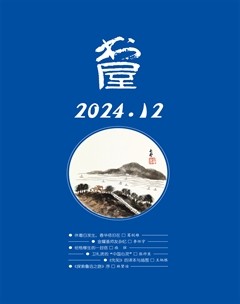一
1939年至1946年,马一浮在复性书院培养学子、刻印书籍。1946年3月,他离开乌尤寺,准备回到杭州,复性书院也一并迁走。
和马一浮随行的有三十多人,加上各种行李,一条大船载得满满当当。马一浮在重庆停留近二十天,访亲探友,依依话别。他的一大堆行李,由武汉大学教授张真如安排,拜托嘉乐纸厂董事长李劼人,寄放在海棠溪盐店湾的嘉乐纸厂重庆分公司房舍中。
李劼人给张真如写信,表示会好好接待这位国学大师,并吩咐秘书处致函重庆分公司,要求他们一定办好这件事。在李劼人的私人收藏中,有一幅马一浮的隶书立轴,内容是晋代傅咸的《纸赋》:“廉方有则,体洁性贞。含章蕴藻,实好斯文。取彼之弊,以为此新。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能幽能显。”马一浮以《纸赋》赠予嘉乐纸厂董事长李劼人,寓意深长。
李劼人是成都人,原名李家祥,生于1891年6月20日,中学时代就大量阅读中外文学名著,特别会讲故事,在同学中是出了名的“故事王”。1912年,他发表了处女作《游园会》,他是一个极具天赋的小说家。但是那时人们对他知之甚少,我也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读他的《死水微澜》。但他经营的嘉乐纸厂很有名,我小时候使用的纸张很多就出自嘉乐纸厂,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破产之前,该厂是乐山最大的机器造纸厂,而李劼人就是创始人之一。
李劼人的《死水微澜》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现代历史小说。我很惊叹他能够那样写出四川的近代历史,书里面对社会生活、风土人情、历史画卷的描绘,不是一般人所能够驾驭的。又泼又皮的四川话是极大的亮点,非常生动,那是一种独特的语言味道,要是换成另外的语言就少了那种味道。
李劼人的很多随笔,写老成都的民俗,写得很透,写出了老成都的韵味,他是能够代表成都的一位作家。
二
1925年,李劼人从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在《川报》当编辑,发现去国四年后,报纸还是老面孔,印刷的纸张——手工制造的土纸仍然粗糙低劣。由于用不起洋纸,四川没有一家机器造纸厂可供应价廉物美的新闻纸。
一天,他和报馆同人宋师度闲聊,面对发黄的报纸,突然说起创办纸厂的主意。两人越说越兴奋,一致认为须“喊得出几位有力量的热心人来,开上一个机器纸厂”。这个偶然出现的新奇想法,改变了李劼人的人生道路,后来他的命运便随着工厂的沉浮而起伏。
要办纸厂,就要有懂得造纸的人。李劼人想起了熟识的王怀仲,他是四川眉山人,在法国专门学习造纸。当时王怀仲已回国,正在江浙一带考察机器造纸厂,调查国内造纸状况和生产技术水平。他早有回国开办纸厂的打算,与李劼人、宋师度的想法不谋而合。李劼人还计划造纸厂建成后,“将来经理一席,即由我担任,而制造一事则一概委之老王”。
经过筹股会,筹得原始股本五万元,1926年6月,四川第一家机器造纸厂在乐山正式成立,因为当地有煤炭,有碱厂,有草料,原材料不缺。纸厂大股东之一陈宛溪是乐山的大实业家,创办华新丝厂,推广桑蚕新法,对四川桑蚕业的贡献很大,还在乐山做过不少善事。他大力支持李劼人创办纸厂,以《诗经》中“嘉乐君子”命名嘉乐纸厂。这个名字,也与乐山的古名嘉州相洽。
1927年1月20日,嘉乐纸厂召开股东会,选举陈宛溪任董事长,李劼人任协理,王怀仲任厂长。
这家刚开办的工厂,一时间欣欣向荣。成都的报馆正缺纸,争着向嘉乐纸厂订货,产品供不应求,股东们兴高采烈。但由于价格和供应要求苛刻,无利可赚,销售日渐欠佳,大家又变得心灰意冷。李劼人在成都联络买主,负责收账,帮忙汇兑,解决一些运输的琐碎事情。
因为前期工厂几乎没有收益,为了养家糊口,李劼人一边为嘉乐纸厂出力,一边在成都大学教书,同时在《新川报》兼职,还做些翻译工作。那是他比较辛苦的一段时期。
1929年,嘉乐纸厂连续几次停工。第二年刚一开头,陈宛溪突然病逝,让嘉乐纸厂的前途更加渺茫。过完春节,王怀仲召集股东开会,准备破产清算,没想到股东们觉得心有不甘,于是又筹钱,让工厂重新开工。人事调整时,李劼人任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