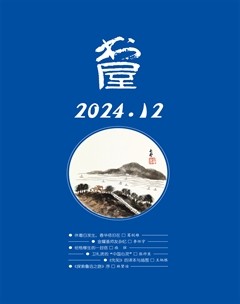一
1994年农历7月30日,一向寡薄病弱、八十九岁高龄的台湾著名高僧印顺法师在离开大陆四十多年之后,回到大陆,巡走当年出家、学习、教学等驻锡之地。此番意外之旅,乃是因为法师不能忘却曾经求法修学的因缘。
8月3日下午,法师到达宁波,先去了当年受戒所在的天童寺,又去了阿育王寺,再到奉化的雪窦寺。去雪窦寺,法师特意准备了一束鲜花,敬供太虚大师的舍利塔。法师在自传《平凡的一生》中说:“雪窦寺是虚大师舍利塔所在,也是我主编《太虚大师全书》(以下简称《全书》)的地方。可惜虚大师的舍利塔,已被毁灭了!只得将鲜花遥敬。”
法师性格平实,害怕礼数,自言不懂艺术,没有艺术气质,出了家,便将身心安顿在三宝中,不觉得有什么感情需要安放。法师自述:“离了家,就忘了家;离了普陀,就忘了普陀;离了讲堂,就忘了讲堂。如不是有意的回忆,是不会念上心来的;我所记得的,只是当前。”那么,这一束突兀的鲜花,定是法师念上心来的凭证了。约半个世纪前,抗战胜利后,1947年3月6日晚,法师从重庆辗转来到上海,礼谒太虚大师于上海玉佛寺的直指轩。“大师为教的心境,当时非常不顺适。”10日早上,因要到西湖一游,法师向太虚大师告别。太虚大师说:“就回这里来吧,带几枝梅花来!”哪知这是最后的礼别,不几天,大师匆遽示寂,舍报往生。法师得到电讯,特地折了几枝灵峰的梅花,带回大师灵前供养。
太虚大师喜欢鲜花,这大概印入了性格平静的印顺法师的脑海。1994年的大陆之行,最后一程,8月21日抵达香港,法师又带了鲜花,往芙蓉山礼拜太虚大师纪念塔。两次奉花供养,这在法师一生中颇为少见,或是仅有。
二
太虚大师与印顺法师同是出生并成长于钱塘江北岸的浙江海宁,大师年长法师十七岁,出家因缘各别。大师爱惜僧才,对法师慈悲关切,但二人在故乡却无缘相遇。法师第一次礼见大师是在奉化雪窦寺,时为1934年新年,法师二十九岁。法师回忆:“第一次礼谒大师,请求开示。大师只是劝我多多礼佛,发愿,修普贤十愿。我没有理解大师的用意,也就不曾忠实履行。现在想来,大师的慧眼,是何等犀利!他见我福薄障重,非多修易行道,增长善根,销除宿业,将来是‘孤慧不足以弘法’,弘法而必招障难的。”
法师在自传《平凡的一生》中时常感叹不可思议的因缘。日寇全面侵华前夕,一种不自觉的因缘力使法师东离普陀——从武昌到四川,远离了苦难,不至于遭受沦陷区生活的煎熬,而能进入一新的领域——新的人事,新的法义,深深地影响了随后几十年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