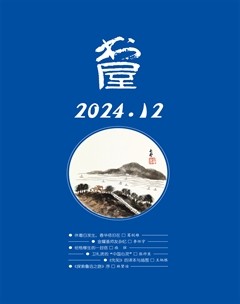2024年6月30日清晨,我在赶往机场飞去西北的路上意外地得知:刘桂生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已于29日中午不幸仙逝。顿时,我感觉心情很沉重。如今,清华“史学四老”又走了一位。这无异于又一次的清华学术之殇。
犹记得好些年前,清华曾云集一批老清华出身的年高德劭的人文学者,仅历史学科就有多位蜚声世界的老前辈。这些前辈各具特点,各有专长。其中,何兆武、张岂之、李学勤等几位从老清华毕(肄)业后,于新中国成立初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侯外庐先生麾下工作。他们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已广受瞩目,被各方寄予厚望,晚年从原单位离退休后又都陆续被聘到清华工作。其中,刘桂生先生是更纯粹的“老清华”。从清华毕业后,他几乎一直都在清华工作,迄今已有五十余年。这与钱逊先生的轨迹相若。及至改革开放之初,刘老先生就已成为清华史学的元老,培育了大批英才。他继承和发扬了老清华史学的精义,贡献了诸多学术力作。
老先生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中外交流史(特别是中欧交流史)及中共党史等,他对历史理论、比较文明史等方面亦有涉猎并有出色表现,蜚声遐迩。他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就在近代史研究、中法交流史料选编、清华校史撰研等方面,取得了标志性的成就,其中精品甚夥。这一系列精品的完成,使先生在圈内享有盛誉,有口皆碑。老先生在思想文化史方面所做的一系列开风气之先的工作(特别是对严复、梁启超和陈寅恪等重要学者或思想家的研究),在海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老先生引领下,校内一批学者集中倾力于该领域的研究,持续推出了一系列高水平论著。以全球眼光观照中国问题,在国际视野下开展深度的思想文化史、中外交流史的跨域研究,是改革开放以来清华史学极具特色的一部分。在学术倾向与治学风格上,注重“原料”、史论交融、科际整合、务求彻底、国际眼光,这些几乎已成为清华近代史研究的“家法”。而这也正是当年陈寅恪、蒋廷黻、邵循正等前辈的一致追求。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北大中国近代史学科带头人陈庆华教授(四十年代曾在老清华任陈寅恪先生的助手)逝世后,该学科的师资力量大受影响,出现了博士生导师的空缺。经两校协商后,老先生于1993年应邀移席燕园,担任博士生导师。老先生由此成为此后数年间北大历史学系和清华社科系在中国近代史学科领域唯一的博士生导师,成为北大、清华的双聘教授(可能也是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文史领域唯一的北大、清华双聘教授),指导两校研究生、博士后。1994—1996年,他在北大开设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专题”“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吸引北大、清华历史学系研究生共同听课,加强了两系合作,形成了优良传统。同时,老先生还指导了国内外一批优秀的访问学者及外国留学生。这正好是他的老师邵循正先生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所扮演的角色。邵先生指导出了巴斯蒂夫人等杰出学者,而刘老先生则指导下了德国学者、维也纳大学副校长魏格林教授及美国汉学家、中央华盛顿大学副校长林如莲等。此外还有若干来自意、韩等国的青年,他们日后大都成为国外新一代汉学家。
及至北大近代史学科新一代的学术骨干成长起来后,老先生于1998年重返清华。此时老先生已年近古稀,随后正式退休了。在此期间,老先生还因其世界瞩目的成就,多次受邀出国交流、讲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就曾应法国外交部之邀,赴该国多所名校和学术机构讲学,在当时可谓是中国学术“走出去”的先行者;九十年代,他又两度受聘担任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研究所客座教授,并讲授“中国古代思想史”和“中国近代思想史”课程。此后,他又数次赴德讲学。
从学术辈分上说,我是刘老先生弟子的弟子,这种渊源不能算疏远。再者,我长期住在清华园,先生家住一墙之隔的蓝旗营,相隔甚近。我们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园子里十余年,但接触的次数不算很多。然而,每次交流他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头几年中,我对老先生的动态时有耳闻,但仍是仅闻其名,未见其人。后来,由于很偶然的一次机会,才开始真正接触到老先生。2006年秋,《清华史学》创刊之际,需要请系内一批老前辈题字以示支持,我受托负责接洽何兆武、张岂之、刘桂生等前辈,于是通过电话与老先生取得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