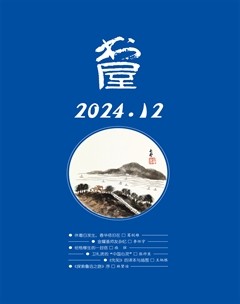若论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艺术家中,谁能迥异于现代世界的审美大潮,引发背景各异的欣赏者抛开群类之异化、个体之成见,又能紧紧抓住无数观画者的心灵,当首推赵无极。
在赵无极的画展中,往往能见到观众如同古希腊酒神狂欢节上的萨蒂尔信徒一般,融入了酣畅淋漓的纯艺术之狂欢。赵无极的画中有一股灼人的魅力,恐怕远不是因其自身命途之多舛而使人共情而珍惜,亦非绘画内容的多元丰富而可供品咂回味,而更应该是源于他画作中一种“生命-哲学”的境界、一种“非今非古”的形而上概念之原象与“亦今亦古”的实在界之生命气质的珠联璧合。诚如他本人在《绘画是我的生命》中所云,“如果说,一个人一生中,必须做些让自己发狂的事,那么,绘画便是我的全部生命,也是我终生去追寻的唯一凭借……”庖丁目无全牛而游刃有余,画师解衣般礴而脱略形骸。赵无极的艺境有两种特质:其一,忘乎所以、几近癫狂的艺术生命;其二,颠沛坎坷、怅然若失的物质生命。两者有着互证互发的关联。
一种哲学的绘画首先起始于艺术家“自画像”的创作。所谓“自画像”,就是把自我对象化、客体化、疏离化,放置在一个可供静观的距离下加以反思。早在留法前,赵无极画作就展现出这种自我审视与自我观照的倾向。他绘于1948年的《杭州风景》即是去国离乡前夕之作,颇具“自画像”的象征意味。该画的主题是杭州艺专西迁时期临时搭设的一处草舍:在逸笔草草的建筑外景交织之处,一把长椅占据了画幅的视觉中心,上有“林界”二字;画面左侧蓬屋中的人物仿佛正在作画。此处并不需多么充沛的想象力和画史知识就可以猜到,这是对画家本人写生场景的描绘,而“林界”指的是敦请亦师亦友的林风眠先生加以评价的意思。
在同样完成于1948年,并被认为是赵无极初到法国后的画作《无题(葬礼)》中,是另一种静观与反思。画家在“秋气肃杀”的氛围中描绘了送葬者惜别亲人棺椁的场景,很可能源于童年时随父在南通生活的经历。画作对于树木的刻画和整体设色,符合一种江南水乡的审美气质。因此,这幅画首先必须是回忆性质的,是一种童年经历与丧子苦痛在异乡之梦中的再体验。毫无疑问,作品的基调是哀伤痛苦的,但赵无极在对现实场景的象征性再现中完成了一种超越:死亡作为生命断裂的冲击性与恐怖特质被消解在沉思的静谧之中。
赵无极晚年的几幅作品都表现了一种“洞观”的视角。抛去在光影色彩应用上对塞尚、透纳等西方画家的学习和在具体技法上可能存在的对张大千一脉泼墨泼彩山水的借鉴,这几幅画作都是对“观照”这一主题的纯粹再现。“洞观”在中西方语境下都有着深刻的内涵。古希腊的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引出洞穴之喻,洞中人摆脱洞内阴影的纠缠而向外试探的目光,是反思与启蒙的先兆。中国文化传统中“洞观”本就是远见与深察之义,如王国维“唯非常之人,由非常之知力,而洞观宇宙人生之本质,始知生活与痛苦之不能相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