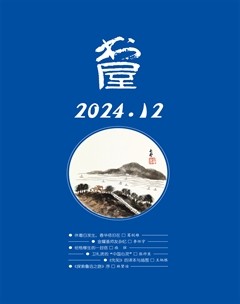之十八: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不一样的南方
“耸立于连绵高沼地间的由砂岩铸就的城市;城墙阴暗处如脉石英矿的残雪;港口区鳞次栉比的木屋,上方的山坡光秃秃的,寸草不生;被风吹乱的云朵,被染成玫瑰色和灰色,这是严寒和暴风雪将要来临的征兆……”
停下手头正干着的活,翻开英国文化学者彼得·戴维森的《北方的观念:地形、历史和文学想象》(三联书店2019年版,以下简称《北方的观念》),开头呈现的,就是苏格兰艺术家达尔齐尔名为”北方的观念”的艺术品。这个艺术品很简单,其实就是一个红色的指针,永远指向遥远的北地。所引的这段话,就是作者对北地的风景的描述。也是这个描述,让人想起著名的电视连续剧《权力的游戏》里的临冬城的风景:阴郁、冷森、荒凉、暴烈,亡灵与异鬼出没之地,却又散发着炉火的温暖……
初翻这本书,我第一时间想表达的是,看来人类的心灵是完全相通的。《北方的观念》可以说是以北欧民族为主的一支乡愁曲。人们无论身在何处,甚或一直生活在北方,却仍然思念、想象北方,甚至嫌弃、惧怕北方。这种情愫,与中国人对南方的执念,几乎没有区别。
正如“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不一样的北方”,每个中国人心中也都有一个不一样的南方。
在南方长大,后来却在北方觅食,且有一定写作能力的人,思念南方永远是笔下一个永恒的主题。春天铺满田野及河湖边的紫云英,悠闲地啃着刚勃发的嫩芽的水牛;夏日炽热太阳暴晒下墨绿的植物散发出的浓浓清香,睡在大树底下蝉鸣声里的小男孩;秋天落日下江边瑟瑟摇摆的芦荻,如水月光下突然受惊飞起的鸦雀;冬日寒风中怒放的蜡梅,一家人围坐的栎树木炭暖炉中时隐时现的火红焰舌……南方有咿咿呀呀的戏曲、壮怀激烈的鼓书、神秘莫测的“抬老爷”以及蜿蜒奔放的舞龙,更有慈祥的外婆、手指白皙而细长的书生、甩着两条大辫素面朝天却宛若天人的少女。当然,这个少女后来给他的心痛,也让他分不清自己到底是思念南方,还是思念当年迷惘的青春。
思念其实本身是一种思而不得或求而不得的无力感。不过,历史上曾有一个牛人,从江南到塞北任职之后,按他记忆中的南方,复现了江南盛景。这个人就是明朝的朱元璋第十六子庆王朱栴。洪武二十六年(1393),朱栴奉诏自南京赴宁夏,成为掌管此地的藩王。宁夏有“黄河之襟带东南,贺兰之蹲峙西北”的独特的地理优势,加上历史上江左之人的不断迁入,早在东汉时期,就享有“塞上江南”美称。后世战乱频仍,至元代已几乎失其美誉。自幼在南京长大的庆王,一直忘不了记忆里的江南。来到宁夏后,他一方面指挥军民按江南景象种树开渠造景;另一方面更为积极地迁入江南百姓,其中包括诸多江南才俊,使得宁夏一时间在山川形胜、亭台楼阁、人文昌盛方面,与江南几乎无异。庆王余生再未回到江南,但却在不是江南胜似江南的“塞上江南”中完成了他对南方故土的回归。
不是所有人都思念南方。我的一位北方文友,就一直视南方为“畏途”。这位陕西长大的文友曾在长沙求学四年,始终无法适应南方常年潮湿的气候。在记忆里,这座城市可以连续两个月阴雨天气,至多偶然在云层里见太阳探了个头。被子是潮乎乎的,与换洗的衣服一样,几乎没有干爽的时候。而长沙的物候给他的印象则是四季如一的阴森的滴着水的肥绿。也因不适应气候,头两年,一到春夏之交,他身上就会长出奇痒无比的小水疱。由于对南方的恐惧,大学一毕业,他便逃也似的回到北方,甚至拒绝了一位他暗恋了很久但却生长于长沙的女同学的表白。因为他知道对方是独生子女,不会离开南方。至今,他对南方夏天的潮闷、冬天的湿冷仍心有余悸,不过在想起当年的那个她时,心里还是充满了悸动与怅然,似淋着南方的雨。
不过,一个出生于南方的青年诗人——我的安庆同乡海子,三十五年前在北方那座叫德令哈的小城,写下了平生最美的一首情诗:“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姐姐,我今夜只有戈壁/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除了那些路过的和居住的/德令哈……今夜/这是唯一的,最后的,抒情。/这是唯一的,最后的,草原。/我把石头还给石头/让胜利的胜利/今夜青稞只属于他自己/一切都在生长/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空空/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从此,这个北方的无名之城以及这位城里的“姐姐”,就享有了南方的印记。
之十九:跨界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在学术上关注的焦点问题,就是社会公平。为此,我读过不少相关著作,并且写下了诸多文字。
当我翻读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历史社会学奠基人查尔斯·蒂利的专著《持久性不平等》(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时,我还是为书中条理清晰、简洁明了的论述所折服。特别是在见识了欧美一些学人云里雾里东扯西拉的文风之后,读蒂利的这部著作,看到熟悉的“首先”“其次”“再次”这种类似中文写作逻辑的文字,很有一种亲切感。
蒂利不研究一般性公平问题,尤其不去追问造成人类普遍不平等的原因,亦非关注同代人在“横截面”上的不平等,而是关注长期的、系统性的机会不平等如何影响到不同社会类别的成员之间的区别,以及这种区别的后果及其消除方式。也就是说,这部书正如其名,关注的是持久性的不平等。书中所讨论的“类别”,即性别、族裔、国界、阶层,等等。
书中用了四个概念来解释为何不平等会累积并传承。第一个概念是“剥削”。这里的剥削概念,是韦伯关于社会封闭理论与马克思剥削理论之间的跨界。韦伯认为,社会关系中形成的“配对”关系,如贵族/平民、男性/女性、公民/外国人、资本/劳动等,并非自然形成,而是人为划分出来的,并且依赖于广泛的社会组织、信仰与执行措施,被人为“封闭”在界限两边。更直白地说,这种配对构成的不同类别,是控制着能创造价值的资源的那部分人,通过这种区分,建立起来的社会封闭、排斥和控制体系,从而获得越来越多的回报。马克思则认为,依托一切在资源控制方面的不对称关系,来索取剩余控制权的,就是剥削。综合韦伯与马克思的观点,在该书中,一方利用不对称的资源控制权,将“对手”(配对关系中的另一类别)排除在价值分配之外,剥削就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