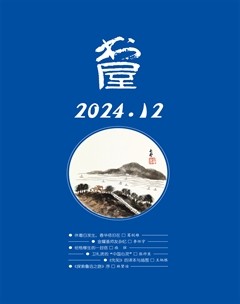“画屏山”的俊影从窗外掠过。“西陵峡!”导游一语,蓦地把我一段久远记忆撞醒了。
“画屏山”其实是我当年——五十余年前,对西陵峡山形的私下命名。那一年,船过三峡。瞿塘峡和巫峡,沿途都是高峻挺拔的苍郁群山。船近宜昌,进入西陵峡,山形山影陡然一变——每座山都有一面嶙峋的石壁,却似一个个被融融绿雾簇拥着而连绵不绝的彩色画屏,让我想起桂林山水中某几个如画屏般的山影。西陵峡——“画屏山”,便从此镂刻进我的记忆深处了。
“真的吗?宜昌,真的是你青少年时踏足过的旧地吗?”从武大会议转往三峡大学的一路上,同行友伴们一再如此问询。是的,它触碰到的,其实不单是个人的记忆,也是时代的一道疤痕、一脉心火。1972年夏秋之间,我十九岁,尚在海南岛乡间抡锄挥汗做知青。1971年大事件的发生,无疑是我辈青春行旅上的一道最深的刻痕。此前的纯真崇拜与蒙昧浪漫,一夕之间粉碎,一变而成众多的疑问与感叹。“中国向何处去?”是当年乡间知青的一个热门话题。于是,我便和一位同在乡间读书写作的好友相约,学古人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各自攒两年农垦兵团的探亲假(一年十二天,两年则可超过二十天),结伴渡海穿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俩规划好了旅游半个中国的路线——自雷州海峡渡海,从湛江出发,坐慢车穿越云贵高原,抵达山城重庆,在重庆坐客轮,自长江三峡顺流而下到武汉,再自武汉经长沙、湘潭返广州,最后返归海南。自然,这个雄心勃勃又有点异想天开的行程计划,在当时不但属犯傻犯狂,也算犯忌犯禁。我俩严守着出行秘密,同时也得从微薄的“农工一级”工资里一点点省攒下来出行的盘缠。春去秋来,日落月升,泪洗汗耕,好不容易熬到那一年秋天,几番折腾后请下探亲假而整装待发之时,那位好友忽然告知我:他临时怯阵了,打退堂鼓,不想与我出行了!
“——大家看,屈原故里秭归,就在对面河岸的高坡上。”导游一语,又把众人的目光引向了那片滚腾河水托着的迷蒙屋宇间。“因为三峡大坝建成蓄水会淹没秭归古城,当年把古城整体移到了对面那片岸坡上。”导游解说道。可以想见当年三峡工程的“牵一发而动全身”,沿江两岸城镇村宅的移民搬迁是一个何等艰巨的大工程。“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一时间,熟悉的《离骚》句子浮上心头,我又追念起过往人生那些“路漫漫其修远”的求索日子了。
如今追思怀想,我才意识到,老友临阵退缩的那一刻,是把我扔在了人生十字路口。艰难筹备了一整年的梦想之旅,难道就因此破灭吗?同伴怯阵止步,我就该放弃吗?!捏捏怀里揣着的两年间拼力省吃俭用攒下的七十块钱,我一咬牙就毅然决然地出行。开弓没有回头箭,必须做,必须走,我一个人也要完成这个逐梦之旅!
记忆如奔马,一下子跳到了十四年后的另一段生命之旅。因为有了1972年独行之旅的铺垫,1986年秋,在留学美国决意“海归”前夕,我打算安排一次只身上路的欧洲流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