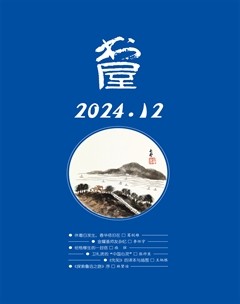记得十年前克厚兄路过开封,席间曾谈及他对经典的认识,说的都是些经典的重要性之类的话,而今他更关心的是如何解读经典。这让我想起多年前的往事。1985年,大学刚毕业的克厚兄背负简单的行囊到西北边陲执教,从此开始了几十年如一日研读经典的学术志业。面对纷扰的世界与熙攘的风潮,克厚兄始终坚守思想本位、学术本位,广泛阅读中外名著,以期对经典作出通识性、普遍性的解读,立志让古人的智慧照亮现代世界,力图以今人的眼光发现古代思想的价值。在古代经典中,他用力最深、所得最丰的就是《论语》。从文字考据到语义辨析,最后到思想解读,克厚兄的《论语句读》将两千多年前的孔子请到今天的世界,为我们呈现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思想对话。
用我们近来关注的人文语义学这一话语体系的视角来看,真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本来,人文语义学就意在“通古今”“究天人”。而且,我们在重视精英、文本的同时,更为看重“对话”。“一切历史都是对话史。”
文归正传,我们为什么要读《论语》?
孔子生于春秋后期,当时周天子权力衰微,天下混乱,诸侯争霸,以往的礼乐秩序逐渐被破坏。孔子因时而起,主张用仁、礼来重建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有人说,孔子“述而不作”,是个复古主义者。表面上看,似乎如此。但他在“述”的过程中也“作”了许多,最重要的就是将三代以来的文化内核总结为“仁”,提倡“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从“仁”之宗旨出发,去重建礼仪。在重建的过程中又有“损益”,即因时而变、因事而变。就此而论,孔子是一个以仁为本、尊重传统、尊重习惯、渐进改革的政治家、思想家。以仁为本,才是我们读《论语》的原因,用仁心来提升自己,用仁心来“立己达人”,用仁心来改革制度。
《论语》是孔子及弟子的言行录,关于其版本与形成过程历代学者已有充分的研究。从汉代到今天,关于《论语》的注本可谓汗牛充栋。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与人们对思想的追求,《论语》更成为许多人争相阅读的经典。因此,寻找合适的注释,也就成了重要的问题。钱穆的《论语新解》、杨伯峻的《论语译注》、李泽厚的《论语今读》、李零的《丧家狗:我读〈论语〉》、鲍鹏山的《论语导读》等是目前市面上较为流行的注本。其中杨伯峻、李零基本是文献学的路径,钱穆则在其注本中融入了许多宋学思想,李泽厚以哲学家的身份解读《论语》,鲍鹏山在“导读”中着重发挥道德的意义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