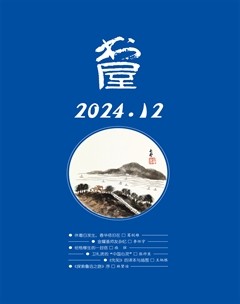一天,北京来电话,是一位女性的陌生声音。对方自称是出版社的编辑,王得后先生主编一部关于鲁迅的书,托她请我作序,特意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听说是王先生的事,话没听清楚,便应承下来。待书稿到了案头,才赫然看见“研究”二字。研究从来是学术圣殿中的事,我非学界中人,可有置喙的资格?
我确乎很早便开始读鲁迅,“文革”时有好几年简直离不开他的书。因为这些书的存在,我在艰难的岁月里获得生存的勇气。出于亲近的欲望,我陆续读了一批回忆录,也读了有数的几部研究著作,如《鲁迅事迹考》《〈两地书〉研究》等。等到《人间鲁迅》写作完成之后,阅读鲁迅的机会便大为减少,几近中断了。
接触中,得知鲁迅研究者集中于两部分人:一是政治家,二是学者。关于政治家,鲁迅早就做过演讲《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而学者,在他那里好像一直不怎么讨喜,而他又好像特别敏感于别人的评论,因此不可能不生警惕。直到临终,他谈到他所敬重的老师章太炎时,也都特别关注那身衣的“学术的华衮”。
王先生主编的《探索鲁迅之路:中国当代鲁迅研究(1949—1999)》(以下简称《探索》),让我重返这方面的阅读,填补了因多年怠惰而留下的鲁迅研究史知识的空缺。这是我至今见到的选材最谨严的一部鲁迅研究论文集,涉及范围广,包括哲学思想研究、作品研究、文献研究等。时间跨度也大,涵盖新中国两个时期。两个时期中间既有断裂,又互相衔接。作者有如上述,既有文艺部门的官员,也有一般学者,而学者更众。他们的研究,随着时势的推移,形成相对的两个世代。但是,无论如何新老交替,同处于一个体制的框架之内是没有问题的。
选文按时序编排,头三十年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全书以李何林开篇,内容是对毛泽东评价鲁迅的三个“家”——“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阐释。茅盾的文章为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而作,使用报告式的语言宣讲鲁迅,思路还是分前后期,肯定后期而否定前期。文章指出,鲁迅强调“国民性”的痼疾是“偏颇”的,对历史上人民的作用估计太低,忽视中国人民品性上的优点。其实,“国民性”的内涵是很丰富的,这种指摘何止于偏颇而已。其余几篇,除了王瑶梳理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之外,都是具体的作品研究。陈涌论《呐喊》《彷徨》的现实意义,工具是认识论的反映论,用的是文艺社会学的传统方法。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他和茅盾在文章中同时使用了从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那里抽绎出来的公式,颇有教条主义和机械论的味道。冯雪峰论《野草》,将《野草》分为三类——健康的、积极的、战斗的抒情部分,讽刺部分,空虚和灰暗的部分,并说这三个部分构成鲁迅思想上的矛盾,及其自我的思想斗争。他指出,矛盾的根源和本质就在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自延安整风以后,反对个人主义便成了在知识分子中开展政治思想斗争,也即“思想改造”的纲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冯雪峰借用“个人主义”的概念描述鲁迅前期思想和创作的“局限性”,回过头看,实在很有点讽刺喜剧的色彩。唐弢论鲁迅杂文艺术,说逻辑思维、形象思维,都没有什么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