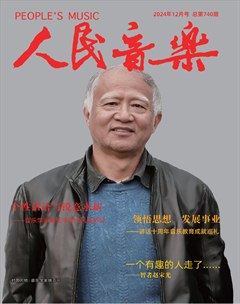赵先生走了!那天,田青对我说:“知交半零落”!我心中顿生凄怆。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再也没有这样有趣的人了! ”我伤心地说:“是的! ”
是的,他是个有趣的人,且他的有趣也是非常独特的。记得赵先生第一次进入我的视野,是读他的《数在音乐表现手段中的意义》和《关于3/4 音的律学假设》两篇文章,接着开始啃《论五度相生调式体系》。在读这些论著时,虽然感觉有难度,但其中的哲学厚度和方法体系,让我感受到脚踏实地的分量感,这给我一种确定的力量,让我有信心解决我所有的学术困惑。数年后,李正天先生问我,为什么会拜赵先生为师,年轻人不容易懂他。我半开玩笑地说:“我在黑暗中找到了光明。”这是最能表达我当时阅读后的感觉,于是我向西安音乐学院申请邀请赵先生担任我的导师。在经历了由于邮件不畅而产生的数月等待, 终于得到了赵先生的回复,并说知道我,看过我的文章。原来,我俩同在《中国音乐学》1991 年第4 期发表过文章。那是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 我是那期所有作者中最年轻的一位,而我和赵先生的文章内容是完全不同的领域,但他读了我的文章,并在几年后还记得我的名字以及读后的印象。他很高兴帮助我完成有关中立音的研究。我从此成为赵宋光先生的入室弟子。
第一次见面
1995 年4 月,我去机场接赵先生,飞机提前降落了。跑进到达厅入口,看见一位半大老头坐在长椅上,心想这位大概就是我要接的赵先生。一边心里想,一边脚步未停,继续往里边跑,还有零零星星的人从出口走出来,等到没人了,急忙返回到刚才经过的长椅, 半大老头仍然气定神闲地坐在那里。我上前问:“请问您是赵宋光先生吗? ”他立刻大声回答:“是的! ”我为数分钟前心中猜对了略感得意。我告诉他我看了他一眼,就猜到他是谁,他也非常高兴。回到音乐学院,他对每位前来拜访他的人快乐而大声地说:“她一见我就猜出我是赵宋光! ”他很喜欢这种心有灵犀的默契。
最奇特的授课
1995 年初夏,我们去陕北考察,这是赵先生为了考察黄河中游而提出的行走计划。车刚出西安城,赵先生就拿出一摞草稿纸写了一个对数的换底公式,让我做换底练习。就这样一路走一路上课,恢复了丢弃已久的对数知识, 在颠簸的车上进行演算,光演算纸就用掉一大摞,当到达陕北佳县时,我已经完成了论文中所有数据的计算。在赵先生一个接一个问题的密集轰炸下,我从招架不住而头痛欲裂到豁然开朗, 最后领略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快乐。后来阅读他那篇《黄河×草原:心底的情结》,我理解了他对技术细节的较真儿和环环相扣的设问方式。因为那是他用生命经历换来的认识:“(1956 年)那次经历中,我体验到了‘生命系于技术’的边缘境况。在一段岩石河床的峡谷中,船工们稍有不慎,就会翻船撞在岩石上。所以,每个人都绷紧心弦,一片寂静,虽然共计不过半小时,它却成了我一生永久的记忆,不停地教导我以高度责任感对待技术细节。”25 岁时一次震撼心灵的草原黄河之行影响了赵先生一生的学术道路,从中凝练出一个观念:要以高度责任感的态度对待技术细节,这最终成就了他在音乐形态学这个领域的理论建设,《关于3/4 音的律学假设》和《论五度相生调式体系》就是由这次人生之旅催生而成。
这次陕北之行于我而言,其意义可以比附赵先生当年的草原黄河之行,不仅开启了本人的系统性学术训练,明确了学术道路,也让我领会他“辩证逻辑形式化,形式逻辑辩证化”的学术构想,赵氏理论律学的表述体系中充满这“二化”。后来学习他每个领域的理论体系,都可以感受到这个构思释放出的学术能量。
壶口瀑布旁的黄河之子
陕北之行, 给我留下几个印象深刻的瞬间,这几个瞬间高度凝练地折射出赵先生的人生观和生活态度。他目标明确,为达目标不计荣辱。他希望连夜绕道去看一个在黄土坡面上植树的示范工程,但带队老师和司机都不愿意去。由于当时交通、经济条件所限, 这是赵先生第一次离这个工程最近,但错失这唯一一次考察机会,对他有关治理黄河的梦想、设想、畅想都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