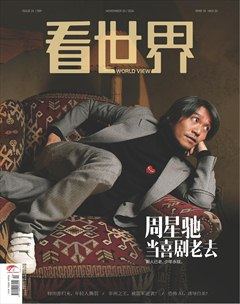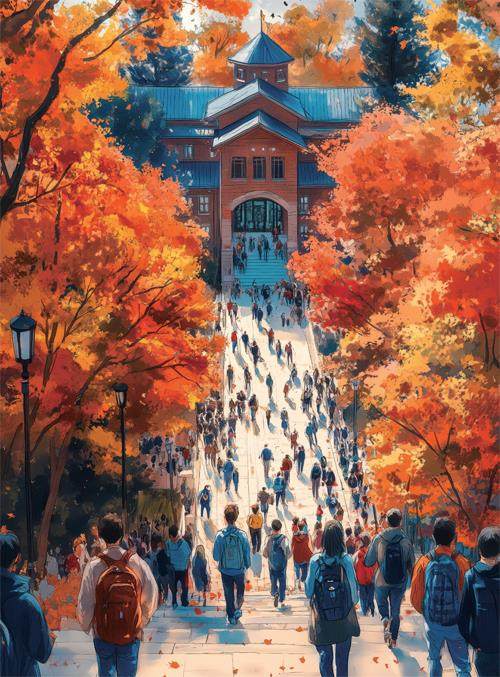
本硕7年,木木在学校先后换过四位咨询师。她所在高校的心理咨询资源较丰富,学生需求也较大,由于每个学期的咨询都需要重新预约,她总是约不到同一位咨询师。
她没想到,有的咨询师会“告密”。
“没有任何想要伤害自己与他人的表达,我始终不懂他(高校咨询师)为什么要突破保密协议。”木木说,她在第四段的咨询过后,咨询师将她对学校制度的不满以及学业的压力告知了导师。
这次泄密让木木开始思考,学校咨询师既是心理咨询师,又是学校的员工,“他们更在乎的也许并不是来访者的利益和福祉,反而是降低学校的风险”。
木木的经历发生在许多学生身上。社交平台上,对高校心理咨询的“劝退帖”不断增加,学生们分享自己被“背刺”的经历,劝退想要尝试高校心理咨询的“同伴们”。
高校内的心理咨询需求在增加。《2023年度中国精神心理健康》蓝皮书显示,对近8万名大学生的抑郁风险检出率大约是21.48%。
但学生们却不敢踏入心理咨询室。日前,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收集了高校学生填写的7595份有效调查问卷,有16.27%的人有做心理咨询的需求但并没有去过,没去过的最主要原因是“不了解学校咨询室情况,不敢贸然前往”(占比44.86%)。
问题出在哪里?
不被信任的心理咨询
木木就读于某双一流院校,在她的学校,临近期末往往是咨询高峰期,她也总是在这段时间寻求帮助,因此很难约到同一位咨询师。最初的本科阶段咨询时,咨询师就跟木木详细介绍过学校的保密协定以及保密突破的范围,前几次咨询结束后,也从来没有辅导员或导师找过她,因此木木一直很信任学校的保密制度。
“告密”发生在2023年第四段咨询,由于学业压力,木木情绪崩溃,尽管这位咨询师并不像前几位咨询师那样适合她,木木还是将自己的烦恼一件件说给咨询师听。令她没想到的是,某次咨询结束后,她突然收到了导师的消息。
木木一开始并不愿意相信咨询师泄密,后来她直接询问咨询师,咨询师犹豫片刻才坦白,自己将木木对学校的不满告诉了她的导师。咨询师解释自己这样做的原因,是觉得导师也许能帮助木木度过这次情绪危机,但这让木木感觉自己被“背刺”了。
木木解释自己没有去找导师沟通的原因,是与导师的谈话总是在公开场合,暴露的环境让她缺乏安全感,很多次谈话她都会崩溃大哭,引起他人的关注,这让她倍感压力。
同时,导师很喜欢在跟学生谈心时举其他学生的例子,她的情况也会成为案例,这让木木每每想到都觉得毛骨悚然。
较为幸运的是,木木的导师并没有向她施加压力,而是以鼓励为主,木木也不断说服自己信任他人,但在后续的咨询中,芥蒂和防备始终在场,木木不敢再向咨询师透露过多的隐私,咨询没有给她带来帮助。
相比之下,王昊受到的伤害更难以疗愈。

那是2019年,他在广西一所高校读大一。第一学期缺课两次后,辅导员找到王昊,得知王昊的情绪不佳,她耐心安慰与聆听,并建议王昊去做心理咨询。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王昊走进了学校心理咨询室,他没想到这会是自己情绪崩溃的开始。
这次名为“心理咨询”的谈话,实际上是一次“心理评估”。王昊回忆,咨询过程中,咨询师只是听王昊讲述自己的烦恼,并没有给出任何反馈。
由于父母长期的语言打压,王昊在高中时就被情绪问题所困扰,他开始自学心理学,对心理咨询也一直抱有兴趣。正因如此,尽管感受到咨询师的回复比较“敷衍和形式”,王昊还是选择继续咨询。
但在咨询室之外,王昊逐渐感觉到了“不对劲”,辅导员将他去做心理咨询的情况告诉了班干部,王昊发现同学们开始区别对待他。辅导员和班干部关心的话语让他觉得刻意与恐慌。“我认为寻求心理方面的帮助并不是特别严重的事情,但人言可畏,同学们都会觉得我去咨询就代表我‘有问题’。”王昊说,他觉得学校就像一个小社会,一旦被贴上“有心理问题”的标签,就可能遭受很多隐性的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