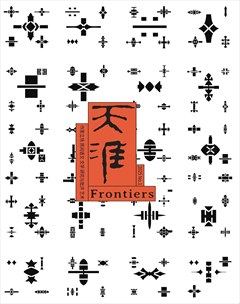活用生态资源,拓展新时代文学新景观
我就生态文学创作这个小切口,讲三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作家若与草木相亲,不愁没有春天。
屈原在《离骚》中有这样一句:“览察草木其犹未得兮,岂珵美之能当?”大概意思是说,连观察过的草木都分辨不得,就更谈不上去鉴赏美玉了。屈原亲近自然,喜欢以香草喻君子美德,他对草木的认识是深刻而独到的,如果探寻中国生态文学之源,一定绕不过《离骚》和《诗经》,虽然古代没有系统的生态文学思想,但有仿生的实践和理念。《离骚》中写了江离、秋兰、蕙等十几种香草,《诗经》里写的植物也多达152种,这源自古人“道法自然”的理念。
我对草木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这与我在北大荒的湿地边生活过有关。湿地是植物王国,草木和繁花是我记忆的底色,每每见到绿植,我就会邂逅故友一般愉悦。我有个习惯,见到陌生的草木总爱刨根问底弄个明白,手机里拍照识草木的软件使用率最高。只要有时间,对那些熟悉的草木我还要重复观察,每次观察都会有些新的发现,可谓览察草木皆有所得。与人相同,草木也在成长,不同的季节,草木呈现出的精神品质会有所不同。比如对牵牛花的观察就让我有了些哲学思考。清晨,牵牛花在太阳尚未升起时就开始笑脸盈盈,像运动会上期待检阅的孩子。太阳升起后一上午它都像微缩版的葵花一样目不转睛地仰望太阳。但只要正午一过,它就会马上敛起笑容,收拢自己,将敞口的喇叭慢慢缩成一截花棍,悄悄隐藏在蔓叶间不再露头。牵牛花对西坠的太阳变脸如此之快,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它是靠什么区别十二点的太阳与一点钟的太阳?相差一个小时的太阳到底有什么不同?但牵牛花区别得分毫不差。

登录后获取阅读权限
去登录
本文刊登于《天涯》2025年1期
龙源期刊网正版版权
更多文章来自

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