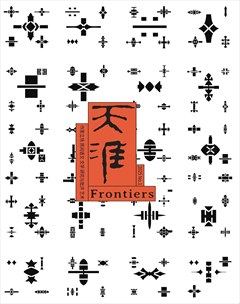新朋友,新课题
从北京坐高铁到福州站,下车时已是傍晚。我找到2023年在屏南认识的司机师傅,去宁德,转屏南,终到四坪,整个过程行云流水。这种“丝滑”的无意识反而激起了我2023年初到屏南时的记忆:云雾下的群山、猝不及防的转弯、随之而来的晕眩……如今,这种面对自然的紧张褪去了,另一种紧张却随之升起:穷尽了2023年的经验之后,重返屏南的我还能写些什么?
好在,屏南没有停下过脚步。随着观察的深入,我发现屏南确实发生了很多变化:潘国老在后山开辟了一片新的稻田;陈小倩在龙潭视野最好的位置盘下了一个新空间;韦永斌、李泾荷夫妇把“星空馆”二楼改造成了放映厅,和新老村民一起发起“我们的四坪”影像共创计划;墘头村“3.0”的建造模式正如火如荼地展开;研究院也换了一批新面孔……当我试图确证我的认知的时候,却往往发现人们的生活愿景、行动方式都差异甚大,能确认的恐怕也仅有屏南的复杂性——这反而使我安心了。
此番前来,潘老师布置了任务,要撰写一份书稿来总结屏南经验。我很犹豫自己能否胜任。我们分到的主题是“‘好山好水不寂寞’:让宜居重归乡村”。围绕“宜居”这个关键词,我们小组确定了以“公共空间”作为关键词的调研路线,希望能在屏南的公共空间中找到“宜居”的要素。但私下里,我的另一个问题是,屏南“建构村民主体性”的经验为何不能在我自己身上发生?它还存在哪些待解决的缺陷?这个经验能否迁移到城市中,继续解决某些岌岌可危的城市病?这个问题来源于去年汇报时贺照田老师的追问:仅用“建成了的主体性”一词来表述屏南经验,很容易忽略其中的复杂性——人的个性是多样的,利益诉求和生活愿景更是多样的,那么他们的主体性为何能同时得以建立和加强呢?
带着这个问题,我重新进入屏南。当时,我为我们组缺乏研究方法和计划感到头痛,而他们似乎完全不担心最后能形成什么样的汇报。但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正是这种缺乏计划带来的“漫游”,使我们得以更加轻松地进入田野,和村民交谈,也听见不同的声音,并充分发挥了每个人的感受力——视觉的、触觉的、听觉的。我对这种偶然却有机的“研究方法”记忆深刻。因此,结合2023年的调研经验,我提出是否可以在空余时间里沿着自己的兴趣进行“漫游式”探索。结果证明,这一方法不仅同样震动了我的新组员们,也为我自己带来了新的认识。有时,暂且放下一些机械的、循规蹈矩的研究方法,或许更能让研究者认识到自己的主体价值,而不必假作“客观”。
画室里的人
一直以来,我都对《乡村造梦记》中讲述的那段故事抱着很复杂的感情:屏南“不拘一格‘用’人才”,引进艺术家林正碌,通过普及“人人都是艺术家”的理念,引导村民投入绘画创作,从而激发了老村民的内生主体价值。首先是老村民,再是残疾人,最后连城里人都被吸引过来。但我始终觉得这个故事无法落地——或者说是没有讲完。书里并没有进一步描写的是,在重建主体性之后,新老村民们是如何投入到村庄建设中去,画完画游客们的生活在这之后又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这次来到屏南,受到“漫游式”调研方法鼓舞的组员们决定去画室亲自体验绘画的过程,但在这个关头我却感到十分犹豫。我对博伊斯“人人都是艺术家”的艺术理论有些抵触,无法相信不遵从技法的绘画能给人带来“解放”,且画室要求七天都得在龙潭画画,往返也很费时。但另一种紧张推动着我也绘画——如果我没有亲自体验过,则无权评价画室和它的理念,既然我迟早要描写作为公共空间的画室,就没有理由拒绝进入画室。伴随着这样的局促,我拿起了画笔。
虽然我全然没有体会到《乡村造梦记》中描述的那些“狂喜”时刻,但绘画的过程和在画室中与人的交往确实给我带来了非常多预料之外的体会。首先是,绘画促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