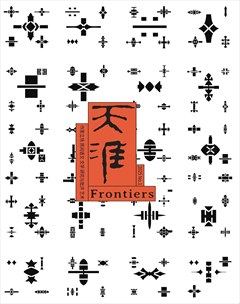乡村的可能
我们坐在一辆从福建古田县发往屏南县的班车上,在重重叠叠、弯弯绕绕的大山里,摇摇晃晃地向前跑着。车里紧凑、窄小,坐满了人,看似都是大山里的村民。他们叽里呱啦的对话完全听不懂,只觉得满富活力。我们紧靠着司机背后的座位,眼睛直直地盯着车窗外的青山。夏天的水汽将大山蒸腾得苍翠、茂密,所有杂木花草重叠交织,眼睛能够辨认的只有绿、绿、绿……
司机熟练地打着方向盘,说道:这山上的芦苇,都是以前的水田,现在都抛荒了。我们方才辨认出这原生态中也有后来者的改造。在熙岭乡大转盘换上去四坪村的班车,经过一段山巅的路,一幅广阔千里、层峦叠嶂的山景出现在眼前。山路盘桓而下,挤过龙潭村热闹的街道,不一会就来到了四坪村口。
古旧恢宏的木构长廊蜿蜒于村庄之上,青石板路曲曲折折于小巷中。斑驳的土墙、深沉的瓦片隐藏着村庄历史,开阔的玻璃窗、垂花的阳台又彰显着现代艺术感。四坪村,安静中散发着生气,古朴中蕴含着设计感,传统和现代如水汇合,融合得如此自然。四坪村不是浓妆艳抹的耀眼,亦非不修妆容的黯淡,那细心描画的古雅浮动在岁月中,吸引人的何止脱俗的外表,还有耐人寻味的生命故事。去过很多村庄,都未有四坪村给我们的第一面美好。无论在深入村庄后了解到多少问题,四坪村都是可以让我们第一眼喜欢上的样子。也许就是这第一眼,激发了我们对这个村庄的感情,也调动了我们探索村庄内里的好奇心。
这是我们与四坪村的初相遇,2023年7月21日,我们来参加由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组织的第三期乡村振兴硕博研习营。在接下来的十天学习中,接受了多位老师关于乡村建设方面密集的思想灌输,又参观考察了四坪村、龙潭村、前汾溪村的新村民空间或艺术乡建情况。在自主调研环节,我和永斌希望以“人”为核心,去发现村庄不同类型个体的日常生活状态,以及更深层的情感思考。我们希望以“生命、生产、生活、生态”的维度,通过纪录片和非虚构写作的艺术形式,尽可能立体地呈现个人与村庄的关系。这种立足个体生命和立体化的创作方式是我们的自觉选择,这是与社会科学以问题为导向,注重宏观分析和理论概括的调研方法所不同的。我们的电影和文学的艺术创作,更关注具体个人的独立存在。他们的日常生活细节、表情言语的状态、内心深藏的愿望或忍耐,这些习以为常的平常背后有着真实的、非常的生命密码。于是,我们对代表性的人物进行了深度访谈,又拍摄了他们的一些生活场景,还捕捉了村庄环境。结营汇报时,我们完成了第一部纪录短片《乡村的可能》。
乡村的可能是什么?它是乡村的希望,是我们的理想,是对未来的想象。十天的调研,我看到了屏南乡村展现出的可能性。这里有敬畏自然、良性农耕的生态意识,有尊重生命、弘扬个性的人文精神,有“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平等思想,有自信地学习、勇敢地实践的自由探索精神;这里还有对乡村历史文化价值的欣赏,有对农民智慧的肯定和激发,有对“城市病”的反思和反叛,有对等级制、精英化教育体制的批判。这里像一个漩涡,像一块吸铁石,它不动声色、源源不断地召唤着老村民一个个回流家乡,吸引着天南海北的新村民披荆斩棘、落地生根,还有南来北往的研究者、艺术家、实习生、旅居者……络绎不绝地来此落脚。
四坪村是我们一眼喜欢上的,屏南却不是一眼能够看透的。它如此多层面的可能,一些契合了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念和对乡村的审美想象,一些又冲击着我们认知的边界。初遇屏南的心情,如同看电影片花,在显与藏之间吸引我们的是一种奇妙的感觉。基于这种美好而神秘、朦胧又模糊的感觉,我和永斌坚定地决定返乡了。虽然我们错过了屏南文创振兴乡村的上半场,但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绝对不能再错过下半场了。四坪村小而美,小而丰富,在反映屏南文创事业方面具有典型性,在全国乡村振兴热潮中也具有前卫性和实验性。我们希望以四坪村为基点,进行长期的跟踪拍摄,只有落地扎根,与村庄同在场,才能进入村庄的内部,才能深入生命的内里。
我和永斌在读硕士期间受梁鸿和小川绅介的影响很大,他们虽然分别属于文学和电影两个不同的领域,以及中国和日本两个不同的国家,但在对农耕文明和乡村价值的喜爱、认可方面是一致的。梁鸿基于对文学脱离现实、学术空蹈现象的反思,提出作为方法的“乡愁”,重新确定情感、乡土、自然之于人类的价值意义。小川绅介长期扎根村庄,身体力行地感受农民生活,拍出了《牧野村千年物语》,记录了一个村庄的生命史。我的硕士毕业论文是《重返乡土“内部”》,永斌的硕士毕业作品是拍摄自己家庭的纪录片《分家》。我们的创作理念都是长时段地进入生活,进行扎根创作。我在论文中提出创作要发掘“内结构”,要通过真实的生活体验,尽可能地呈现世界的复杂关系和深层内涵,尤其是人的精神世界和生命情感。
返乡的念头一旦开启,就一发不可收拾。2023年10月我们再次来到屏南,对发展文创的漈下村、厦地村进行了考察,期间还碰巧赶上四坪村老村民的一场婚礼。这场婚礼上半场是西式婚礼,在新村民空间星空花园举办,下半场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婚礼,在祠堂和戏院举办。我们第一次看见四坪村民集体亮相的热闹场景,被他们在吵吵嚷嚷中协力办大事的精神状态所感动。难以想象,几年前大山里的空心村,今天进行着一场兼容古老与现代、乡村与城市、东方与西方不同习俗、不同审美、不同文化的婚礼。新郎的堂哥潘国老那晚开心地喝醉了,他激动地说:想当年他结婚的时候骑自行车走山路,还摔了新娘子一跤。虽然只是一场婚礼,我们感受到的却有太多:村庄的开放与包容,村民的凝聚力,还有每个人由内而外散发出的对村庄的热爱、自信,这都让我们感动良久,至今难忘。
就在这种朦胧的感性与自觉的理性交织中,我们进入了屏南,开始一步步深入四坪村,慢慢打开了这片乡土大地生长着的乡村的可能。
共创那场雪
白茫茫的山连着山永无止尽,不曾凋落的树木在雪的覆盖下尽显神奇姿态。清晨暖而清凉的光落在雪上,恍惚进入了童话雪国,竟忘了我们还在去往屏南的高铁中。这是我第一次遇见南方的雪,对于从小见惯雪的北方姑娘而言,还是被美艳到了。北方的雪是寂静的,褪却树叶的枝条挂着几缕白,清冷而孤寂。南方的雪覆盖着万木葱茏,是掩饰不住勃勃生机的浪漫。
在古田高铁站下车,遇到一对从厦门赶去屏南看雪的母子,一起拼车去四坪村。可惜正午的阳光就像天空挥动的扫把,从山顶一点一点把雪往山下扫去。等我们赶到四坪村时,融化的雪水把村庄滴得湿漉漉的,只有阴暗的屋瓦、墙角还残留着积雪。老村民嘎子哥高喊道:你们来晚了,昨晚雪可大了。我们知道,一场风花雪月的美景让在地村民大饱眼福。
看着大家开心地给我们分享美照,心中遗憾又羡慕。之后我们碰撞出一个想法,我们可以把大家的拍摄素材集合起来共创一个作品,至少可以弥补难得一遇的美景。这种方式可以使村民获得表达的主体性,把拍摄权交给村民,就是把话语权交给他们。四坪村被媒体报道,被学者研究,被游客传播,四坪村是否可以拥有一个“我拍摄,我传播,我表达”的发声平台呢?屏南文创总策划林正碌提出“人人都是艺术家”的理念,那人人也可以是纪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