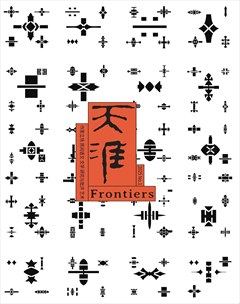上午
也并不是说,他非得走这条路过去,但这条路无疑离家最近,当然也最冒险。
有几条路崎岖难行,比他现在走的这条更难,甚至有的山根本没有路,只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走。
方圆数百里的山中,长了些什么草、开什么花,他清清楚楚。
他是偷牛贼。
但他不认为自己的行当有多缺德。世界上缺德的事儿多啦,要是大大小小的仔细拎出来说,他想了想,偷牛这件事,只能算一件小事。
他不能与人群居。他的职业习惯不允许有邻居。以前他试过,到一个村子里居住,不到半年,他就轮番把他们的牛偷了一遍。虽然没有被人抓住把柄,使用排除法,也大概知道他就是那个贼。那是四十年前的事儿了。那个时候他只有二十二岁,是个年轻的偷牛贼,胆子比现在大很多,四十年一晃过去,现在六十二岁,他是一个偷牛的老贼。那时候他是真心想要过一种正常的日子,就像那些本分的老农民一样,长年累月坚守在耕种的土地上,他想成为他们当中最勤劳刻苦、最善良、最受欢迎的那一个,就像那些苦了一辈子的庄稼汉,最后坐在他们村口的道路边的一棵大树下,就有一种德高望重的味道,人人都会为这个人早前对生活的付出感动并尊敬他,他想过,要成为这样一个人。他不是不知道如何做人,做什么样的人。他知道好坏。可是后来的事情,那就说不清楚了,他是如何爱上偷牛这个事儿,只能说,是老天爷要他成为一个偷牛的人。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一个人要成为什么样的人,非凡的人或堕落的人,知识渊博的人或粗鄙不堪的人,朴素的人或奸诈的人,有时候就是随机性,由不得他过于理性,如果按照他的思路,那他就该是他想要成为的那种德高望重的老农民。他相信,凭着自己读过的那些书,凭着自己的三分口才和见识,当一个德高望重外加几分儒雅的人,他会比任何人都表现得更加德高望重。偏偏他就不是这样的人了。如果没有“命中注定”这种解释,那又如何解释呢?不然怎么理解那个时期的选择呢?在某年夏天的夜晚,他看见一头长得十分漂亮的花牛,在他眼前晃过去,正赶上那时候他的口袋里一毛钱也没有,再赶上当时的牛价非常可观,他看到那头牛过去,就像看到一大扎钞票晃过去,可比看到他亲爹晃过去还叫人高兴,他就是在那个情景下动了偷牛的心思。晚上他便潜入那户人家,顺顺利利地把漂亮花牛牵走了。那个晚上,月光亮得像专门为他照明,这样明亮的夜晚不适合出来偷牛,即便偷了,也容易被人发现和抓住,偏偏那个晚上,他顺利得手了,就像他的前途亮堂堂,预示着将来的路也如此明朗。他当时就感觉到,这是一条他能走的路,也是命中注定要他走的路。他觉得自己被命运之神选中,要他成为一个悲剧人物,或者一个幸运人物,他说不清自己是高兴还是心酸,毕竟是一条别人都不太愿意去走的路,一条离群索居又时刻回旋在人群中的路,遭人记恨和诅咒的路。又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他的命。总的说来,应该是高兴,然后高兴之中有种心酸的悲壮意味。
那就是他过去的生活和选择。
现在他还延续着过去的选择继续生活。他在偷牛这条道路上,也算得上是本本分分,算得上兢兢业业、刻苦勤劳,往大了说,他在他这个行业中,可以自称为“德高望重”。他并不像别的人那样,什么牛都要,他偷的牛,一定是他瞧得上的,无论瘦弱、伤病,只要他看见的牛符合他的心意,就把它们带走。他从来不会牵走一条不愿意跟他走的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他一次也没有失手,他偷的牛就像他自己喂养的,不用催赶,牛自己跟着,一个响声也不出。他觉得自己已经是这个地区最懂牛的人,他是牛的知己,知道牛的痛苦和疲累,要说他偷牛,不如说,他在为牛服务。他懂得哪些牛在向他求助。牛也是会求助的,这个事儿无法跟人说得清楚。牛和人一样,也有诸多心思,有时候它们的情感也很脆弱,在牛的世界上就有牛的烦心事,就有它们的悲伤和痛苦,一些牛时刻想着离开它们所生存的环境,一些牛尝试成为野牛,一些牛选择失足坠崖,一些牛死在浩荡的山水中,一些牛仰天长叹后吃了毒草,一些牛莫名其妙暴死在夜晚的星空下,一些牛累死在耕地上,就是这样,在牛的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死法,因此,他这样一个人的出现,有时候就是会给一些正在“走投无路”的牛一种希望,它们会向他求助,牛和人一样,在关键时刻,即便一心寻死,却没有勇气自我裁决,就指望着被帮助,对那样的一头想死又没有勇气自己去死的牛来说,被偷走转卖后哪怕被宰杀,也是它的出路和希望。牛和人一样,时间长了,会厌倦一直生存的那个环境。它们也想换一种地方生活,或者如果死,就换个地方去死。这是牛给他的信号。这些信号一般人难以察觉,就算是跟他年纪相仿的老偷牛人,也不能察觉。他们缺乏一种与牛沟通的天赋。所以他为什么能自称“德高望重”,就是这么个意思。这辈子如果他有什么朋友,那一定就是那些他偷过的牛。他的职业不允许有人类朋友。
他和妻子后来隐居在独角岭。这个名字像一味中草药,是他妻子命名的。他们有一天赶着牛经过那个地方,看到那儿非常适合隐居,便在那里安了家。那是个险地,除了飞禽走兽在那儿拉屎,就算是鬼,都不会光顾。因此那儿没有外人正在使用的任何现代设备,他们夫妻二人,过着最简单的古人般的生活。也许是偷牛太忙,或者他们夫妻都没有生育能力,结婚二十多年来,一个孩子都没有生出来,不过这样也好,这样更简单了,像他们这样的行当,也不需要有什么继承者。二人世界有二人世界的好。两个人现在都老了,起码他老了,妻子比他小许多岁,现在还不到五十岁呢。说起来,他这辈子也值得了,有个这么死心塌地的女人愿意跟他生活,尤其是,她格外支持他的“事业”,对他的这份工作没有半分嫌弃,他出门偷牛的时候,她就一个人居住在独角岭。他和妻子坚信,那就是他们后半生该住的地儿,只有在那里,他觉得她是个快乐的女人,他是个快乐的丈夫,他们活得无拘无束,像一对寻常夫妻,不用与人群居,就不用时刻觉得别人在用道德审判的双目盯着。妻子在独角岭山脚下种了许多小菜,养了一只小黑猪,一些鸡,一只山羊。她是个勤劳吃苦的女人,算得上是他的贤内助。
现在他想起来这些,想到可爱的女人,觉得这辈子他除了偷牛这件事可能不受人敬重,他的生活态度和生活的决心,应该是受人敬重的。脸上的疲惫感消失,嘴角露出笑意。抬手看了看手腕上的表,时间是上午十点三十分钟。
他拍了拍牛的肚子,让它稍微走快些。又怕它走太快,伸手挡了挡。掏出腰间的水壶,洒了一些在牛鼻子上,自己喝了几口。
前方是密林,这个地方有许多杂树,其中最糟糕的是长着许多倒钩刺的野花椒树。比起红花椒树,它们的刺已经算少的了,可是它们的刺更粗大尖利,尤其有一人多高的野草掺杂,小一些的野花椒树被包裹其中,让人防不胜防。这个地方的人称它们为“狗屎椒”。他又不能把它们都放倒。没有这个必要。他不能为了偷牛而特意开出一条道路,这样只会让他的行踪暴露给别人,越是往深山老林里钻,人们越摸不清方向找不着他,不仅不能砍倒它们,还得感谢它们。除了贼,正常人谁会往有刺的地方去。
进入刺林中,他提前给牛肚子的两边绑了些爽滑的牛皮,用死了的牛皮保护活牛的皮,牛总不至于说他残忍吧。什么东西不残忍呢?世上的事儿,残忍的多了去。他给自己穿了件牛皮大衣,套上妻子给他准备的特制鞋底的蓝色鞋子,走这样有刺的道路,就不怕了。
这时候是上午十一点二十分钟。他和牛在密林中穿行,牛身上的牛皮和他自己身上的皮衣,被野花椒树刮出许多印子,刷刷响,皮肤丝毫未伤。
这次偷的是一头老牛。看上去别说卖钱,白养着,都嫌它糟蹋草料。但他必须将它偷出来,能不能卖掉,卖什么价钱,都是以后再考虑的事情。先把它弄出来,这是道义,是他给自己这个行当立的只有他一个人会遵守的规矩。关于这条规矩,其他的同行是非常不屑的,觉得十分可笑,甚至觉得他根本不适合干这一行,做了贼的人,就不要有菩萨心肠,即使你有菩萨心肠,牛不会对你说一声好,牛的主人更不会说你一声好,一条道走到黑了就是黑了。但他无所谓黑还是白,一个人在世界上生存,必然有他自己生存的法则和道理。他觉得自己应该这么做,并且这么做不会错,一个人做坏事的时候,顺便把好事也做了,难道不行么?好和坏,有时候是可以并行的。这种赔钱买卖,他这些年干得也不少了,不差这一桩。
十天前他在耕地上遇见牛的主人,那是个非常年轻的小伙子,长得很壮实,比这头牛还壮实,用他有力的胳膊拿着鞭子使劲抽它。那时候它就用求助的眼神望着他。他明白那种讯息,可当时的情况下,他总不能当即把牛牵走,为了缓解牛的痛苦,他试探性地对那个小伙子说,你不要打它了,它都这么老了,你不要不相信,它都想死了。小伙子对他的话满不在乎,抬头看了看老天爷,又低头看了看他这个外乡人,咧了咧嘴说,我爹更老,还照样干活呢,当牛作马的货,不干活要干什么?当我的牛就要干我的活儿,要它去做官,它有那个本事么?年轻人说话直爽,一点儿也不拐弯。他暗中尾随,跟踪了几天,看他什么时间睡觉,什么时间出门,好瞅准空当偷牛。今天凌晨一点半,小伙子睡得很沉,他抓紧时机潜入了院子,把牛牵了出来。院子相当洁净,造了小桥、流水和假山,要不是急着偷牛,他就多逗留一会儿了,看得出来,这是个生活很讲究的年轻人,除了心肠硬点儿,没什么缺点了。
牛鼻子上还穿着一条绳。刚偷牛出门那会儿,他都不敢伸手扯这条线,总觉得这个东西比什么看着都难受,就像是从自己的鼻孔里穿过去。残酷啊,可什么东西不残酷、不可怜呢?他能有什么办法——作为一个贼,如果对小伙子说,你应该怎么善待它。他会如何反驳呢?作为一个贼,呵呵,没有替牛说道的权利。
现在,牛到了他的手中。
到了他的手中又能如何?牛鼻子上还是必须穿着绳。在这种险要的道路上,它如果没有牛鼻绳,也很不安全。不好引导它走路。山林中的路不是随便能走的,不熟悉路况,失足掉下悬崖或跌入某个野猪坑(以前这里没有禁止捕猎时,猎人设了许多陷阱),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关键时刻,他还得牵着牛的鼻子走,把它始终带在正路上。他现在要是被人抓住,指不定也给他的鼻子上来这么一条鼻绳。
摸了摸鼻子,摸到一把冰凉的空气。
这是秋天了。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他像是赶着一块会走动的田地,走在属于自己的道路上。
牛的腿上还有伤,伤口粗糙,虽然顽强地结痂了,可也看得出来,还在发炎。牛时不时地,想要用尾巴挠痒痒。十天前,它一定是老得缺钙,一下子就失了前蹄,跪在它拉犁的土地上,剐蹭在一面锋利的石块上。年轻的小伙子显然没有对它的伤口进行任何处理。
他现在把这头牛带出来,不是为牛服务又是为什么?他和别的偷牛贼是不一样的,他是理想主义的偷牛贼。他给牛腿包扎,用他日常戴着睡觉的眼罩套在牛腿上,眼罩套在那个位置,看上去像一只护膝。
走了许久,还在刺中。额头上被刺抓出了血。这次出门唯一忘记带的就是头盔。早知道走这条路,就把头盔带出来了。他的装备多着呢,都是以前在一些村庄里花钱跟人买的。他不会专门为了买个什么东西到集市上散逛,他需要什么,哪儿遇见就在哪儿买,哪怕花的钱其实可以买个质量更好的了。他不在乎钱。他也可以顺手偷走,比如说头盔,各种款式的头盔多着呢,很多头盔都挂在摩托车上没有人管,既然能偷牛,这些小东西,也不是不能偷。但他有自己的原则,除了偷牛,其它东西,都不值得让他成为一个贼。
他对牛的爱是可以让他沦落为贼的,就像一些人对书的爱,对酒的爱,对金钱和权力的爱,以及对某个男人或某个女人的爱。这些人的心思,差不多也有几分贼式的悲壮。这个东西理解起来,也很容易的。但必须是他这样的心境才会体验这个世界上与他共同命运的人多不胜数。只不过像他这样心性的同道之人,隐秘在世道的暗中,他们不会这么明朗地出来表达自己全部的真实心思,他们只表达克制险恶,表达美和良善,表达谦让和成全,不像他这么赶着偷来的牛,明晃晃地穿梭在苍茫的山林中。
他想想,一些人负责偷牛,一些人负责谴责偷牛,是平衡的。要发生点儿什么,才会形成什么,这是平衡的。
一些人在大路上走,一些人就会在小路上走。他在白天和黑夜中的路上走。这都是老天爷选中的。不然如何说得通,他会这么爱偷牛,愿意为了这些活物,孤单地走在山路上。
午睡的时间要到了。开始想要打瞌睡。在这之前,他必须找个地方先解决午饭。他的生活也和那个年轻小伙子一样讲究,哪怕吃得不好,一日三餐,必须按时吃。
抬起手腕上的表,确认时间:十二点十分钟。这是他往日的午饭时间。正好也走出了刺林,到了一块长满嫩草的地上。
吃吧,他挥了挥手,让这头倒霉牛赶紧去解决它的温饱。
如果他估摸得不错,追赶他的人早就已经累熄火了。他们一开始骑着车子在大路上乱转,闹出呜呜的响声,想用那种气势汹汹把他吓出来,一些人扛着东西朝与他相反的那座山上追去,他们都发誓要将他碎尸万段。这些话,他听了几十年了。虽然他现在已经很老了,可他有丰富的偷牛经验和逃走的经验。在这片区域,他要什么样的牛,就能偷走什么样的牛。他的牛也只在晚上去卖,在那个专门销赃的窝点,买牛的和卖牛的形成一种默契,买定离手,后果自负,都遮着面孔,谁也看不清谁。凭感觉,把牛卖给自认为最可靠的人。
牛在吃草,看它费劲地咀嚼,这点儿草料不多,但对它来说足够了。它老得开始厌食。
乌鸦在头上飞过去。叫声难听极了。它们象征着死亡。
死亡是什么?死亡就是不能再偷牛了。
他啃着妻子十天前给他准备的干粮。一些牛肉干,一些鱼干,一些蒸熟的腊肉干,一些炒熟的大麦粉,还有蒸透了晒干的蔬菜碎,用水一搅和,也就对付一顿。
吃完饭开始睡觉。这是他的习惯,也是他这个行业中最危险的一个习惯。一些人当了偷牛贼以后,一辈子没有睡过午觉。
拴住牛,然后找个隐蔽的地方。他必须半睡半醒。这是做贼做出来的本事。许多同行就是在午睡的时候被人抓个现行。人们会把抓到的偷牛贼殴打一番,然后再交给官家。有个人活活地被打断了一条腿,嘴里还被塞了些牛粪,真是狼狈啊,他做梦能想到,这辈子因为偷牛而被人逼着吃了牛屎。有个人被绑起来挂在树上,挂了整整一个晚上,号叫了一晚上,尿了一裤子。这些事儿他听闻得也多了,让人毛骨悚然的酷刑比比皆是,要知道,一些人一旦将另一些人定罪,他们整人的手段就会没有下限。但他从未想过改行。人是很难改行的。上了贼船的人很难洗手不干,就像人的性格一旦形成,也是很难改变的。人会遵循某种模式,在他能掌握的熟悉的环境里周旋到底。他从来没有被抓住的原因就在于他睁只眼闭只眼睡觉。他的耳朵非常灵敏,在睡眠中,也能分辨得出风吹草动,或是人的脚步声。
他始终相信第一次做贼的晚上,那种吉祥的预兆。那是非常幸运的一个晚上。所以往后的这条道路,能发生什么倒霉事儿呢?根本不可能。到此时此刻,这不,一切顺利,他的牛在吃草,他半睡半醒。一只眼睛在梦里看到了一片山川,他半个身体在梦里飞行。
下午
豹子沟村的人们,把摩托车停在周围所有村庄的每一个的入口处,自从昨天晚上那头瘦牛被偷,整个村子的老少全部聚集起来,会开车的开车,不会开车的走路,总之,四散开去,像一张大网,发誓要将可恨的偷牛贼抓出来。他们要叫他好看。
黄有才提着一把杀猪刀进了山。他就是那头瘦牛的年轻主人。虽然那头牛什么活儿也干不好了,可它好歹是老父亲传给他的财产。当然啦,他也不是真的为了那头牛进山,他只是想趁此机会找个人出一出闲气。他这几年日子过得差,憋着一肚子火。要说那头牛,要死不活的,多它不富,少它不穷,偷不偷走,他的日子都一样憋屈。
不过,现在,他得找出那个偷牛贼。村里所有的人都出动了,哪怕是为了感谢大家的好心,他也必须作出气势汹汹的样子进山。大家的日子过得肯定都不怎么样吧,所以这一次,他们得到了一个宣泄的机会。他们比他这个真正丢了牛的人更热闹地冲出门去,要找那个偷牛贼报仇雪恨。报什么仇,雪什么恨,只有他们知道。
他们在各个村口堵截,到处打听有没有人看见一个人牵着一头瘦牛经过。那些人统统摇头表示不知道。他们知道路人不知道。要的是一种紧张、威严和张扬的味道,要全世界都知道他们在干一件大事,在寻找那个令人唾弃的偷牛贼的下落。他们要让偷牛贼知道,他干的是一件堕落的可耻可恨的事儿,而他们,一群光明正义的使者,要将他包围起来,重重包围,无路可逃。
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他们必须知道,由不得他们不知道,黄有才扛着他祖传的那把半米多长的杀猪刀进山了。
山里到处都是杂木,挡来挡去。走一步退半步。这种速度,偷牛贼早就去很远了。可他不能回头。他用杀猪刀开路,一路砍呀切呀戳呀,时间长了,感觉自己不是来追贼,而是上山开路干活的。毫无意义的宣泄。回头一看,自己走的路,才这么短一条。偷牛贼是不需要路的,路就长在他们的身体和灵魂上,眨一眨眼都能眨出一条路来。他们那样的人,专门走那种别人都不知道怎么能走通的路。
有一阵儿他觉得好像快要赶上了,仿佛已经闻到了牛的气味。他坚信自己进山的这条路就是那个偷牛贼走的路。
很快有人跟了上来,十来个人,他数了数,十一个,全是年轻人。黄有才本来想回家去了,不找了,这下可好,走不了了。大家比他这个丢牛的主人更积极地抓贼呢。
他们带着干粮,带着开路的镰刀,好像这辈子不找到偷牛贼,就永远不回家了。
一群人开始忙活起来,向着深山老林里钻。他们相信这条路是对的,偷牛贼走的肯定就是这条路。年轻人的直觉向来比老年人的判断更准确。黄有才的父亲走的则是另一边山林的路。那条路谁会去走呢?说起来,那座山就根本没有路,就算是做贼,也不可能选一座完全无路可走的高山逃跑。那座山全是长刺的树,各种各样的刺,其中最多的刺就是野花椒树的刺,没有人会笨到把偷来的牛带入一片刺林。更何况那座山,他们都称之为“死山”。偷牛贼都很迷信,光听那座山的名字,他们就不可能去。可是黄有才的父亲,黄二老爷子就不顾众人的劝阻,一大把年纪了,还坚决地要去那座山上看一看。他能去看到什么呢?等着瞧吧,他只会看到自己怎么走也走不到那座山里去。他们对黄有才说,你爹能看到什么呢?
黄有才非常了解自己的父亲,那是个没什么耐心的老人家。稍晚些时候,他们家的厨房就会冒炊烟,老爷子会一个人走一走,走不动了回家去,在家里杀鸡煮肉吃。他爱吃肉。
想到吃的,黄有才肚子更饿了。带来的那些干粮,还不够塞牙缝。可是他们好像都不饿,都在拼命地拿着刀具在那儿开路。要把偷牛贼隐藏在山中的暗路明白地开出来。抽丝剥茧,让路展现在阳光下。大家忘了一个重要的事儿,谁又会牵着牛走这条特意开出来的路呢。
黄有才走最后面,随时都想打道回府。世界上丢失的东西多了去,一头瘦牛,丢了就丢了,不要也罢。可他们不干。他们像被什么东西下了咒,砍呀切呀戳呀,像他刚才发疯的样子。
他们都没有水喝了,平白地流着汗水,十一个人,汗流浃背,渐渐地,汗水都快流不出来了。
这有什么意义?为了一头牛,大家都在瞎忙,都不去收割地里的庄稼。这可是收获的季节呀。虽然今年遭了天灾,所有人的地里都没有几粒饱满的粮食。可有几粒算几粒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