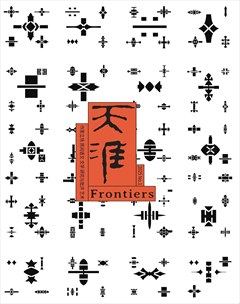人类最优秀的品质就是不屈不挠,这是长生经常和我讲的。长生是一个哲学家,至少在年少的我看来,他是懂得最多大道理的人。我坐在仓库院里的大水泥斜坡上,戴着棉线手套,双手紧紧攥着一根尼龙绳,绳子下端绕过我正坐着的一块薄木板底部,这就是我和长生一起制作的简易雪橇。奶奶新买来给我过年戴的红色棉手套上已经沾满泥土,虽然离过年还有十几天,但我完全不在意手套已提前变得如破布一般脏污,一心都扑在这雪橇上。这是我一雪前耻的机会。
几日前下了一场大雪,雪已经被院子里的热心大妈们扫到了路边,混着垃圾杂物,形成一摊摊黑色泥沼,如同醉酒后的呕吐物,硬是将消化一半的东西掏出来给你瞧。为什么这么白这么美的东西,会变成这幅人嫌狗憎的模样?我曾这么问过长生。长生说,越是纯净的东西,越容易被玷污。人也是这样的吗?我又问。长生没有回答。
下过雪的水泥路面,结了一层薄薄的冰,仓库院的孩子们都跑出来玩。若是看到哪个孩子穿着父母过年给他们新买的溜冰鞋,小孩就像一群叽叽喳喳的麻雀看到掉落在地上的小米粒一般,蜂拥而上。我最瞧不上他们这样的行为,但长生说我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我和长生是这群孩子里的异类,在大人眼里,我们是最不合群的孬种。但这真不怪我们,是这群小孩太势利眼了。有人说过,人之初,性本善,小孩子的世界是单纯善良无污染的,但这话放在现实面前就是狗屁。我们仓库院里的孩子,如大人的世界一般阶级分明。仓库院里住的大部分都是后头木料厂的员工和家属,小孩子们每日耳濡目染,也就有样学样地复刻了成人世界的阶级观念。不信你看,那群孩子里的小霸王,准是厂里哪个领导家的儿子。
不合群,并不意味着可以被这群臭屁小孩忽略。前几日出了期末考试成绩,成绩一出,总免不了几家欢喜几家愁。我险险跨过及格线,排在班里的倒数几名。长生和往常一样,每次考试都玩消失,成绩也一如既往的垫底。这些我和长生早已经习惯了。因为他的情况,他妈妈向来不会因为成绩苛责他。而我这边呢,奶奶每次看完我的成绩,就面无表情地把成绩条往麻将桌底下一塞,继续打牌。成绩条混同着那一堆三五毛的零钱,消失在暗红色的粗毛呢桌布底下,如同被人一把扫入下水道的垃圾。没用的东西,眼不见为净的态度。真的,我已经习惯了。
我唯一不能习惯的是院子里那群臭屁小孩的骚包模样,拿着考试后家长给他们新买的滑板车和溜冰鞋,在我面前一圈一圈地转悠,走起路来,那屁股好像被炮崩了一样扭个不停。士可杀不可辱,我单方面决定和他们一决高下。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长生。长生说,你冷静一点。我说,我冷静不了,他们一直在我面前绕来绕去撩拨我。长生说,这院子就这么大,他们除了在这儿还能去哪儿玩儿?我说,你看问题太简单,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
就这样,长生被我成功拉上了贼船。我觉得,既然这群小孩耀武扬威的资本是溜冰鞋,那我就必然要整个比他们更气派的行头。大冬天里,只有造雪橇才能满足娱乐性与观赏性的双重需求。于是,在这北方数九寒冬的凛冽大风中,我捏着一根细细的尼龙绳,蹲在我的木板雪橇上,愣愣望着面前覆盖着薄薄冰面的巨大陡坡。深吸一口气,我心一横,学着电视里人五人六的成年人,大喊了一声“发射”。长生站在我背后,手掌的力度透过厚厚的大袄传递到我背上。他推着我一路助跑,加速,而后快到陡坡边缘的时候使出全身力气,嗖的一下把我推下陡坡。
我死死攥住尼龙绳骑在破木板上,但我相信这一刻我的身影就如同胯下骑着恶龙的驯龙骑士一般威风凛凛。木板顺着冰面疾速滑行下降,扑面而来的寒风夺去了我的呼吸,但我仍用力在风中瞪大双眼,因为我不仅想要清楚地看到院子里小孩艳羡的表情,还想要在这一瞬间飞驰而过的风景中,寻找名为自由的感觉。
我向来知道,自由是个奢侈的东西。语文课本里说,风是自由的,鸟儿是自由的,但我觉得它们并不自由。风总是要被其它的风推着往前走,它若停下了脚步,甚至会失去自己的身份而变成普通的空气。鸟儿为了生计,也总是需要随着季节迁徙。我爸妈就和鸟儿一样,他们也必须要为了生计,跑去南方谋生。小时候,我不想让他们走,他们就说,那里四季温暖如春,等我长大了就带我去。他们去了南方之后,我做过这样一个梦,梦见爸妈站在南方一棵长满鲜花的大树下,而我和奶奶两个人手拉手,孤零零立在北方冬日铅灰色的天空里。自那之后,爸妈只有过寥寥几次返乡,但他们并没有如我梦里那般得到温暖适宜气候的滋润,而是肉眼可见变得越来越黝黑粗糙。我问奶奶,奶奶说,他们在工地上打工,哪能有多滋润。可见,大人也不自由。
要我说,这世上只有一种人是自由的,那就是充分被爱的富足小孩。他们拥有无条件的爱,能够选择想做的事,并且无须面对成年人的责任。不被护在羽翼之下的人,哪有那么多自由。
风呼呼划过耳畔,刺得我眼睛生疼。木板雪橇嗖的滑过开阔平坦的院子,毫不减速地向着对侧的一排洗脸池冲过去。这老式仓库院里面的房子都是像宿舍般的单间,没有厨房、卫生间,连洗脸池都是露天公用的,在黑魆魆的楼栋门口一排排开,就像从戛然张开的大嘴里伸出的一条诡异长舌。这里无疑是个嚼舌根子的好地方,不管是洗衣、洗菜、洗手、洗头,仓库院的女人们一天到晚都得聚在这里,好好说道说道那东家长西家短。为了方便排水,洗脸池砌在十几厘米高的台阶上,这台阶完美挡住了飞驰中的木板雪橇,但这一迅猛刹车让我整个人揪着尼龙绳向前翻了出去,然后,脸先着地。
随着我这壮丽的一摔,周围尖叫声一片。一瞬间,眼前的世界变得如同抽了帧的老电影,模糊朦胧。我感到嘴里隐隐钝痛,用手背蹭了一下嘴,原本已经弄脏了的红色棉手套红得更加鲜艳了,上面还挂着半颗碎裂的三角形牙齿。我的大脑嗡嗡作响,隐约看到长生跌跌撞撞向我跑来,待他站定在我身旁,我才看清楚他那双眼睛。只一眼,我就知道,长生不在了。每到重要的时候,他总是不在。
不用说话,我都知道他是谁。
我不死心,拽了一下他的裤脚说,你跟长生说,下次助跑可以不用这么拼命。我也不知道大壮能否听得懂我这口齿不清的嘱托,说完我就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的时候,眼前的房间一片纯白,我以为自己上了天堂。
还没来得及回顾这短暂的一生,我就被刺鼻的消毒水味以及钻心的疼痛折腾清醒了。我抬手一看,整个手掌被纱布缠得密密实实,只露出了还算完好的拇指和食指。我看着这两根手指叹了口气,看来寒假作业还是逃不掉的。门外传来说话的声音,我挣扎着坐起身,一抬眼惊得我汗毛竖起来,面前白墙上挂着的镜子里窜出一个有着两只黑洞洞眼睛的木乃伊。
随着我撕心裂肺的惊叫,一群人推门冲了进来。奶奶挤开一旁的白大褂冲上前来,想要伸手摸摸我,但又好像无从下手。我扭头看了看镜子,确认了两件事。好事是,木乃伊是我晃神看错了,坏事是,我被包扎得宛如一个木乃伊。
一群白大褂后面露出一个灰扑扑的瘦长身影,我看了看他的眼睛说,长生你过来。他慢吞吞走到病床前,头低着,眼睛不愿看我。他本就瘦,这垂头丧气的模样更是让他看起来像一只泄了气的皱巴气球,连肩胛骨都恨不得从棉衣里突出来。长生说,对不起。我说,没事,刹车系统设计有缺陷,我们下次再改改。奶奶在一旁嚷道,你这小妮子还想再来一次?!她朝我扬起了常年摸麻将造就的精准厚实的巴掌,但瞄准了半天,我身上实在没处好皮给她打,只好作罢。长生梗着脖子继续说,我不是说这个,我说对不起,是因为我又临时逃跑了。我想朝他笑笑说没事,但这张脸实在不允许我做出过于丰富的表情,只好伸出硕果仅存的食指,蹭了蹭他身侧紧攥的拳头,说,没关系,我知道你控制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