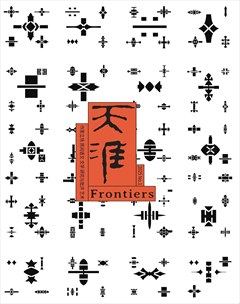一
去安阳,为的是寻访一位商朝女子的遗迹。
妇好,好是她的姓,妇是尊称,意思是姓好的妇人。在商王武丁时期的甲骨卜辞里,这个名字出现过二百多次。一条条卜辞的内容,指向了她的多重身份:武丁时时放在心上的妻子、背负着生育责任的王后、朝中主持祭祀的大祭司、拥有自己土地和军队的封臣、平定外敌的赫赫战神。
三千多年前的女子,何以将不长的人生过得这般热烈?
身后也不寂寞,十六个奴隶和六只小狗,随她一同奔赴黄泉,更有近两千件陪葬物,如今分放在几座知名博物馆里,每日领受着千万人的赏赞。也因此,她的名字,会不时在世间被提起。我筹划很久,要去看她。
时值清明,约小桂同行。从清晨开车,午后抵达安阳。当日逛了安阳博物馆,次日一早去了中国文字博物馆,然后前往小屯村。此村听起来朴实平淡,放在考古史上,实为伟大灿烂的地名,是甲骨文的故乡和殷商的都城遗址。商朝时它的名字是殷,商灭亡后,昔时繁华渐渐凋敝,又有了另一个称呼:殷墟。这两个字散发着荒废和空寂的气息,与它有关的一切,仿佛都是深邃难明。而妇好墓的面世,还原了其中一段老去的岁月。
以妇好的身份,本应在王陵区建墓,武丁却把她葬在了处理军政大事的宫室旁,又在她坟上建造了一座祭祀的庙宇。此举或许是出于悲伤,想把她留在身边,也可能是希望她的英灵留在这儿护佑国家安定。不承想,这样的安排反倒护佑了她,王陵区的大墓后来无一不被盗掘破坏,宫殿区的妇好墓完整无损。
走在通向妇好墓的路上,两旁立着跽坐玉人和鸮尊的石像,其原型都是她墓中文物。向远处望去,一位汉白玉雕刻的妇好,正披甲戴冑,举着一只龙纹大钺,站在自己墓前。快步走近,只见她生了一张标致的椭圆脸,娥眉杏眼,高鼻薄唇。妇好尸骨已朽,眼前这位美人的样貌,不知是从哪份资料中提取出来的。然而,也算是见着了。我仰起脸,含笑向她挥手,小桂举起手机为我们拍下了这次会晤。
妇好像的身后有一座青铜颜色的小房子,进去下两层楼梯,看到一座二十多平方米的长方形竖坑墓,墓中摆放了复制的文物和人骨。1975年,小屯村平整土地,考古队进行勘查时,意外发现了这座古墓。据主持发掘的考古学家郑振香老师回忆,墓里堆得像仓库一样,遗物一层层出土,人没处下脚,玉器和铜器用桶筐向外运送。她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华丽妇好墓》。如此华丽的墓,赶在那个时代发掘,村民们也享了眼福。现场是半开放的,围观的人熙熙攘攘,每取出一件都有人喊:又是一件。当偶方彝的器体拉上来时,有个人大叫道:长方的,像猪槽……
那一声大叫好似还回响在墓室中,时空已转到今日,墓边的人,换成了我和小桂。小桂觉得没意思,玩弄起了手机。我俯身向下看,墓底有一片遗留的朱砂红。想必正是由于朱砂的腐蚀,加上地下水的浸泡,使妇好遗骸无存。当年,她长眠在木棺中,司母辛鼎、偶方彝、鸮尊这些样貌威严的青铜礼器排列四周。我看过考古报告,知道她棺上共有六层填土,如同为她覆上的六层锦绣被褥,每一层里都裹着宝物。第一层陶爵;第二层玉臼;第三层石铲和鸱鸮纹的石磬;第四层铜戈、骨簇、玉管;第五层玉戈和玉圭;第六层最丰盛,石锤、石熊、铜镜、骨笄、象牙、骨刻刀、玛瑙珠、玉壶、海贝。
墓室上层的台子上,四面都躺着殉人和殉狗。墓壁的东西两面,挖了两个长条形的壁龛,里面也躺着殉人。龛内现在安装了射灯,雪白的光照在殉人身上,氛围略显怪诞。他们中有男有女,还有两个儿童,多被杀戮,或是腰斩。那是一个流行殉人和人祭的王朝,甚至食人。主人下葬时,随葬品放好后,奴隶们也要跟着入墓了。在同时期的墓葬中,妇好墓的殉人不是最多的。
从墓中出来,我留意到草地上有一种小野花,短短的茎,黄澄澄的细密花瓣。我说是旋覆,小桂说是蒲公英,极有可能她说的是对的。我们在殷墟走了很久,经过了一个一个的祭祀坑,有时过去看看,有时默默绕开。我们脚下,始终只开着那一种花,隔几步,见一朵。在这白骨与鲜血之地,它犹如祭奠之花,异常静穆庄严。
二
在殷墟博物馆的餐厅里,看到有甲骨文面,小桂雀跃起来。我不怎么爱吃面,便说,倒也不见得好吃。她说,不好吃也要点,这个别处没有,我要发在朋友圈里。很快两份宽宽扁扁的面条端上来,每一根上都用墨鱼汁印着竖行的甲骨文,竹简一般古雅。小桂赶忙用筷子挑起拍照,我也捞了一根品尝,绵软弹滑,味道尚好。服务员告诉我们,面条上写的全是吉语:日进斗金,吉祥安康,大吉大利。
小桂结合着答案,把每根面上的文字都对应上了。一碗面条入腹,俨然为她增添了不少知识底蕴。当听说目前尚有许多未被识出的甲骨文,谁若能破译一字,可得赏金十万时,她不禁面露神往之色。
遥想清朝末年,一片甲骨惊天下。时任国子监祭酒的金石学家王懿荣,看到一味名为“龙骨”的中药材上,刻划着图形般的符号,立刻断定为上古文字。自此,甲骨文被发现了,一门显学开启了。这一切看似偶然,又怎知不是天意。王先生的家乡是烟台,有一年我去游玩,在广场上迎面遇见他的铜像,想到他一生耿介清廉,后以身殉国,不由驻足默然。考据过甲骨文的还有王国维先生,以及曾写下《殷商卜辞综述》的陈梦家先生,都是百年不遇的大学问家,命运最后却令他们同样陷入绝望的洪流之中,无法自渡,令人思之长叹。
甲骨文朴拙可爱,商朝人把对世界的认知,绘成了象形线条,许多字都如一幅素描小画。它又十分自由,偏旁常常不守规则,随意地变换位置,字形也不拘一式,能正着写,也能反着写,竖着写。虽是汉字的鼻祖,却也是汉字最天真活泼的时代。
“妇”在甲骨文中,是一个跪着的女人与一把扫帚的组合,扫帚的方位不固定,可以在女人的左上方或右上方;“好”则是一个跪着的女人和一个小孩的组合。在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器上,大多带有“妇好”的铭文。器物应当是由不同工匠所铸,铭文的写法也相异。有一种是合并书写,两个字中的女人分别在两侧,中间放一个小孩,扫帚在小孩的上方,这种字形的样式对称牢固;又有一种是两个字共用一个部首,只一个女人,她的头上是扫帚,小孩在女人左边或右边,这样的写法飘忽灵动;还有一种是两女一孩在一起,扫帚单独被放在远处。工匠们仿佛在信手随笔,为王后设计着奇特的签名。
也正是由于甲骨文的书写如此不羁,才引发出学术界著名的“司”“后”之争。殷墟出土的那件重达875公斤的铜方鼎,过去人人都知道它叫司母戊鼎。谁能想到,一个鼎竟然会有改名字的时候。有些学者认为甲骨文会“正反书之”,所以原先考证的代表祭祀的“司”,应是象征着尊贵地位的“后”。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国家博物馆将其改为后母戊鼎,而殷墟博物馆和考古博物馆仍然沿袭旧的释读。我因为是在中学课本上就认识了它,多年习惯,亦不想再改变。
但我中学时并不知司母戊鼎的主人是谁,后来才知她名叫妇妌,也是武丁的妻子之一。戊是她死后的庙号,她的儿子为祭祀亡母铸造了大鼎。我在寻访妇好的线索时,难免会与妇妌不期而遇,也会以小女人的心肠去揣测,两人之间的关系是否微妙。妇好的儿子也为母亲铸了鼎,名为司母辛,但个头远不及司母戊。妇妌与妇好都没有被史书记载过,究竟谁先嫁给的武丁,她们的儿子分别是谁,甲骨卜辞上也不曾出现相关的讯息。假若以献给母亲的鼎的重量来推想,应是妇妌的儿子继承了王位。
司母辛鼎共两件,殷墟博物馆藏了一件,视为镇馆之宝。我在展厅里见到了它,满身绿锈,稳重大气。长方形口,器身有乳钉纹,四根圆柱形的脚上分别刻了兽面纹。内壁刻“司母辛”,“母”在右侧,与“女”的写法相同,也是一个屈膝的女人,只是身上多了两点,象征着哺育的乳房;“司”在左上方,与现代字形接近,下面的“辛”字,是妇好的庙号,它的形状就像一棵小草,头上顶着一根木棍。器物本只是金属与化学元素的合成,身上带了文字,就创造了命运和身世,在沉闷规整中多了些鲜活饱满的气息。
旁边是几件铜方壶和铜斝,铭文都是“司巧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