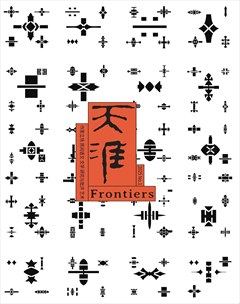一
娘客死他乡奔尸回家,那一夜北风紧,飘飘扬扬的雪铺了一地。
那是怎样的一场雪啊,先是雨夹雪打在瓦上泠泠作响,高压线在寒风中又搓又绞,黑暗中舞动的声响像新磨过的刀刃,枯黑的树枝随后摔下来断成几截,待到头更,风歇了,原以为会云收雨住,却是半空中肆意变换着姿态的雪花,飘飘洒洒,落下来,很快地面上便堆积了厚厚的一层。
看热闹的人们渐渐散去,剩下几个本房叔伯袖着手缩着颈在灵堂里走前走后。兄弟们围拢来,无助地看着娘白天还是温软的遗体慢慢变硬。伯娘小心地摸着娘冰冷的手,突然一跺脚,拔掉娘身上的呼吸管、导尿管、输液管。她一边轻声细语地唤着娘的乳名,一边扶娘坐起来,给娘换上寿衣。娘贴身的衬褂,还是在医院手术前小弟脱给她的,伯娘说让她带去好了,留个念想。不等伯娘说完,一旁嘤嘤的老姑陡然放声大哭,兄弟们也跟着簌簌地落下泪来。
父亲挨着老姑坐,半个身子被老姑紧紧地搂在胸前。父亲无声地哽咽,颈脖一上一下地抽动,几次他想站起来去扑娘的遗体,被叔伯们制止了。叔伯们狠狠地把他按坐在椅子上。伯娘招呼着侄女们把父亲扶回房间,可一转身,他又趔趄着踱回娘的身边。
雪无声无息地落在地面。门前的老槐蜷缩着身子,下雪天让它觉得分外委屈,冷不丁一抖身,像得过热症的病人的寒战,平整的雪地里便砸出几个窟窿来。在大冷的寒冬,老槐竟然没有一件可以御寒的衣衫,那些葱绿了一个夏天的叶片,一到冬天便纷纷逃离枝头,叛离树身。但老槐宁可光着膀子,也不愿接受外来的怜悯和施舍。它的孤矜耿介,像极了父亲。
二更后,宵过夜的鼓师唱完“梅花三五点,傲雪几千尘”,开始插科打诨。争烟环节便是绝好的机会。穿插着挖苦讽刺,兼几句押韵的下流话,把个庄严肃穆的孝堂搞得乌烟瘴气。父亲听不下去,他抖动着下巴,枯瘦的手朝空中一挥,厉声喊道,滚,都给我滚!但父亲的愤怒,像投向巨浪的一枚硬币,很快被孝堂里的喧闹的声浪所淹没。父亲意识到自己老了,说话没人会听,他瞪了一眼门前的老槐,脖子又开始一上一下,身子抖动得更厉害了。
多年后,我听人说,雪可以覆盖忧伤,可以纾解人生的烦恼,可是那一年父亲的雪,却像一粒粒精神的泡腾片,让忧伤铺天盖地,让烦恼像刺丛里的茅草蔓延,扯不断理还乱。
二
父亲原本是喜欢雪的。
他的童年,尘世安稳,风有风的模样,雨有雨的模样。每年的三九,该来的大雪总会应时而至。耀眼的白,半人深的雪被,使他的童年被欢乐包围。他和伙伴们一起堆雪人,打雪仗,唤猎狗,赶野兔,学着《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的方法,用一面竹筛在雪地里捕麻雀。为了让患上黄肿病的祖父在大冬天能喝上一口热鱼汤,他单衣薄衫去东港湖敲开厚厚的冰层。雪夜,燃烛读诗,《正气歌》是背诵得最熟的一首,常常把孟夫子的“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置于座右。雪的洁白、浪漫,不染尘埃,裹挟着他的灵魂,扎在他的心里。雪的世界,其实是他安放理想的最好的地方。
父亲十二岁那年,故乡遭遇百年一遇的洪灾,整个分洪区白浪滔天,一片泽国。祖父挈妇将雏,挑着一家人的四季衣衫,随着逃荒的人群来到崇阳县。那时候物资匮乏,富庶的江汉,大多数人尚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日子,更何况山高地少的崇阳?灾民们的到来,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寄人篱下的灾民只好挨村乞讨。人多了,很难讨到,于是偷地里的红薯,挖下窖的甘蔗。因为饥寒交迫,加上不服水土,同去的村民,好些人都丢了性命。脑子活络的祖父,不甘心自己的子女沦为乞儿偷儿,更不甘心一家老小沦为饿殍,决心做一点小生意。刚开始尝试着做了几项营生,没蚀本也没赚到什么钱。入秋时,他看到山里早开的酒曲花,红扑扑的,心里一下子有了主意。于是动员全家做酒曲卖,一分钱一个赊销给当地山民。由于祖母做的酒曲产酒率高,味道甜沁沁,放再久也不变辣,备受山民青睐,故根本不愁销路,以致多年后,通山、崇阳老一辈的山民都还在念叨江北何家婶子做的酒曲。九月洪水退去。十月底,故乡堵口复堤,灾民们陆陆续续踏上了返乡的旅程,但尝到甜头的祖父仍舍不得回去。他把父亲留在崇阳帮衬祖母收账,自己与伯父伯娘先行一步返乡打理祖屋田产。
那年冬天,寒潮提前来临。十二月下旬,气温陡降至零下十七摄氏度,故乡水域除长江外全部冰冻,洪湖湖面可以推车、滑船。还是少年的父亲顶风冒雪,在异乡崎岖的山路上艰难地行走,挨家挨户地推销祖母做的酒曲。父亲承继了祖父勤奋、刻苦耐劳的品性,在推销收账的几个月里,不知起了多少早床,摸了多少夜路。
俗话说,一百天没有不打破一个碗的,也是父亲的命数,在劫难逃。在一个雪夜里,他不幸从四五米高的山坡上摔下,从此落下一个叫做癫痫的病根,伴随终生。
父亲于是对雪有了阴影。他逐渐变得谨小慎微,变得沉默寡言,变得优柔寡断,变得人云亦云。他向自然妥协,向岁月妥协,向周围的一切妥协。他把自己交出去,做一粒善良的种子,把爱孕育,让爱开花,让世界阳光明媚、花团锦簇,自己则慢慢地变成掏空了的句号。
三
经过那次意外,父亲变得体弱多病,走路风都吹得倒。祖父怕父亲熬不到成年,听信巫师的蛊惑和撺掇,把父亲过继给年轻时投笔从戎在外战死尸骨无存的叔爷,办了酒,请了中人,写了抱书。真奇怪,从那日起,父亲身体日渐强壮,喷嚏都不打一个,二十来岁血气方刚的时候,甚至可以抱起碾场的石磙,绕禾场走上三圈。虽然实力摆在那,但他还是改不了胆小的毛病。
父亲完全拥有与人抗衡的实力,就因为胆小,他一辈子几乎没与人交过手。但有一次例外。记得那时我还小,隔壁年长几岁的阿毛偷了我的小人书,我和阿毛纠缠不清。他的光棍爷凶神恶煞地走过来,呼了我一耳巴,父亲瞟见后也不言语,猛地冲到光棍爷身边,只一个回合,便把他压在胯下。而仅此一次,还是改变不了父亲胆小怕事的实质。
父亲即使棍棒临头、刀斧加身,也不为难对方,并以笑脸示人。晚年的他,常常对儿孙说,雷公不打笑面人。有一年在刘家淌疏浚北江河,因为界桩与邻村发生打斗,明明腰梗子已吃了对方一扁担,父亲却还在一个劲儿地给人赔笑脸,结果药罐子背了整整三个月。每逢家人与人争论,他总是“扳反机器”,从不说自己人的对,而是一个劲地给人赔罪,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志气,让家人丢光了老脸。
父亲年轻如此懦弱,老了更加一筹。乡下人背地里喜欢东家长西家短,父亲的悭吝总是成为那些人茶余饭后的话题。有人说,你看,狗都不上玉嗲家去,晓得么子原因吧?因为他家一年到头不见肉,狗是要啃骨头的呢!父亲听出这句话的弦外之音,不言不语,只是眉头皱得更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