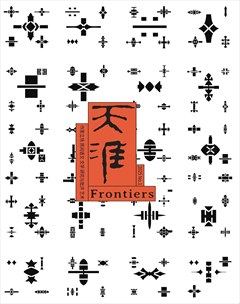一
某年夏天,我和先生在布拉格小住。房子在伏尔塔瓦河西岸。登上山顶公园,顺台阶下到河畔,河水湍湍地流淌,站在桥上远望,城堡耸立在灰白层云之下,一朵一朵的云从天空浮到桥上,浮过去,掉落到桥下,化作了浮沫,随水流逝……过桥即是老城广场,泰恩教堂黑尖顶的沉默、披檐阴影的青幽、栏杆窗台的明丽,全都坠落在亮白广场上。扬·胡斯塑像披着大麾、耸着肩,顶天立地,一大片黑色鸽影掠过,如风扬起灰烬,万国的人影都在他身边簌簌移动,聚合,散开,如星辰或流沙……环绕这个广场的,有卡夫卡的几处故居,他诞生的“塔楼”,写下《饥饿艺术家》的房子……若是沿河畔行,可一直走到查理大桥。圣约翰·内波穆克主教就在这座桥上被国王扔下河去,如今,他的雕塑立在被扔下去的那个位置,雕像的一角已被游人摸得溜光铮亮。唉!无论怎样平庸的时日,无论如何惊心动魄的人生,都如河水流逝,一去不复返了……
有些天,我们一大早登上山顶公园,那里有个露天餐厅,挑个可俯望伏尔塔瓦河的位置坐下,重读《城堡》和《美国》。上午的河水呈湖蓝,中午转成明绿,成片起伏的红色屋瓦中,不时冒出教堂的乌黑顶子、碧绿顶子,阳光满溢,云影转移,面光的河好似跳跃着无数银鱼。不知何故,即使是大晴天,这个城市也似乎笼罩着一层暗哑雾霭,一层诗性、忧郁的烟蓝。午后,半城年轻人都聚集在山顶公园餐厅,陌生语言在周围嗡嗡作响。我们起身,穿过草地和树林,顺公园小路,一直走到城堡去,走到城堡附近的霍特克维花园,那是卡夫卡经常散步的地方,他常带一本书,坐在树下读。
有一天,从城堡转回来,天已昏暗,河面黑蓝,只剩薄薄一抹夕光染出山下屋瓦的红,路灯也亮了,草地绵延着融进暗黑树林,归林的鸟啾啾叫个不停。我们坐在一棵花树下,紫红花瓣不时落下来,身上椅子到处都是。远处,那个露天餐厅灯火辉煌、人影绰绰……突然,低哑的二胡曲哽咽而出,穿破夜幕,如一个人在倾诉,一句一顿,时而幽咽叹息,时而缠绵悱恻,时而悲怆激越,情绪抑抑扬扬,节奏顿顿挫挫,如河水,在清晨、午后、黄昏,或柔情流淌,或如漩涡回旋,或遇礁石激起浪花。是《江河水》!在异国他乡,听见这支二胡曲,泪水瞬间涌出……斯美塔那结束流亡后,回到故土,磨难、病痛、孤独,没有减少他的爱与激情,他写下《伏尔塔瓦河》,这首深挚、宽广、诗性,沉郁而壮阔的交响诗,是献给二战后他那苦难深重的祖国。在这布拉格晚暮中,伏尔塔瓦河在脚下湍湍地流淌,缠绵哽咽的二胡曲,令我泪水盈眶——在这里,我终究是一个过客,一个漂泊者,一个异乡人。遥远的东方,那里,有我的祖国,我的故乡,我的父亲——
在黑暗花树下,在远处的灯光人影中,遥遥屹立的黑色城堡的上空,好似一片空洞虚无的幻景。我听不见黑暗的河水湍湍地流,《江河水》曲声却潺湲流淌在我的耳边、我的心中。在这二胡曲中,父亲的银白头发,清瘦多斑的面庞,深情温暖的眼睛,骨节嶙峋的手指,全都浮现在我的面前。我分明看见,在那湛蓝星空之下,在涌动起伏的伏尔塔瓦河之上,父亲搬一把凳子,端正坐着,二胡立在他的腿上,他一手扶着琴杆,一手颤动着弓弦,《江河水》曲声,在他的手指颤动间悲怆激越缠绵悱恻地流淌,他的身子随着曲声有节奏地俯仰,好似那起伏的伏尔塔瓦河水……
这首《江河水》,最早描述的是一个女子在新婚丈夫被抓去当劳役后,无助地在河边恸哭,滔滔河水,好似能带走她的哭声,宣泄她的痛苦。后被黄海怀改编为二胡曲,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第一场“苦难岁月”中作为配乐,二胡的喑哑、呜咽很能传达曲子的痛苦、凄婉、悲愤而又沉思的情绪,如泣如诉,催人泪下。父亲很喜欢这支曲子,每到内心忧愤不能自已时,就会拉这支曲子。我是听着他拉这支曲子长大的。
回国后,给父亲打电话。当时他听力尚好,只要我给他打电话,总会聊许久,似要将平日没说的话,在电话里一下子说完。我说:“爸爸,想听听你拉《江河水》。”听我说想听他拉二胡,还是他喜欢的曲子,父亲高兴地说:“你等着——”他将电话一搁,接着,好长一段时间,就听见电话线那端,拉凳子的刺耳声,翻动曲谱的窸窸窣窣,转动琴轸调音的吱吱嘎嘎,弓弦擦动琴筒颤出的几个试音,忙了好半天,中间是长长的空白,我耐心等着,知道父亲在酝酿情绪——好一会,一个幽怨、清凉、喑哑的曲句,透过细细的电话线,从父亲那端,传到我这端——
窗外,盛夏,明晃晃的烈日,猫在睡觉,鸟儿也躲起来。清凉、幽暗的二胡声,从电话线那端传过来,像幽暗、深沉的河水,慢慢地席卷过来,淹没了我。
二
寒露才过,山上早早下了霜。天空高远黑蓝,很小几颗星子,闪着钻石的光亮。一弯薄薄下弦月,如镰刀般,锐利,洁白。远山、近树,全都黑魆魆沉默着,收割后霜冻的稻田、茶园、弯曲的公路,泛着模糊的灰白,试图分割黑暗。在远处的黑暗中,闪现一二点灯光,传来一二声狗吠,表明那里有人家,但狗吠和灯光,也很快隐遁进浓黑混沌中。
农场的几排土墙平房,静静站立在天地间,微弱的月光勾勒出模糊影子。黑瓦上落下薄薄一层霜,在弦月下,清寂地泛着白光。鸡们猪们全都进窝了,只有一二只狗,踩着凝霜的泥地,孤单地无目的地走来走去。家家户户已闭门,几个小小的木窗户,透漏出昏黄灯光。
母亲和我已上床,捂在被子里,隔着蚊帐看父亲走来走去。卧房只有一盏15瓦带铁罩的电灯,薄薄灯光,在房间圈出一小块昏黄。父亲收拾完,闩好木门,倒了杯热开水,捂着搪瓷杯走进卧房。他取下挂在墙壁的二胡,搬了把方凳,对着小木窗坐下。父亲用松香反复擦拭着白色丝弦,一边调节琴轸,一边试拉了几下,直到音调准了,这才端严地坐直了身子,闭眼静默良久……我和母亲等待着……
一个喑哑的乐音颤抖开来,好似一个人长长叹了口气,接着,如怨如诉的乐音,在小小的灰墙锁住的空间回旋、辗转,浓郁得无以化开,似要突破木窗,飞到外面世界。这是《二泉映月》!长大后,我才知道这支曲子的名字,并了解到作曲者阿炳(华彦钧)的生平,也曾去无锡拜访过阿炳故居。父亲拉出的第一个乐句,是《二泉映月》的引子,这一句低低叹息,凝聚着阿炳几十年生涯的长长辛酸。年过半百后,我再听《二泉映月》,体会到更多复杂思绪:随乐句的潮起潮落,主题被反复变奏,传达出悲苦、沉思、骄傲,有时又是逍遥徜徉的情绪,是阿炳的自言自语、自我追问,他将自己对生命的追寻思考凝聚在这支曲子中;我听懂了它的悲苦,也听到它的诗性、沉思、追问;尤其是尾声,情绪由扬转抑,慢慢回落,越来越弱,细如游丝,意犹未止,满怀对生命的无限流连、无限惆怅。
父亲拉二胡时,微闭双眼,沉浸在阿炳描述的最底层最苦难的人生里,一如他所经历体会的。但年幼的我,尚不能理解《二泉映月》的主题,只觉得拉二胡的父亲很帅。我后来常常回想当时的情景,回想父亲拉胡的姿影——音乐在房间流动,鄙陋的日子,乏味的空间,沉重的生活,贫瘠的物质,因为这二胡曲,黯淡的一切似乎退隐了,小小的泥屋似乎闪闪发亮了。那是神的手啊,他恩惠的灵降到这个小屋,慈悲的手抚摩着沧桑劳累的凡尘的心,在这个瞬间,将美善、温暖的光亮和馨香的希望一起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