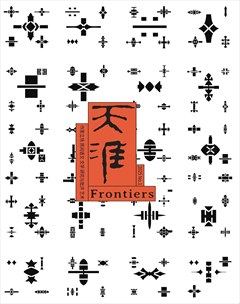一
2022年初,临近除夕的一个上午,父亲打来电话说医生告诉他确诊了肺癌,他的语速平缓,声调正常。在他退休之后,疾病就悄然尾随,连续两次脑溢血使他从对自己身体的极度自信中变得有所警惕,这次确诊也是脑溢血的愈后复查发现的。关于他之前的任何一次生病,都不是父亲第一个告诉我,总是医治有方了,信息才被允许传到我这里。我明白他不愿意使我陷入对疾病的恐慌和忧惧中,所以接到这个电话,我也没有露怯,用跟他一样的节奏和语气说,涪陵的医疗条件我不是太放心,咱们到重庆检查后再决定治疗的方案。
接下来就是在各个医院之间的奔波问诊,我像所有的患者家属一样四处打听相关资讯,再反复比对那些多方打听来的结论,终于决定采用陆军医院的手术方案。正月初十,父亲切除了左肺。主刀医生说虽然切得干净,仍旧建议我们送标本到基因公司做检测,以便决定后续的治疗方式。在等待结果的那段时间,父亲引流管的伤口一直感染,我不愿加重他的痛苦,就隐瞒了送检的事。检测报告出来,父亲的基因结果没有突变项。我从医生办公室回来只得跟父亲讲实话,因为没有突变项吃不了靶向药,只好采取化疗的办法,而且最好是术后四十天左右开始化疗,但现在他身上的伤口一直不愈合,化疗会加剧感染,就只有等伤口恢复再说。父亲说,他早已知道我送检一事,病房里那么多患友,人家都检测基因,怎么可能独独他不检测?然后说,既然要做化疗,躲不过就积极些,伤口怎样处理快就尽力配合。
于是,按照医生说的彻底处理好腐肉并加快清洗频率,父亲几乎隔天都要承受剪掉腐坏组织后黄纱条搅动清洗的疼痛,他说,剪就是了,我不觉得痛,尽量让它不再化脓。每一次,我都暗暗想,这是最后的疼痛了,后面一定不让父亲遭这些罪,其实哪里知道,这才只是抗癌之路的开始。
父亲对疼痛的忍耐,让他得以如期化疗。医生的计划是第一轮四次,每二十一天一次,差不多就是身体被化学药物攻击之后勉强复原就继续展开对癌细胞的歼灭。熬过了四次,我们就每三个月复查一次,到第二次复查的时候,父亲的癌胚抗原(CEA)指标就升高了。刚刚升高的时候,医生考虑到结束化疗才半年时间,担心马上用药父亲身体吃不消,就说复查时间缩短为一个月一次,随访再看。第一个月查CEA数据升高了一倍,CT检测一切正常;第二个月查CEA数据升高了两倍,CT还是没有异样。不能接受束手就擒的等待,这个阶段我又开始遍地寻医访药,得到的反馈也都和医院的说法接近,总是要我们自己做决定,激进一点就上化疗药物,保守一点就再观察。后来总算是访问到MRD(Minimal Residual Disease)的检测手段,说是可以通过检测血液中的ctDNA来判断体内是否存在癌细胞。联系了燃石生物科技公司,他们也说MRD可以比影像学更提前发现微小残留病灶。费用很高,即便是办一个终身套餐依然很高,可我只想做证明题,证明父亲到底有没有问题。一个礼拜以后,结果出来了,是阴性。我拿报告给父亲的时候,他说得把大家叫上吃一顿饭,这段时间周围的朋友很为他担心。
MRD的报告拿到手里还不到一周,父亲髋关节出现了疼痛,他认为前前后后搅得家里很不安宁,便安慰我说,这个疼痛不是大问题,关节痛有一二十年了。可是,疼痛迅速加剧,我们再到医院一拍PET-CT,全身多处转移。医生无力解释原因,找我谈话只是说打算在第一轮化疗药物的基础上增加免疫治疗,有国产和进口两种选择,关系到选医保还是全自费,因此要询问家属意见。谈话间一位父执来到办公室听到后,就回病房去和父亲讲了用药的事。我正准备签署进口药的使用同意书时,那位叔叔拍了我的肩头,告诉我父亲有话跟我讲。我以为出了事,小跑到父亲病床前,他用了一种不像病人的口吻跟我讲:“双儿,爸爸知道你要治爸爸的病,但是有些病治得好,有些病不一定治得好。我们这样的家庭,经不起重病的拖累。爸爸更不能给你留下许多负担。”没想到父亲突然说这些话,我原本就不打算告诉他PET的结果,现在更不能讲了。我心里急得想马上给父亲用上进口的药,还是沉着冷静答道:“不是不能治了,报告显示只是骶髂关节有转移,医生说进口药效果更好一些,我承担这个费用也不会产生爸爸说的那个影响。”他没有再坚持,后面听那位叔叔讲,父亲想的是当天顺着我,等到第二次使用他就去跟医生要求换国产药。他不知道我一下子签了两年的合同。进口的帕博利珠单抗在国内号称慈善赠药,它的治疗周期也是每三周一次,前四次使用自费,之后的两年内用药免费。其实四次下来的费用已经是天价,但抗癌家属的心情总是不惜一切代价,而且因为慈善的名义,就使得这个用药极其复杂,手续磨人,基本上用一次药,中间的三个礼拜都在为下一次领药完善手续,可我也不觉得麻烦。心里就是一个念头,即便治不好也要缓一下,万一能踩一脚刹车呢。
又是卡铂加培美曲赛二钠的四次化疗,另外担心癌细胞对股骨头的侵噬太快,给父亲打了一种保护骨皮质的地舒单抗针剂,每四个礼拜一次。父亲说,这个治疗是不是太多了,周期怎么这么复杂?我说现在是关键时期,咱们得咬牙打下这个硬仗,周期我记着的,你不用惦记。可是,这个硬仗没有随着第二轮化疗的结束而结束,一个月复查的时候,癌胚抗原又开始飙升,情急之下我背着他改了报告单,但瞒得了一时,却躲不过病魔的不断袭击。他越来越迈不开腿,连站立都使不上劲,整个大转子失灵了。父亲说,生点病倒是没什么,就是生活要能自理,但真的瘫痪了,那也是身体要受的考验。这不只是对他的身体考验,也是对我的考验,小敏说我已经把做科研的精神用在了给父亲治病的事上,一年多来我不止一次地想过,当初如果不是学中文而是学医,是不是会更好。虽然无法弃文从医,但我还是拼命学习各种医学文献,只想着和时间赛跑,能够更早了解到癌症下一步会怎样摧毁一个人的身体,我就能够为父亲做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抵御。
在亲友的极力推荐下,父亲喝上了中药。我从几百公里外拖回一麻袋多的药材,父亲说喝就要信,信更要喝。我也说,一麻袋应该就有起色了。父亲是带着信念在喝药,但喝到一半的时候,他的消化系统就开始出现问题,我也不能说是因为中药副作用的缘故,定期检查癌胚抗原的结果我还继续做着手脚,希望让他保有信心。父亲说,管一点用也是管,药还是得喝,有点不舒服免不了的,治病本来也不是为了舒服。就在我饱受煎熬,不确定是不是放弃中药的时候,父亲突然半边身体制动,我担心是脑卒中旧病复发,连夜送到急诊,折腾半晚上得知是脑转移。原先本有准备,我知道转移总归是拦不住,但癌细胞怎么一下子随机到大脑了,我的脑袋也轰的一声。可已经开始欺骗,只能继续欺骗下去,我以治疗脑卒中诱发脑水肿,并辅助控制股骨头癌细胞的破坏为由,再次把父亲送回肿瘤科。
这次医生没有制定新一轮的化疗计划,只是说我们先试,如果有疗效就继续。他们采用了中枢渗透性较好的替尼泊苷做化疗,希望能建立起血脑屏障,再辅以贝伐珠单抗做抗血管生成的系统性治疗,半个多月下来,继发性脑部恶性肿瘤压迫神经的问题得到了缓解。父亲能够抬起手臂,活动指头,他不断地给我演示,表示说脑卒中问题解决了。因为疗效还好,医生建议我们连续做三次完成一个疗程,仍旧是二十一天一次。在两次之间,父亲开始脱发,他说前面我就在想,没有掉头发说明药效没发挥,现在头发掉了,药效假不了。剃发后,他变成了标准的化疗头,父亲摸着头皮说,再长起来的时候,正好下一次就开始了。
没有等到下一次,父亲以谁也没有料到的方式,突然就结束了我们准备打持久战的抗癌马拉松。我知道最终的结局,但是我也被死神提前终止这份生命契约弄得愤怒、沮丧、无力而无助。
二
听父亲讲述他最早经历的死亡,是关于他的打柴同伴。他说爷爷奶奶是反对他去打柴的,主要还不是因为十二岁的父亲挑一担柴几乎和柴捆一样高,更重要的是打柴的地方山高路陡往返六十多里很不安全,可父亲还是和马武场上年纪相仿的孩子约好,先把打柴的工具藏在外面,再若无其事离开家门,以此避开大人的管控。有一天下山路上忽然听到身后嗾的一声,等他回身去看的时候什么也没看到,只听见柴刀一直往深涧下落不停撞到山岩的声音,声音从清亮变得轻微,最后再也听不见一丁点声响。打柴摔死人的阴影并没有持续多久,父亲和小伙伴又上了山。我问他,砍的柴是自己家里用还是卖了换钱?他说大多数都自己烧,偶尔也卖点钱,很少,卖的钱攒起来最多的时候有一角,拿一角钱给家里面的感觉就比卖柴时赚一分一分的感觉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