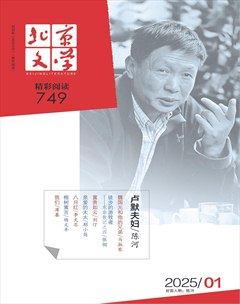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男人,生活总是停留在少年般的天真与倔强中。他的世界就像一块块破旧的泡沫板,虽被他用诗与画精心装点,却始终无法逃避生活的磕碰与磨难。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个懂得欣赏他的人……
理想成从梦里醒来,拉着了灯。
灯一亮,房屋紧跟着亮了,院子从黑暗里浮现出来。卧室的窗户正对着东屋的北山墙,墙的中间部分是温暖鲜亮的鹅黄色,下半部分和屋顶是柔和高雅的灰。天空是蓝紫色的,地半睡半醒,被晨曦和光影调制成了斑驳的复色。
胡同里传来一阵尖叫声。理想成瞥了一眼墙上的月份牌,这才知道,今天是星期六,孩子们不上学。要照往常,娘会走出家门,对着孩子们一声接一声地喊:
慢点儿,慢点儿,脚下长个眼儿,别摔着喽。
孩子们玩多长时候,娘就喊多长时候。这一回,胡同里只有孩子们呜哩哇啦的喊叫声,没有娘一声紧接着一声的喊吵。
每天早晨睁开眼,理想成都感觉是在梦里。哇,阳光多么柔软啊,像是小猫,翘着毛茸茸的尾巴,跳到东,跳到西。而这个家,是多么的新啊,屋里,院里,一切都是新的,就像是刚从大地里生长出来的花骨朵。
唉,娘哩,要是娘还活着,能看到这些就好了。理想成的鼻子有些酸,眼里腾起一片雾水。
“丢了母亲丢了魂,活得像个小纸人儿,找不到心,找不到肺,找不到眼睛流把泪……”
理想成突然想出了四句特别棒的话,就把它写到床头一个巴掌大的纸片上。
他胡乱洗了把脸,刮了刮胡子,拿起剪子对着镜子咔嚓咔嚓给自己理起了发。
理想成从来不大嗓门喊吵那些孩子,他觉得孩子们跑正常,栽跟头正常,就算头上碰个窟窿也正常,要不然就不是孩子了。
村里会说话的小孩儿都知道理想成,一有时间就往理想成家里跑。孙旗辆大半年没来,进到门口觉得像明山家,一看院子和北屋觉得不像,就站在门楼下喊道:
明山,明山,这是你家呗?
理想成姓李,叫明山。理想成是李明山的笔名。说是笔名,其实最开始是QQ名。理想成在省城学手艺时,在网吧给自己申请了个QQ,名字叫理想成。后来一想,自己姓李,干脆笔名就叫理想成吧。
理想成爱画画,爱作诗。理想成的画下面、诗下面都署名理想成。烟盒、方便面箱子、生日蛋糕盒子、白色的泡沫板,理想成逮住什么使什么。理想成家里的纸板泡沫板一摞一摞的,上面到处是理想成的诗和画。
孙旗辆把咬了两嘴的梨扔了,理想成一看没人,就把梨捡了起来。理想成问孙旗辆,你吃呗?孙旗辆说,不吃,都脏了。理想成拿着梨找小刀,一点儿一点儿往下削。下课了,孙旗辆从学校跑出来,理想成再问,你吃呗?孙旗辆说,吃。后来理想成作了一首诗:找个破门就当船,找个烂梨就解馋,找个旧衣就避寒,找个茅屋就睡眠。
有人问理想成多少岁了,理想成说,俺还小哩,才不惑。那人哈哈一笑,还不惑,分明是个永远也长不大的老小孩儿。村里的男女老少,上至八九十岁的老人,下至刚会说话的孩子,人人都喊他明山。没有人知道他的笔名理想成。
其实明山这个名字也不赖,这个名字是村里的医生他爹给起的。医生他爹说,属虎,虎不离山,就叫明山吧。
理想成举着剪子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一首诗像是一只小松鼠,从他的脑海里蹦蹦跶跶跳出来:明山手艺高,剃头不用刀,一根一根剪,剪成电灯泡。理想成觉得这诗不赖,赶紧放下剪子,找来一个废纸板,把诗记了下来。
“明山,明山,咋变了?这是你家呗?”孙旗辆这次不是喊,而是尖叫。
理想成歪着剪了一半的脑袋看向门外。
“你说哩?”
“俺看大门口像。”
孙旗辆在里间屋转了一圈,外间屋转了一圈,竖起大拇指说:“明山,你真牛!”
又来了几个小孩儿,其中一个说,这么好的房子,就你一个人住?另一个小孩儿说,养几个孩子。
理想成前年还住在西边的两间小破屋里,没了老人后,才挪到东边。东边的三间也是小破屋。屋里顶着几根柱子,小孩儿们捉迷藏,扒着柱子跑来跑去。理想成作了一首诗:屋里顶着几根柱,扒着柱子跑猫步,别扒别扒快停步,怕这屋顶撑不住。
孩子们在院子里跳绳,打秋千,挖地道,抱柴火给理想成做饭。
盖了新房后,孩子们在院子里踢球。理想成说,别把玻璃碰坏喽。孩子们扭头走了。孩子们在屋里这儿捅捅,那儿动动。理想成说,别给俺动坏喽。孩子们扭头走了。理想成叹了口气,唉,还不如住在原来的小破屋里哩。
春天里的一天,理想成被叫到村委会,村支书李菜包指着坐在会议桌旁的一个圆头圆脑的男人说:
“明山,这是县纪委的史书记——史红旗。史书记是你精准扶贫建档立卡的责任人。今儿个找你就是想具体了解一下你的情况,请你签个字。”
理想成一脸蒙圈,看看史红旗,再看看李菜包,眨巴着眼说:“支书,你不知道呀,俺没吃低保。”
李菜包说:“我知道你没吃着低保,这回是精准扶贫,跟低保不低保的没关系。”
“明山,不好意思,我这样喊你行呗?哈哈,我听说村里的人都这样喊你。”史红旗站起身,向理想成伸出一只手。
理想成愣了一下,把自己的两只手在衣裳上擦了擦,一把抓住了史红旗的手。史红旗的手真热乎,理想成的心里跟着涌起一股暖流。
“史书记,还是您懂俺,喊俺明山就好。”理想成声音里有些颤抖。半辈子了,理想成从来没有跟人握过手,今天握住眼前这个男人的手,理想成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握过手,他在史红旗对面的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
“明山,你现在生活过得咋样?”史红旗说。
“不赖!不瞒您说,现在的日子,那可以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以前,要吃没吃,要穿没穿,现在哩,您说老百姓什么没吃过?什么没见过?”
李菜包插话说:“史书记问的是你的收入情况。”
理想成吐了下舌头,犹犹豫豫地说:“收入……俺现在种着三亩多地,地流转出去了,一亩地一年八百……”
李菜包说:“这个先不说了,你给史书记说说除了地流转的钱,还有别的进项呗?”
理想成挠着头想了一会儿,说:“没了,一下子想不起来还有么,过去还摆点儿摊……”
史红旗说:“明山,你的情况我们基本上也了解了一些,听说你有残疾证,是几级?”
理想成说:“三级。”
史红旗拿出一张纸,又拿出一支笔,说:“明山,来之前,我们已经研究过了,你已经够精准扶贫的条件了,你在这里签个字,过几天我们再来,到时咱一块儿商量一下具体的脱贫办法。”
理想成像是屁股下着了火,腾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史书记,您的意思是……俺……是贫困户?”
“对。来,明山,你在这儿签个字……”史书记把桌子上的一张纸往理想成面前推了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