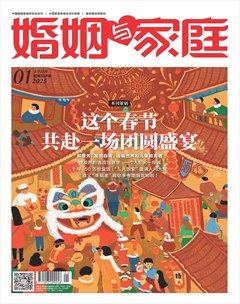无论是从前选择学物理,成为科幻作家,获得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还是入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做策划研究,抑或是如今作为教育项目“童行书院”的创业者……郝景芳的每一次出发,背后总有着相似的原因。
“景芳老师,你的科学经验能分享一下吗?我长大后想当发明家。”
“如果想当一位科学家,你得有一个特别好奇的问题。它可能从生活里来,可能从你看的书里来。比如,我特别好奇量子力学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有不确定性,就去学了物理。如果想当一位发明家,你就得考虑别人需要什么,我发明什么能帮助别人,或者这个世界需要什么,我发明什么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面对孩子们天马行空的想法和问题时,郝景芳从不觉得厌烦。她总能结合自己的经历,极富耐心地鼓励他们拥抱梦想,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实现梦想。这是她身为母亲努力在做的事情,也是她自2017年创立童行书院后,努力为更多3~12岁儿童做的事:通过系统性的通识教育课程,激发孩子们的志向和憧憬,指引他们发现自我、探索世界。
自然长大:开放式教育让她自由生长
出生、成长在天津这座工业气质鲜明的城市,郝景芳的童年生活可以说是极富秩序性的。“全市都是红砖6层小楼,我和同学们住着一模一样的房子。”郝景芳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这些“表里如一”的建筑里,第1段台阶是12节,第2段是6节……
郝景芳的父母是那个时代少有的大学生。毕业后,他们在天津财经大学工作,郝景芳便顺理成章地在大学的家属院里出生、长大。
彼时,爷爷奶奶还没有退休,爸爸妈妈又要上班,从3个月大起,郝景芳就在托儿所过上了集体生活。离家不远处有一所很普通的小学,因为近,成了大院里几乎所有孩子的“母校”。
街坊邻里都是熟悉的人,孩子们自小便一起组队上学、放学,今天去这家写作业,明天去那家玩儿,或者一起在院子里跳皮筋、跳房子、拍洋画。等到爸妈下班,才将他们一一喊回家吃饭、睡觉。集体活动的占比过高,让郝景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小家”的概念。
身为大院里的“孩子王”,郝景芳经常带着大家四处冒险。虽然调皮,但她造成的伤害仅限于自己:不是胳膊磕破了皮,就是腿摔坏了……父母的开放式教育,给予她深深浅浅成长印记的同时,也给予了她无限成长的空间。
学了两三年钢琴后,郝景芳想放弃,妈妈也不强迫她坚持,同意她把时间都用在喜欢的阅读和画画上。
比起学习,父母更注重她的生活习惯、品行的培养。小学期间的一次期中考试,语文卷子上有一道题不会,郝景芳偷偷翻书找了答案。妈妈知道后,郝景芳得到了成长中唯一一次的打手板。“她说,考试的时候你不能翻书,这个叫作弊。我希望打你一次,你这辈子都能记住。”
从小到大,郝景芳一直是自己做决定,不论是选专业、转学,还是创业,父母都鼓励并支持她掌握自己的人生方向。
仅有的一次异议是在她14岁那年,父母要调到北京工作,郝景芳却想留在天津。
“我自己去查怎么租房子,如何生活,等等。我跟他们申请说一个人在家乡租房子。父母说不行,毕竟我才十四五岁,他们不太放心。”郝景芳如是说。
争取了再三还是没能成功,但有想法就去寻找可行性方案并第一时间付诸行动,成了郝景芳此后的行事准则。
郝景芳说,妈妈对自己的言传身教最重要的两点是诚信和关心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