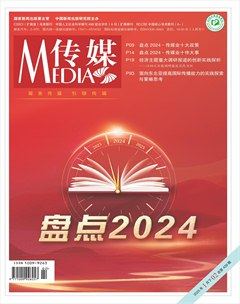摘要:当代电影的媒介性表现为其时代负载、文化想象和现实隐喻。身处地缘战略中心之一的东北亚,其电影恰当地承担了“软性媒介”的文化角色,“调和”了地区政治纷争,弥合了族群矛盾,以强大的情感力量介入区域公共生活。这类电影弘扬人的善意、情感与共有价值,捕捉生命中的共同性元素,这使东北亚电影的软性特质化合效应显著,其人文蕴含为当代世界纷争地域的艺术沟通、文化同频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关键词:东北亚电影 软性媒介 地缘文化 亚洲新电影
媒介视角的当代电影是沟通人类心灵空隙的桥梁。作为全息视听艺术,其感性、流动和具象,以三维的运动画面在时间轴上给人们以“现实”和“历史”的经验,由此向观众传输某种价值观、人生观以及对特定社会生活的情感肯定或否定,带来全方位的身心慰藉和洗礼,进而引向对人类共同情感价值的追求。东北亚属于复杂而敏感的区域,在这样的地缘文化语境里,东北亚电影发挥它作为“软性”媒介的作用,透过中日韩三国近而不同的历史记忆、地缘文化和毗邻优势,勾勒东北亚现代社会的视像颗粒,促进东北亚地区政治和社会化合与交融。
笔者所说的“软性”,指的是一种基于情感和人性的立场,也就是人文性的电影自觉,它从日常视角、从人类共同的境遇及其感受出发,以自然和平的心理审视人的遭遇及其命运,慰藉大众。通过这种“软性”方式,电影能够诉诸“人同此心”“将心比心”“以心换心”的路径,捕捉生命中、生活中的共情点,能够让观众体认那些矛盾的、复杂的、多样的,甚至是另类的事件、境遇、情感和观念。而当电影深挖其“软性”的一面,在更加亲和包容的叙事空间里展现更具人性和人道而非对立和仇视的内容,将不仅有利于电影的艺术表达,亦有益于发挥电影的文化效能和社会政治性效能,使电影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对话、情感交流、命运与共的具有政治化解力的艺术载体。
由此出发,笔者审视东北亚电影作为“软性”媒介的意义,把目光投向那些在中日韩三国间搭建起心灵桥梁的银幕作品,即看到其间“软性”的成分是如何在由历史沉疴、政治压力、民族隔膜和文化龃龉构建的复杂东北亚地缘环境中起到宽慰社会、消弭仇怨、温暖人心的巨大效果。
一、“软性”之由:东北亚电影与地缘性历史积沉
以中日韩为核心的东北亚地区不管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还是经济舞台上都是夺目的焦点。从大陆到半岛再到岛国的历史漫游已经在这片区域内描绘出独特而复杂的关系图谱。一方面,地缘纽带加强了东北亚各国的联系,构成了东北亚自成一格的文化风貌。另一方面,沉重的近代史以及现代化历程中产生的纷争与矛盾又在一定程度上筑起国家间的民族主义高墙,阻碍区域共识的形成。因此,东北亚各国的文化传播动向和文化交流程度不单纯受掣于本国的国情国力,往往还紧密寄依于彼此政治关系的松紧。
就电影艺术而言,历史上东北亚电影文化交流情况大致可分为“早期交流—战时交锋—战后交错—再度交好”四个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日本接触西方技术的时间较早,中韩两国影人常有留日背景或受到日本影片风格的影响。例如,《定军山》导演任庆泰就曾于1874年自费赴日本深造摄影技术。1910年,日军占领朝鲜半岛,1931年日军侵华,随着战争的进行,东北亚紧张的局势致使各国电影交流形成错综复杂的局面。日本为推行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加强对占领区人民的思想控制,于1937年在中国东北起建“满洲映画协会”,由甘粕正彦出任理事长,下设养成所、映画科学研究所、大连出张所、奉天出张所等,服务其“大东亚共荣圈”的政治宣传。在朝鲜土地上,日本审查严苛,不断镇压由朝鲜无产阶级艺术家同盟主导的卡普电影运动,并于20世纪40年代颁布“朝鲜电影令”扼喉朝鲜影人。
但同样是此期,东北亚各国影人的交流也并没有因为民族关系的紧张就此停滞。在“电影救国”的呼声中,中国影人罗明佑、黎民伟和关文清希望用日本的先进经验和技术来提升国产片的制作水平,上海有声及左翼电影的历史里也留下了日本影人川谷庄平、小谷亨利和岩崎昶的身影,川喜多长政与张善琨一同重组上海电影业,成立中华联合制片公司。另外,朝鲜半岛内政治局势的黑暗及电影生产环境的恶劣也让众多朝鲜影人出走中国,寄寓于中国上海。李庆孙、韩昌燮、郑基铎、全昌根等朝鲜影人形成了有鲜明创作特色的“上海派”群体,朝鲜民族现实主义路线代表李圭焕也曾师从丰田四郎、沟口健二等日本导演。
战后,中日韩三国的电影交流受本国政策影响呈现出相对顿滞的状态。特别是朝鲜半岛禁止“倭色文化”,电影多拍摄日殖时期人民的苦难生活和抗日运动等题材,反对日本文化的输入。中国与日本的电影交流未断,今井正的《不,我们要活下去》(1951)曾在中国公映。但在大陆总体政治环境不断增压的情况下,与日本电影的商业化交流更多存在于中国港台地区。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东北亚地区经济形势向好、政治关系改善,东北亚各国的电影交流再度频繁起来。日本电影《情书》(1995)、韩国电影《生死谍变》(1999)、中国电影《那山那人那狗》(1999)等都走出国门,在东北亚邻邦获得热烈反响和欢迎。
回顾东北亚电影的交流历史不难看出,即便在最严峻的政治局势下,各国影人都出于技术革新或产业发展的需要,不断地为获得他国优秀电影创作经验而付出努力,都以电影为媒介,反映着区域社会生活和情绪;而在传达自我民族意志的同时,其也在倾听他国的声音和故事,共塑着东北亚文化记忆。更重要的是,这背后蕴含着一股与对立和仇视的意识形态相撕扯的力量,无论是在混乱的战争年代,还是在民族主义情绪弥漫的时期,都持续蓄发并引向交流互通、殊途同归的趋势。这也意味着东北亚电影作为当代的一种“软性”媒介,在东北亚文化空间里蕴含着深厚的根基。
首先是历史根基,东北亚各国在相接相近的地理环境中有着天然的文化亲近感,基于儒家文化而拓展的传统东方文化在中日韩三地生根发芽,由此形成东北亚各国的“近文近种”,造就了文化艺术的某种高度的“同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