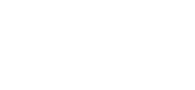一
对于家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宋小芙来说,男女只分两种:结了婚的和单身的(包含离婚丧偶的)。这一套分类标准能直接套用。只要当事人打立案诉讼服务大厅一过,除了安检“嘀”一声,宋小芙的脑海也“嘀”一声。眼睛上下一扫,猜个七七八八。这跟她目前处在适龄年纪,业余活动只用来相亲关系极大。
童安市是个四五线小城市,在祖国大地上面目模糊的那种。一个小城市装载的娱乐项目极少,除非她去广场上练健身器材或者干脆破罐破摔,在二十七八岁的年龄迷恋上集体舞和太极拳。但宋小芙感兴趣的是婚恋,她自己被迫“挂牌上市”,被父母耳提面命着,频繁相亲,待价而沽。尔后,她被分到家事审判庭,做周大方的法官助理。
在童安法院,鄙视链很隐秘地存在着,威严的刑事法官瞧不上终日家长里短的民事法官——哪怕具体到民事里头,也有鄙视链,搞知识产权的看不上整商事的,整商事的瞧不上审建工合同的,审建工的瞧不上辨侵权的,辨侵权的看不上家事庭的——太琐碎也太不符合法官这威严面目了吧。结果,宋小芙来的第一天,周大方就开始给她洗脑:“谁说民事家事不重要?他们刑庭的,可能这辈子除了审案子,就不会用上《刑法》,可人们一睁眼,只要喘气只要活着,那都是《民法典》管着的!你呼吸的大气、你踩的草皮、你吃的食物、你买的东西……哪一个不是它管着?嗯,你嘀咕什么呢?”
宋小芙声音挺起来了:“我说,这都是知识产权庭和环境资源庭审的,跟咱们家事审判庭有什么关系?”
周大方这就要发作了——他脾气不好,终日让这些案件纠缠的——嗓门儿刚拔起来,书记员小帽儿就慌慌张张地钻进来:“咱们的熟人来了,快啊!快!”
周大方紧张了起来,他紧张的下意识反应就是缩脖子,耸肩膀,忙站起来,冲出去。这熟人不是别人,不是外人,是周大方老家出五服的同族,叫周酽。常年信访户,跟上班似的。一早坐班车颠颠簸簸来法院,先在传达室等,等周大方开完庭,等他把他请进调解室。好嘛,在调解室一坐就是一上午,没别的,就是聊聊最近的心路历程。他不能不聊,因为他没人可聊。为什么没人可聊呢?因为周大方二审判他离婚,他孤独了。
周酽的妻子老来俏,跳广场舞跳出了新好。当时他死活不放,说离婚就喝老鼠药。但周大方看女方已跟对方合铺,这对夫妻也分居五年有余。当时合议庭也考虑到周酽情绪不稳定,真判离了,说不定就成了信访、闹访、缠访户。但周大方不信邪,一边出判决一边劝他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周酽不干了,扬言:“你要是判我离婚,我就天天找你去!”
这不,他来法院“上班”了。先把午饭放在一楼水箱上面加热着;接一杯水,吸溜吸溜地喝茶;在调解室吹着风,一条腿还颤颤地弹着。周大方劝他:“您老回去吧,人家都领证了,强扭的瓜不甜,您在这儿有什么用呢?”
周酽说:“你把我老婆判没了,我没人说话,我就过来跟你说说话。”
从他身上,周大方看出来了,“说说话”也是有杀伤力的——相当于小型炮弹。调解室是透明的,但凡睃见穿法袍或制服的经过,周酽就腿脚麻利地站出来,跟人喊冤——“多冤啊,五六十岁的人了,给判没了媳妇。儿子呢,向着他妈,也瞧不起爸,这下好了,以后跌倒了没人扶,病了就等死喽。”边说边用叹气和泪水做伴奏,很是哀怨了。院领导每周有接访日,约谈过周大方,让他想办法解决老人的后顾之忧,又给他上了一堂“判决不是简单地一判了之,要注意社会效果、法律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统一”。意思是,他机械办案、简单粗暴——这下换周大方冤屈了。他嘀咕着:“闹就有理吗?”转而望见了宋小芙那张刚刚毕业、童叟无欺的脸。从那以后,陪上访户聊天成了宋小芙的工作内容之一。
周酽上下打望宋小芙:“你实习的?”
宋小芙说:“大爷,我是新考来的。”
周酽把腿高高跷起:“你跟着他能学好吗?你看看他怎么办事——啊,让我这把年纪无家可归,无家可归啊!”愤慨过后,转而又叨念,“你结婚了吗?”
宋小芙说:“哪有空啊,这不白天听您诉苦,晚上加班草拟裁判文书嘛。”
周酽一听,有意思了,小姑娘看着柔弱,还挺伶牙俐齿的。他打听她多大,家里几个孩子,住哪儿,父母做什么工作,想找个什么样的人。
宋小芙站起来:“大爷,您调查我的户口想干吗呀?”说完把头发一甩,抱着笔记本就回办公室了。
刚进门,就见周大方正端着杯茶顶着窗户,她的怨气就冒出来了:“周庭,你不是说你有庭让我去接待,可你这不没庭嘛!”
周大方说:“你看窗外!”
宋小芙就踮着脚,打眼一望,又疑惑地瞅他。周大方笑说:“多大的雪啊,大雪封路,当事人来不了,调整时间了。”又叹了口气,“怎么公交车还运转呢,也没耽误上访户过来啊。”
宋小芙把周大方摞在沙发上的一摊新分案件稍作整理,说道:“我知道他不容易,但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周大方说:“你忍着点儿吧,既然来了这儿,你就得学会多站在当事人角度考虑。”
宋小芙说:“那个大爷调查我户口呢,问得细着呢,我都害怕了。”
周大方停下来,忽然很神秘地笑了笑,说:“我看这老周闹访快闹够了。”
下午又开了两个互联网庭审。看来雪不仅压路面,还压网线,一会儿原告掉线,一会儿被告下线,一会儿代理人黑屏。音量不均衡,全程靠喊。下了庭审,周大方感觉透支了当天全部的说话欲望,准备回家就当哑巴。
但宋小芙不行,她晚上还有个相亲局。
二
童安市是个既普通又不普通的小城市。人们都是熟人,百里都是街坊,就像结婚久了,既彼此需要,也彼此厌恶着。它的婚配市场同大部分城市没两样:男多女少固定化,但女人难找常态化;一胎嫌少,二胎正好。在这样的童安市,女人的鲜亮又不是全靠外表,而是要透过现象体察本质——看子宫坚韧的程度。但男人就是要既保鲜又坚韧的,所以有的女人总得“开膛破肚”两三回,堪比赴汤蹈火、两肋插刀。童安市的大爷大妈们会在跳完广场舞的角落里竖起千篇一律的相亲角。白纸、黑字,年龄、家世,仿佛契约和军令状。街坊邻里胜亲朋,小道消息飞散密。傍晚,他们交换隐秘信息。宋父早就提醒了宋小芙,要行成人礼,就先得跟婚姻过招——对方是童安市人民医院妇产科大夫,比宋小芙大三岁,被学业和工作耽误了终身大事,现在功成名就,只等贤妻进门。
那人坐下后,睨了宋小芙一眼,看了看腕上的表:“我妈不喜欢爱化妆又聒噪的女人,你这样真挺好,符合我妈的标准。你单位那儿忙吗?我跟你讲,结婚后,最好辞职。这工作不养人,我们家挣的钱够了,娶媳妇就在家里生儿养女,相夫教子。现在政策放开了,多生点儿,咱都养得起。”说话间,他把手折叠出三个指头,宋小芙忍了,半天没说话。或许是见她表情不好,他夸她,“我看你很旺夫。”
宋小芙忍不住回道:“我就是我,旺什么夫!”
对方皱眉:“现在就是女权讲多了,离婚的才多了。你不是在家事庭吗,你说,是不是离婚变多了?”
宋小芙接嘴:“离婚的多了,那是因为大家都想明白了,没必要凑合,我认为是社会的进步。”
龙虾光盘,甜点消失。对方说:“进步?我怎么觉得是退步呢?现在动不动都闹离婚,一点儿苦都吃不了。”
宋小芙说:“你的意思就是想再过那种女人甘愿付出牺牲忍受的日子呗,男人不改就让女人改,想得真是美,还说都是因为女人‘合适干’!”说完,她立马后悔了。
对方还沉浸在自己的深谋远虑中:“我妈身体不好,原本我想在齐城发展,只好回来了。她的心愿就是尽快抱上孙子。吃点儿中药,一调来一对。”
宋小芙冷笑:“最好是一男一女喽?”
对方说:“俩男孩也行啊。”
宋小芙站起来了,从兜里掏钱,放了一百块在桌子上,马尾一甩,大步离开。听见身后“喂喂”,她加快步子逃离。她反思,童安市离婚率飙升跟女性觉醒有关系——是必要不充分关系。但又不能因此就不让女性觉醒——那才是绝对退步。社会正经历阵痛,总得有一代人去适应这件事情。她心情略微灰暗,回到家也是没好气地爬上了床。
第二天刚开完庭,书记员小帽儿又来报告,说这次来的人不是周酽了,是周酽家亲戚。宋小芙用眼神求助周大方,对方还在跟电话里的人缠磨——俩当事人为了抚养费五百元还是五百五十元吵个不休。宋小芙只好先去了。
她先看到了一个跷着腿的男人。对方抬起头,模样里有上访户的影子。对方问是宋小芙吗?她坐下来,问有什么诉讼请求。那男人便自我介绍,是周酽的儿子周正阳,他老爹让他来提交材料。
看上去还是信访件,但这次收件人不是院领导,不是纪委监委,也不是审判监督庭。上面就写着:给宋小芙法官。信还密封了。宋小芙说:“给我又有什么用呢?都二审终审了,再说那边都结婚了,总不能撤销人家结婚证吧?你爸——”她想说什么,又欲言又止。想必父母离婚再结婚,对儿子也是种羞耻。周正阳样子很勉为其难,交完材料还不走。宋小芙问:“你还有什么事儿?”
周正阳说:“没事儿,我就是不明白一件事情。他说只要我往童安法院这儿跑十趟,找你递交材料,他以后就不信访闹访——放过我妈了,这理由很奇怪。”他打量了她一下,“你们为什么让他跑十回?不是说一次性办好?”
“我哪儿知道啊!”宋小芙喊,“你老爸快黏上我们周庭长了,让他还老婆。你父母常年分居的条件,而且你妈——不好意思,反正你也知道那个情况。”
周正阳说:“没关系,我听你说。”
宋小芙说:“我也没什么说的了,你也别来送材料了,劝劝你爸,让他也可以再找个女人什么的。”
周正阳就笑了:“谁还需要一个脾气这么坏的糟老大爷啊。”
宋小芙摇摇头:“劝劝吧,法官不是保姆,不能包办一切,对吧?”电话响了,立案庭又让她去抱新分案件,她叹口气往回走,顺便拆开信封,里面的字是小楷,样子很工整:
小芙同志你好!我看你是个好姑娘。给你送信的人是我儿子——别担心,他跟他妈一个路子,一点儿不随我。他在童安大学做老师,教文学,很怕我给他丢人,但那是我自己的权利。他33岁,未婚。你们多聊哈。
宋小芙脸热了,像刚在冰天雪地受了冻后又进了屋——脸燥热,烧起来了。她收起信。立案庭于楠瞧见了问:“怎么,相亲失败?”
宋小芙说:“切,是对婚姻看透了,失望!”
于楠说:“别啊,去刑口看看——你猜怎么着?你会对人生失望。”
三
周大方坐在审判席上,他在憋尿。案子已审了三个小时。一般开庭,他都减少喝水,争取“一锤定音”。但今天两位离婚当事人都反常。怎么呢?他们不急不躁,你一言我一语,好声好气地商量,一套房给谁二套房给谁车给谁车库给谁冰箱给谁沙发给谁电视给谁,不像是爱多深恨多深的当事人——甚至比旁边的代理人还不急不躁,一笔一笔谋划得清楚。周大方忍不了,敲了法槌,暂时休庭。
他出来,抽了根烟,插空看了下手机。十八个未接电话,陌生号码,当事人的、代理人的、单位的、个人的。不用想,每个电话打过去都是一种绵长的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缠。周大方感觉自己这份工作已经不神圣了,简直是卑微的,每个来打官司的当事人,情绪都易碎。你要小心轻放,你要温情呵护。
如果想判得深入人心,先要学会换位思考。而你换位思考,就会深刻感受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悲哀,似乎判离和判不离,都有人受伤。以前想得简单,为了孩子,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但家事审判庭最近又新挂牌成立了“未成年审判庭”这么个内设机构,一下涌入了太多未成年刑事案件,都是第一手资料。看了,又令他格外神伤:那些被勉强在一起的夫妻扔在老家的留守儿童,缺乏了一种感受爱和施与爱的神经,他们对爱和共情不敏感,于是麻木,更可怕的是残酷——极易铸成错误。流放在农村的土地上或者城乡接合处的简易棚,无人依靠又满目疮痍。可你又能为他做些什么呢?普法有用吗?有用!教育有用吗?有用!社区治理有用吗?有用!但,统统治标不治本。谁也替代不了父母。可是父母就有错吗?为了维持生计,远离土地,奔走他乡——是一种迫不得已,他们错在哪儿呢?
老同事赵朴鲁劝过他,既要当好“体验派”,又要学会“好好抽离”,及时放下,案子过去了就过去了,别纠结。就尊重法律,就尊重证据,然后判吧!别太忙着去听苦处,因为你解决不了,你什么也解决不了!妈的!家事嘛!
屏幕又亮了,是助理宋小芙。看到这个名字,他就想起那张满怀着法律理想的稚嫩之脸。天真也是一种福气!嗬,这小丫头还没吃过苦呢。他笑笑,接了电话,宋小芙的声音挤压过来:“周庭,我都有心理阴影了,今天又一对六七十岁的大爷大妈在立案庭这儿闹离婚!我劝得嘴都起皮了。您看看能诉前调解吗?要是让他们立上案,我怕又是信访钉子户。”
周大方叹口气:“小芙我这还没开完庭呢,你先问问什么情况,尽量先调解,撑住!”
宋小芙对“撑住”这个词有她别样的理解。童安市不是一线城市,不是二线,是个三四线,甚至接近五线水平,GDP在全省排倒数,就这样——离婚率倒是很赶潮流,稳步并轨了一线大城市,居高不下。她刚来就跟着周大方参与了童安市诉讼离婚情况的调研,这才知道这小城市的离婚案子一年就得六千多件——有那么多人急着摆脱婚姻,好像结婚是一种标签,只要给自己贴了就好了,哪怕将来撕掉,身上也是有过了标签,适用一生了。
离婚率在各个年龄段几乎达到了平均分布,而女性启动离婚诉讼达到60%以上——宋小芙对这个数字有了欣慰之感,说明小城市的女性也开始觉醒了,能经济独立,还有了自我维权意识;年轻人离婚率比大城市高——说明童安市这种小城市晚婚还没波及得太彻底,也侧面提醒了宋小芙,再不考虑终身大事,似乎很快就要从婚恋市场出局了;三十岁到五十岁社会中坚力量离婚的,占据了半壁江山——很好解释嘛,工作和家庭两座大山一块儿压下来,都是亚健康状态的肉体凡胎,扛不住啊。但整个调研报告中,最诡异的部分是:六十岁以上的夫妻离婚激增,达到了往年的二十倍——童安市老人变得不安分起来了,是全球变暖让人们变得更燥热了吗?
调研报告中,周大方法官还给这部分“不安分的老人”做了分类。
“半路夫妻”“保姆型夫妻”“爆发型夫妻”。“半路夫妻”多是离婚再婚的,特点就是两人都不是一个人结婚,后边都拖儿带女——成家立业的儿女。这些儿女都捂着老人的房子、票子,唯恐分走。两个老人自结婚就互不信任,稍有拌嘴就觉得对方“算计”自己,一旦吵架,儿女就助力;“保姆型夫妻”一般始于大爷生病,终于财产分割。目的性明确,堪比到市场买菜。有的老人甚至写好遗嘱,照顾到什么程度,相应得到什么报酬,明码标价,童叟无欺;“爆发型夫妻”属于两人为儿女几乎迁就了一辈子,眼看土快埋脖子了,都能看到阎王脸上几个痦子了——不能再忍了,知天命就是有了大明白,余下的生命尾巴要为自己活,要自在、逍遥一次。
常年信访的周酽老两口就属于“爆发型夫妻”,不过是他被妻子“爆发”了。大爷在家里也要当大爷,但大妈却不甘心再当保姆——这是宋小芙的总结。童安市不乏如此夫妻。革命年代过来的,听到爱情都想要捂住耳朵,生活温吞如水——温吞如水还是好的,可怕的是,生活如滚沸的水,两人在一块儿相当于化学作用,相互加温了,一天到晚生气冒泡,几乎灼伤人了。
四
宋小芙这株尚未被栽进婚姻里的植物,还水嫩嫩的,以为脚下土地无限肥沃呢,用周大方的话来说,她只要被栽进去,就知道这块土多贫瘠了——但周大方也只是吓唬她。婚姻是小马过河,总有人水温适中,深浅适度,就像多肉配拇指盆,葡萄藤配地栽。今天来的这对八十岁的老人,看上去就像是花盆跟植物十分不相适宜了——土太贫瘠或者植物过于丰茂?
老大爷刮了头皮,耳畔各留了一撮白发。个子不高,穿老式西服,打领带,领带式样是20世纪80年代的。他一见宋小芙就嘿嘿笑,两个黑眼珠子一滚,又一滚,捏着衣领:“我这是真丝的,当时花了一百多买的!”
宋小芙说:“当时,当什么……时?”
老大爷说:“哼,跟这个娘儿们结婚时!我可真是——”
后半句话没说出口,只飞了一个眼白来替代。宋小芙见怪不怪,知道是类似于“瞎眼了”“造孽啊”“倒了八辈子血霉”之类的童安式表述。她父母也经常以此快意恩仇。那老太太穿着一身运动服,双颊耷拉着,生长着许多老年斑,但声音也没有含冤带屈的,一进门就高亢起来:“我跟你讲,法官,他不把房子过户,我是不会同意的,除非我死了。”八十岁的老太太说这话显得特别逼真,带有诅咒的气势了。法警给了宋小芙一个眼色,宋小芙把他们带去了调解室。两个老人在二十平方米的屋里,以最大的距离抱膀子对站。宋小芙拉来两把椅子,如此狭小的空间,还要相互传话。老大爷的意思一定要离婚,这样的日子过够了。老太太的意思,想离婚先把房子过户。老大爷的意思,过户了房子,老太太肯定又反悔不肯离——关于离婚,她反悔过三回。也就是说,两个人已经是离婚惯犯。
在这段寿长五十五年的婚姻中,老大爷提出过三次离婚。他是当年下乡的知青,宋小芙一听这语重心长的介绍,就猜到两件事:
1 这通调解肯定一上午完不了;
2 按照剧情发展,老太太应该是老大爷在乡下羁绊上的恋人,不得已结了婚。
但宋小芙猜对了开头,没有猜中结尾——老太太竟然是城里等着跟老大爷结婚的世交之女。老大爷心心念念的女人反而是村里的“小芳”。当年他回城后,渴望再见到她,可她选择嫁人,他才娶了等他多年的青梅竹马——也就是眼前这位老太太。宋小芙感慨,您老这故事都能写本书了。老大爷捋了捋领带,老太太哼了一声,别过脸去。看来是听多了,有“消化不良”之感。
第一次闹离婚是二十多年前,他又见着那位“小芳”,对方丧偶,为了人生圆满,他想重建当初。老太太不许,闹到机关大院,搞得他升迁黄了。老大爷的声音低沉迂回:“升迁这种事情,小同志你是知道的,就是看个时机,一步落后,步步落后。我就只剩下当初单位分的房了,除此之外,一无所有。”接着,他伸出干瘪的手,啪一下就挥向老太太的方位,“就是她闹的!你说我跟她有什么过头?”
宋小芙没搭腔,就像周大方给当事人分类型,她在心里也给他们划分了类型,也是三种。
“倾诉型”,以老年女性为主,属于在婚姻里压抑久了,家庭地位低,没有发言权,来了法院,就像倒面袋子,不倒空是不能停的。“爆发型”,以男性为主,一般内向,通常在婚姻里不爱说话,也不想搭理对方,隐忍和冷暴力并行不悖,到这儿来,碍于情面听着对方诉苦、倒豆子,终于忍无可忍,一下就爆出来了,往往就几个字,“你该!”“你编瞎话!”“无动于衷型”,男多女少,表现为不管对方垂泪或愤怒,都一脸麻木,或者干脆眼睛长在手机上——你说吧,我听不见。
今天这对儿倒过来了。老大爷属于“倾诉型”,老太太属于“无动于衷”型,老大爷已经说到第二次离婚了,这次是因为炒股,老太太没有别的嗜好,就是喜欢钱,跟风炒股,赔了,女儿帮着还了大头后,她以为老大爷会把钱给女儿,但是并没有。老大爷在报复呢,老太太控制欲很强——宋小芙在后来翻看卷宗时,看到老大爷提交了一份长达十五页纸的草书起诉状,控诉的是老太太这些年对他的“精神压制”。
大概意思是,老太太在两个人分屋对立之前,要控制他的一切行为,吃饭时间、吃饭饭量、休息时间、散步路线,甚至连购买狗的种类、遛狗的路线也要规划。老大爷也不想听,已经经历了反复抗争。但老太太自有招数。“别看她不受待见,她有的是作妖的方式”——老大爷的起诉状中如此写道。她会一动不动坐在沙发上垂着头:“你知道她没看你,但你也知道,她就是在看你,在等你认罪认罚。”
老大爷说:“你们是叫认罪认罚吗?”他指着宋小芙,“那么多年,我感觉我在她面前,就是个犯人!我就是个犯人!府前街望山苑1单元101是房子,是家吗?他娘的——是座监牢!一座监牢!”
所以他来了,起诉离婚,但是奇怪了。宋小芙说:“大爷,您五年前起诉过一次,怎么就突然撤诉了呢?”
大爷本来高昂的声音忽然就低下去了:“我为什么撤诉,我……”他低下头去,忽然埋头,是哭了。宋小芙莫名其妙,老太太则皱紧了脸,把纹路都挤压出来了。“看来今天不是个好日子,囡们回,囡们回,等你们审判长有空,囡们再来,你个丫头片子,你没吃过苦啊。”她用一种老女人对年轻女人常用的眼神打量着宋小芙。
“唉,你不懂啊,你不懂啊!”大爷说。
五
宋小芙尽管不懂她“不懂”的是什么,但在家事审判庭,她和婚姻这“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怪物,还是打过无数次交道的。她见过女方出轨,男方通过车辆导航一路跟踪蹲守,捉奸在床的;审过丈夫打工,妻子四年生了仨孩子,养大了都不是丈夫的;也看过男人在多个同城交友群“钓鱼”,最后把小姨子钓上来的;还有更离谱的,闹离婚——因为跟丈母娘有了情况。如此种种,已经无法用“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来涵盖了,简直超出了宋小芙的认知。她感到自己的局限了。
大爷大妈走后,她对被看低正生气,门口又进来熟人了,周正阳。身份证交给法警,前后摆动身体,穿过安检。他看着宋小芙,是对法院熟门熟路的样子了。宋小芙脸上先一燥,往后一退:“你又来干什么?”
周正阳说:“送信啊。”
宋小芙说:“请通过证据交换信箱流转。”
周正阳把证件收了:“说是口信,就一句话。”
宋小芙说:“什么话?”说完后悔了,不该接这茬儿。信访人的儿子,你能跟人家有什么牵扯?说不清,太说不清楚了。
周正阳说:“我爸让你去看现场。”
“什么现场?”
“离婚现场,你们不是判离了?他想让你看看他离了之后,这一天是怎么过的。你去现场看看。”
“为什么让我去现场看?案子都判了,后续不是法院管辖范围。”
“你这态度算‘冷横硬推’了哈。你们不是‘能动司法’吗?案子判了,‘前延后伸’不管了?”
宋小芙听出来了,有备而来,这都是法院工作报告的内容。她求助周大方。周大方又在为另一个案子闹心呢,听宋小芙抱怨了两句,忽道:“让你去你就去啊!你不去是态度问题——你去就是啊!”
挂了电话,周大方才回到了眼前问题。他也在纳闷,怎么童安市老年人出问题的这么多呢?一个公婆起诉儿媳妇不当得利的纠纷案。奇怪了,都一家的,怎么不当得利了?细看下去,有意思了。被告小两口是双职工,原告这对公婆平日里带孙子——这爷爷看孙子,越端详越觉蹊跷:不像啊,长得很偏离,有点儿脱轨了。张大爷家都是小眼睛酒糟鼻,孙子长出了双眼皮高鼻梁。这也不属于儿媳妇的基因——儿媳妇也是细眼睛塌鼻子啊!一开始只是盘旋不去的心头阴影,但天天接送,外人看着也奇怪,都说:吆,一看就随了优势基因。说是优势基因,意思就是大爷家基因不好。也许别人没那个意思,但大爷心里疙疙瘩瘩。儿媳妇什么模样,他清楚啊!就这么几年下来,心中的块垒越积越多,快赶上一座小山了,还是火山,直到有一天,火山喷发了——他中风了一次。康复后,觉得不能忍,死前得办大事,就算是为民除害了。在检验结果出来之前,他不敢让儿子知道,儿子天天出差,他为他心寒。他查了一下,知道他跟孙子能做亲子鉴定。
终于,哄着孙子去了医院。结果一出,心中的块垒消解了:“妈的,一点儿也没匹配上,真不是亲生孙子!”鉴定机构的人还劝他想开,他硬是巴掌一挥,气势如虹的样子,“我早就知道!”
这就过来童安法院打官司了,养了十三年了,等于养的不是自己人。十三年的劳动付出和精神投入怎么算?来前请教了律师,说这就是儿媳妇的不当得利。需要返还抚养孩子的支出,还得赔偿老两口精神损失。
这样的案件,在周大方这里,不稀奇。什么没见过?婚姻就是个放大镜和哈哈镜,是人类繁殖行为的附属——早就在经济压力下扭曲变形了,见怪则不怪。但今天他紧张了。他紧张不是因为案情复杂,也不是因为又涉及大爷大妈。
而是因为里头有熟人。
爷爷是原告,被告是儿媳妇,这当然。翻开案卷一看,这被告很面熟,再多看一会儿,又觉得陌生。这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又似乎熟稔了——就他多年的经验来看,是岁月在擦拭记忆。心里有一阵不安跳动,摘了眼镜,目光在名字上流连:焦叶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