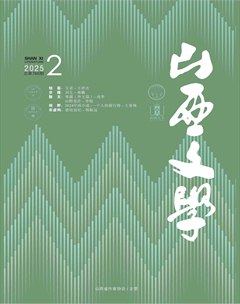行李箱划过地面,发出轰隆隆的声响。李茉给李海平发了一条微信:到站了。周围的人互相推搡,只要落后几秒钟就是极大的损失。乡音此起彼伏,像苍蝇一样扑到身上。家乡话唤醒了她心底某种沉睡已久的气恼,它们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
出站的台阶没有电梯,她只得悻悻拎起箱子,一点点地往下搬。过了地下通道,需要再上一段楼梯,依然没有电梯。她咬牙搬了上去,以为这就到出口了,没想到前头又是一段下降楼梯。终于该上台阶了,楼梯旁明明安装着一部扶梯,却一动不动,还拿挡板遮住了入口,李茉环顾四周,想找个工作人员理论,却发现周围一个穿制服的人也没有。她又回到了熟悉的泥淖里。
一出车站,好几个拉客的师傅围上来,李茉摆摆手:家里有人来接。他们失望地散开。只有一个穿皮夹克的人似乎没听到李茉的话,孜孜不倦地围在她身旁嘤嘤嗡嗡,二十块一位,上车就走,走嘛走嘛,李茉只得快步躲开。皮夹克似乎觉得李茉看不起他,也来了气,站在不远处冷冷地斜眼站着。
李海平还没回微信。李茉又发了一条:在出站口前面,路边放了个黄色路障的地方。
暮色四起,白天的暑热大势已去,出站的人纷纷融入远处的县城中心,仿佛那里是一块喧腾温软的磁铁,把从车站抛撒出来的微尘全部吸附了过去。路边只剩李茉一个了。难道李海平还在家里,跟那个女人吃晚饭?应该不会啊,二十分钟前,他还叮嘱她,到站了说一声。她隔了两年才回来一次,他就不能提前一点来站前等一会儿,非要卡着点。皮夹克时不时扭过头来,幸灾乐祸似的瞟她一眼。
足足等了二十分钟,一辆黑色奥迪终于犹犹豫豫地开过来了。那是李海平的性格,温吞、缓沉,火烧眉毛了,他还是不紧不慢。
李茉坐上副驾,李海平自知迟到,但也不好意思跟她道歉,于是自顾自喃喃道:“我来早了,就进了停车场,昨晚陪人打麻将熬夜了,今天中午又喝了酒,有点困,睡醒看到你的消息,赶紧开出来,没想到出来的时候不小心上了高架桥,绕了好大一圈才转过来。平时我接人,这条路走了好多遍的,今天怎么回事……”说着说着,见李茉不搭话,自己也不说了,两眼直视前方,显出专心开车的样子。
我还以为你陪她在家里吃饭呢。话都涌到了嘴边,李茉又生生把它们一个字一个字地咽了回去。现在的李海平跟以前还是不一样了,她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必须得经营,如同面对商业合作伙伴,小心翼翼地维护他们亲切友好的外交关系。“没事,”她说,甚至颇为通情达理地补充了一句,“我刚出来,也没等多久。”
高铁站在城北,是近几年政府规划的新区,李茉摇下车窗,风涌进来,车里的空气变得活泼了些。比起她上次回来时,目力可及的范围内又多了一片拔地而起的新楼。李海平终于找到了打破沉默的话题,跟个导游似的,兀自介绍了起来:“那边是新修的体育馆和购物中心,听说明年还要修一座文化博物馆。这几年,这边起来好多新房子。”李海平迟疑片刻,晃了晃脑袋,“我有点想把老城的房子卖了,买个新房,搬到新区来。”李茉问:“决定了吗?”李海平说:“还没有最后确定,只是暂时有这个初步的想法。”他当了三十多年的人民教师,说话时会用一些文绉绉的词,让人搞不清楚他是想幽默还是真迂腐。李海平话里当然也是有炫耀的,说话时,嘴角和眉梢都忍不住上扬。
“等一下啊,我看看这路怎么走。”李海平说着踩住刹车——他们开进了一条死胡同,前面已是尽头,高架桥巍然悬在头顶,挡住了天边最后一点暮光,让这条路看起来更加黯淡,后头一个人、一辆车也没有,只有道旁疯长的野草摇摇摆摆,仿佛千万只手此起彼伏地向他们指路,朝这边,朝那边,那边那边。“本来应该上高架桥的,我跟你说着话,怎么就走到这里来了……”李海平一边嘀咕,一边打开双闪倒车,李茉问:“要不要我下车去给你看看路?”李海平说:“没事,倒回刚才那个岔路口就行了。我刚才往右拐,记错了,应该往左拐。”
风拂上李茉的面颊,远处田野的绿意已经变得黯淡,茫然融入了飘飘忽忽的黄昏。
李海平终于倒回了岔路口,正准备往左打方向盘,李茉忽然指着路边一个高耸的指示牌喊道:“等一下——这儿写着是公交车道,看到了吗?还得往回开,再倒一点,再倒一点,倒回前一个岔路口——”
李海平额头上冒出了一排细细的汗珠,李茉脱口而出:“别慌啊,慢慢倒,还好后面路上也没车。”但话一出口她就看见他的脸色张皇起来,他还是跟以前一样,自从那件事后,每当面对窘境,哪怕丝毫尴尬时,挫败感都会加倍在他脸上显现。
终于上了高架桥,李海平长长吐出一口气。两人开始东一句西一句地聊着:身体怎么样——刚刚做了体检,没什么问题;个人问题怎么样了——别催;忙不忙——挣钱哪有不忙的,生意倒是很好;你工作怎么样——还行。像在玩简单的掷球游戏,双方都对游戏规则了然于心,你扔给我,我扔给你,沉默在一旁伺机而动,稍不注意便会溜到他们中间,冷冷地一屁股坐下来。为了避免冷场发生,一方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就要准备好抛出自己的新问题。但话题依然很快就说完了。
李海平开始讲起闲话来。说一个熟人,欠了他五万块钱一直没还,已经逾期两年,他前几天就把这人之前抵押给自己的一辆车转手卖了。她说,他为什么向借你钱?他说,老婆手腕上长了个瘤,要做手术。她说,这人是做什么工作的?他说,在南丰镇上一个厂里当搬运工。说到“南丰镇”时,他的声音停了一下,仿佛那是路上一块多余的石头,硌了他一下。她奇怪,当搬运工也挣不了多少钱,为什么还要买个车呢?他笑了一下,现在的人,就是想享受一下。她说,你把人家好不容易买到手的东西又卖了,人家不会恨你吧?他吐出一口烟圈,我们是签了协议的,我已经等他快一年了,他还是没钱还,我就只能卖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李海平掸了掸烟灰,怅然若失,又有些劫后余生的优越感,“在这个世界上,没钱是寸步难行的。”他转脸看了看窗外,李茉似乎看见他眯起了眼睛,脸上的肌肉有些颤抖。
李海平有一次给李茉打电话,说之前给杜丽补缴社保,借了银行两万块钱,我已经还了一万,剩下这一万我没有义务了,杜丽也没这个能力,那就由你来还。李茉只是嗯了一声,她刚工作一年半,还完大学的助学贷款,卡里只剩两千块钱,找同学借了三千,又找隔壁办公室的老吴借了五千,才把钱给李海平打过去。过了一阵子,李海平又打电话,想再借一万,不是要,是借。李茉说,我没有了,你之前不是说我以后管杜丽就可以了吗?后半句噎了回去。李海平听了默不作声,从此再也没有问李茉要过钱。这件事已经过去七八年了,李茉不知道他话里是不是在影射借钱那件事,也没法追问。现在他们坐在一起,一直在谈钱,好像除了钱以外再也找不到别的话题。
话说完了,李海平只得说:“坐了这么远的车,你累了,先眯会儿吧。”
李茉睡不着,阖上眼睛只是为了不再继续和他聊下去。
很多年前,李海平讨厌谈钱,那时候,他还是南丰镇中学的教师。杜丽在镇上开杂货铺,首先嗅到了风吹草动。她说,你看老罗,停薪留职,两年就买了一辆小汽车;还有老苏,人家当了教导主任,也咬牙在县城里买了套房。李海平依然笑眯眯地晃着脑袋:夫人,别急,该来的自然会来。他每月拿八百块的工资,骑一辆破破烂烂的嘉陵摩托。十一岁那年一天傍晚,她放学回家,一个开汽车的把李茉碰倒后逃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