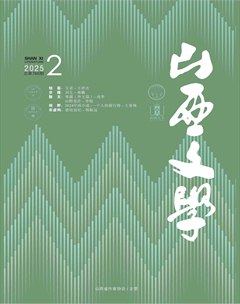作家张石山这样急速地和大家告别,无疑让很多朋友意外。谁都知道,在山西作协这个作家群里,他的健壮结实,是出了名的。大概朋友们都没有想到,钢硬容易脆断,这个应在张石山身上了。
我和张石山是同龄人,都是“老三届”,他比我长一岁,老高三。在创作路上,他比我成名早多了。我调进山西作协时,他已经是名满天下的著名作家,荣获过一次全国短篇小说奖。在山西作协,他和那一批知青作家一浪喷涌而出,可以说继承了“山药蛋派”的强大流风,张石山当时就有“唯此一人”的美誉。在全国文学界,那一批新时期后起的新一代作家群,张石山无疑敢领风骚,风头正健。若论作风,石山之摧枯拉朽,又有那么几分北方草莽英雄的风貌。
1986年,张石山到《山西文学》担任主编。我正在当编辑。1980年代是思想解放的岁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一种新生活正在萌发滋长。花正红,风正劲,张石山的创作和生活都沐浴在新风里,和上一代的日子断开了裂缝。一代新人茁壮成长,文学界作家圈那时可谓得风气之先。张石山除了自己创作要冲破旧的樊篱,要说管理风格,他鼓励作家编辑们走出去,多看看外边的世界。宽松管理,创作至上,这是石山在任时意图带来的新变。
石山兄这种宽松自由、开放身心的做派,显然不那么适合当时门户初开的整体气氛。他的文学主张有些另类,他的解放个性的呼喊,更是让许多人坐立不安。叛逆和服从,管束和放任,在这里不可弥合。由此张石山匆匆地结束了主编履历,成为文学院的专业作家。
兜转了这么一个小圈,石山终于回到了他视为生命的专业创作。一旦写起小说,他的状态有如神助。他对于山西民间社会的谙熟和剖析,对于世事人情的把握,对于人生命运的彻悟,很快让他领先于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他那一批写故乡女儿命运的《含玉儿》《甜苣儿》等,至今读来,也是难得的好小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文学和政治的关系一度成为强势话语。政治和艺术的关系,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张石山应该是最早摆脱开这个惯性,直奔人生主题的先行一流。对于小说应该怎样表达人生,怎样写出下层村庄农人农妇的悲剧宿命,张石山早已超脱了一般的文艺和政治关系的纠结,很早就把目光扫向一辈辈的国人命运。石山这些小说,现在很少有人提及。其实它们的凄凉优美,寒光里的温煦,总让人沉浸。最近我看到石山的小女儿做论文,论小说《甜苣儿》的艺术成就,不禁感慨这父女两代之间的授受真传。游目骋怀,驻足回望,石山兄这些开山之作,在山西文学史自有其地位。叩击一下,依然发出巨大的回响。
张石山写小说,编故事玩得花活。但他绝不是一个浅薄的写者。时在2009年,大约是觉得我们有些气味相投,他送给我一本新著《拷问经典》。全书列举了流行词汇100条,逐一加以解析评判。石山兄不是一个理论家,他解读历史,靠的是感性认知和“皮肉亲历”。他的解读,可谓事理融合,破皮入心。在一系列画面感极强的连缀拼贴中,我们能够依稀看到石山兄对于我们这一代人青春经历的凝视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