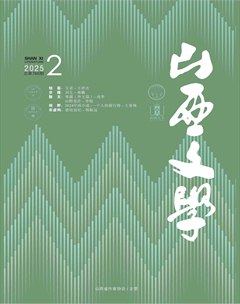甲辰初冬的11月23日下午,惊悉张石山老师逝世,一时不敢相信,赶紧向朋友徐建宏核实。放下电话后,我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
回想结识张石山老师已经有十八个年头,但真正交往却不足两年时间。就是这短短的两年时间,他却给了我莫大的帮助和支持,这足以改变我后半生的人生轨迹。张石山老师是我步入文学殿堂的引路人、恩师,更是我人生道路上的指路明灯、人生导师。
一面之缘
我从小兴趣广泛,尤其喜欢文学和历史,心中早早萌生了写作的想法,但也只是想想而已。由于工作和家庭生活上的压力,很少有闲暇工夫去付诸实施,但梦想还是有的。
2006年暮春,我正在盂县工作。有一天上午去县委开会,在楼道里迎头遇见好朋友、时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李晶明老哥,简单打个招呼便转身要走。李部长突然把我拉住,悄声说:“今天县里来了个大作家,要不要认识认识?”我深知自己在文学上毫无建树,高攀不起如此大人物,便推脱要走。李部长显然看出我的心事,赶紧说道:“是咱盂县老乡,人特别好,见面熟。”我的顾虑顿时被李部长的话打消了一多半,便壮着胆子跟在李部长身后,来到高明远办公室。高明远时任县民政局局长,还兼任县作协主席,著作颇丰,我跟他很熟悉。
在高明远和李晶明两位老哥的引荐下,我认识了张石山老师。原来高明远与张老师既是文友,还是至交。张老师这次回老家,是专门为创作大型历史连续剧《赵氏孤儿》而来的。
张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正如李晶明所说,丝毫没有大作家、名人大腕的架子。张老师年龄在六十岁上下,个子很高,腰杆笔直,人很精神,眼睛里闪着光,骨子里透着文人气质,一开口又很健谈,使我有一种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的感觉。临近中午,我特意邀请张老师和二位老哥去我公司食堂吃饭,还叫来公司在家的领导一起陪张老师。由于机会难得,自己心里还留了个小九九,下午想请张老师给公司干部员工讲一堂课。
十二点不到开始吃饭,酒过三巡,张老师便显露谈锋,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古今中外,天南地北;历史典故,地方古语;戏曲掌故,民歌小调,信手拈来,张口就唱,那种挥洒笑谈的神态,如入无人之境。
张老师的大脑就像个超级储存器,只要不按暂停键就滔滔不绝源源不断地输出;又好像是一个超级计算器,反应速度之快令人称奇叫绝。在座的七八个人只有听的份,根本插不上话,唯一能打断他说话的只有喝酒。
张老师的酒量也很惊人,大家轮番敬酒,而他总是来者不拒,从不摆出高人一等的架势,整场下来足足喝了一斤开外。这让我感觉到什么才是真性情、真汉子,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午饭从中午一直持续到晚上,原本计划下午的讲座,我都没顾上说出口。其实,整个中午到傍晚,张老师一直在给我们上课。
这次的相遇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让我领教到什么是真正的大作家、真文人的风采,所有人都佩服得五体投地。
自那次以后,十几年时间里,我没有再见到张老师,也没有主动给他打过电话,偶尔从朋友那里听到过他的消息。由于长期在基层工作,无暇从事文学创作,所以一直不敢轻易打扰张老师。
再造之恩
2018年初,我调入省城总部工作,并在太原定居。人到中年,工作和生活总算安定下来了,心也静了许多。但在内心深处,总有一种莫名的遗憾,时常思考人生价值和意义这类问题。
繁华过后终归平静,人们终究需要用精神层面的东西来慰藉自己的心灵。读书和写作就是不二法门。读书是跟圣贤对话,写作就是跟自己的灵魂交流。
2020年疫情期间,工作之余,我开始整理多年从事人力资源和教育培训工作的一些课件和随笔,忽然发现有些价值,似乎就是我所思所想苦苦寻觅的答案,于是萌生了写本书的念头,开始创作《人生价值体系》一书。2022年冬出版后,该书受到朋友们的一致好评,为我继续从事文学创作提供了动力,梦想着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