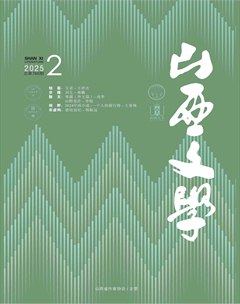在晋南,男人们将麦子倒进粮囤的那一刻起,就将麦子交给了女人,以后,麦子的清香会伴着女人的劳碌,给一家人带来肠胃的满足和家的温馨。
女人接手麦子的第一件事,是将麦子由颗粒变为面粉。磨盘一圈圈转,嘤嘤作响,两扇磨盘间,麦子被研磨成粉,雪花一样飘落,成为女人巧手揉搓的面粉,化身为飘香的面食,就有了璀璨夺目的面食文化。
晨光熹微,我走在离家不远的公园。翠绿的草地之间,一只只浅赭色石磨盘铺成小路,一个接一个的圆,如同一个接一个的印章盖在绿地上,走在上面,坚硬,踏实,每一步踏下去,都好像踩在历史的脊梁上,麦子、磨坊、磨盘和雪白的面粉,甚至飘香的面食渐次出现在眼前。石磨盘小路尽头,连接着一个小广场,广场中央,一具石磨端踞,像个满面忧思的老者,神态之间挂满了沧桑。每每来此,我会敬佩公园设计人的巧思。晋南是个农耕文化悠久的地方,一具石磨,几条磨盘小路,会将游人带往农耕文化深处,思绪里飘出麦子的味道。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石头是一种奇妙的物质,最能保持恒久记忆,坚硬不朽,存在感最强,给人印象较深的是深埋在地下,历千万年重见天日的石器——石核、刮削器、三棱器、石斧、石刀、石镰,这些粗糙笨重的石器,一旦拿到手里,就证明了人何以为人。一旦凿成佛像,佛会从石头里走出来,供人膜拜。凿成兽,就是神兽,比真正的兽还令人敬畏,比如石狮子,威风凛凛的模样,会给人以安全感,守护着国人的精神世界。石磨盘出现较晚,却是最晚被淘汰的石器,人类手里的石刀、石斧、石镰已变为锋利无比的铁刀、铁斧、铁镰,石磨仍被牛、驴拉着,不急不慢地转,流泻出雪花一样的面粉,带来谷物的清香。它是农耕文明的产物,伴着农耕社会从一而终,从诞生那天起,模样似乎从没有改变过,当两块岩石被凿成两个圆盘,咬合在一起转动时,便若一轮旭日,一盈满月,一阴一阳,一下一上转动研磨,娓娓讲述石头与小麦、石头与面粉的故事,
一年深秋,朗日高照,大地苍凉,我与几位年轻编辑来到吕梁山里,山腰间,一个小山村屋舍叠垒,形似高楼,若一幅古意氤氲的中国画悬挂在山坡。走进村子,在一座古朴的明清大院角落里,一具石磨吸引了我,孤零零,没有遮风避雨的磨坊,没有磨面的人,没有拉磨的驴,磨杆已被风吹雨打成灰黑色。只有磨盘的颜色没变,还是砂岩的浅赭色,神情落寞却个性鲜明。几位白发老人坐在不远处的屋檐下,抬头朝这边望。我也朝他们望,与石磨一样,老人也是山村的最后守护者,不同处是一个衰老,一个古老。几位年轻人也看到了古意盎然的石磨,兴致勃勃,你推几圈,他推几圈,嬉闹中,古老的石磨失去实用价值与历史沧桑,沦为玩具。石磨右侧,有一具石碾,圆形的碾盘、碌碡样的碾滚子、灰白色的木碾杆和直立在碾盘中央的铁柱,同样像一个憨态可掬的玩具,却暂时还不能玩。一个女人正围着碾盘忙,仔细清扫后,将红的、绿的、紫的辣椒倒上去,碾盘顿时色彩斑斓了,女人将辣椒均匀平摊,双手握住碾杆,抵在腹部,两腿弓起使足劲推。碾滚转动起来,一圈圈碾压,辣椒变为浆状,白麻石碾盘、碾滚都粘上颜色,辛辣呛人。女人腾出一只手,用小铲子不停翻动。她这是在做辣椒酱,山里人喜欢吃这种辛辣食物,秋天做好一大罐,可吃到明年夏天。早年,我见过母亲用碾盘碾谷子,黄色的谷子经一遍遍碾,脱壳去皮,会变为黄橙橙的小米,碾辣椒酱是第一次见到。更让我感兴趣的,是碾子这种古老的石器,历经千年风雨,至今还能使用。
那几年,我走过许多山村,各个山村也许地貌不同,建筑不同,石磨、石碾始终是一对伉俪,成双成对地出现在某个角落,村内可能已没几个人,房舍可能已坍塌,巷道可能已荒芜,只有石磨、石碾顽强坚守着,它们是最后的石器,农耕时代的标本,乡村生活的标配。农耕社会里,一个村庄也许没有水井,没有庙宇,不能没有石磨、石碾。
在各地乡村行走,我所看到的石磨、石碾造型几乎相同,都那么简单,那么粗糙,一眼即可看清材质、构造,不用想也知道出自石匠之手,用于村妇之间,但它们在中华民族农耕史和饮食史中的地位,却令人心生敬意。它们最初是怎么来的?什么时候出现在农耕社会中,藏着怎样的奥秘?我查不清,想不透,请教过几位学者,也语焉不详。
在中条山深处一个叫下川的小村旁,我驻足四望,山峰连绵,逶迤不绝,不远处是著名的历山,那里奇峰雄峻,草甸青青,还有中华民族先祖虞舜的美丽传说。我更在意的却是一方石碑。身前的草丛中,不大的石碑像从历史深处探出头,上刻着简单的四个字:下川遗址。透过这四个字,我好像穿越时空,来到一万六千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身边林木茂盛,大象、犀牛晃动着庞大的身躯穿行其间,远处山前草地上,羚羊、斑鹿、野驴、野马成群结队,撒欢奔跑。近处,几个袒胸露背的男人高举木棒在围猎一只斑鹿,身旁的茅草棚内,女人们将谷物放在一块鞋底样的石头上,手握一根擀面杖般的石棒,来回滚动碾压,嚓嚓响动,谷物脱去皮糠,变为米粒,然后淘洗,然后制作食物,谷物的香气飘出来,引诱着他们的食欲。我不知道一万六千年前,没有灶具的情况下,粟米饭是怎么做的,是放在石板上炒,还是丢进石窝里煮?也不知道这样做出的饭是什么味道,可以肯定的是,原始先民们还没有盛放食物的器皿,没有油盐酱醋之类的调味,却分明感到香气四溢,可以大快朵颐。
我不明白,发掘下川遗址的考古学者,为什么将这种鞋底样的石头命名为石磨盘,将这种擀面杖一样的石棒命名为石磨棒,在我看来,应该叫石碾盘、石碾棒才更恰当。一万多年前的先祖们还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刚开始从狗尾草之类的植物上获取原生态的谷物,粒食刚成为他们的饮食习惯。他们的肠胃还没有尝过面食的滋味时,仅有石头加滚动的石棒就够了,不需要徐徐转动的磨盘。
以后,在寻寻觅觅中,我终于在博物馆看到了考古学家们所称的石磨盘实物。初见,直呼那分明就是案板加擀面杖,但那确确实实是为谷物去皮脱壳的石磨盘。更让我吃惊的是,这具石磨盘与下川遗址发现的石磨盘竟相隔一万年,从河南新郑裴李岗村发掘。这一万年间,我们的先祖一直在案板样的磨盘上滚动石棒,嚓嚓作响声中,漫长的时光一倏而过,他们有了尊、罍、壶、匜、盂、豆、罐、鼎、杯之类的陶器,有了半穴居的房屋,开始垦耕,收获粮食。男人外出耕种去了,女人将谷物平铺在石磨盘上,操起石磨棒,使足力气来回滚动碾压。她们也许年轻,也许年迈,也许是个少妇,也许是个老妪,但碾压谷物的动作都很娴熟,因为这种工具已经出现一万多年,模样没变,操作方式没变,只是被打磨得更加平整光滑。由于长时间使用,石磨盘中间被磨成凹状,马鞍一般。磨盘与磨棒滚动摩擦着,又几千年过去,石磨盘、石磨棒演变为木案板和木擀杖,被女人们完整地承袭下来。在烟熏火燎中,身陷厨房的女人们用一双巧手熟练地擀动着,无休无止,面团一点点擀薄,一圈圈擀大,面食诞生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案板是石磨盘的变异,擀面杖是石磨棒的异化,可谓最原始的厨具。
我心中的石磨不是案板加擀面杖,应该分阴阳,有上下,徐徐转动,在两扇石磨盘咬合中,麦子破碎为齑粉,从两扇磨缝间落下。这种石磨,现在称之为石转磨,古人称为硙。
我来到中条山之南、黄河之北的山西芮城县,这片缓坡状的狭长地带,曾是古魏国的发祥地,两千多年前,古魏国的先民们曾高唱“硕鼠硕鼠,无食我粟”“硕鼠硕鼠,无食我麦”,魏风飙猛,传递出先民的愤怒,还让后人知道,春秋时期,粟与麦两种不同的农作物,已是他们的主要食物,尽管此麦非彼麦。在当地文博馆,一件东汉随葬绿釉陶磨坊惊艳了我,磨坊中的石转磨,分明与我在各地见过的石转磨一模一样,莫非两千年来,这种粮食加工器具从没有过改变。这件陶釉古磨坊属冥器,汉代有“事死如事生”习俗,就是说,石转磨最迟在东汉已经出现。以后,我又在多地博物馆看到过年代、造型基本相同的东汉随葬绿釉陶磨坊。
石转磨的横空出世,让人不能不想到小麦。在大汉雄风吹拂中,来自两河新月沃土的小麦一出现,就带着不一样的味道,让大汉先民既似曾相识又捉摸不透。华夏农耕史中,麦早已与黍、粟、稷、稻一起出现在“五谷”中,春秋时期,《诗经》中已有“我行其野,芃芃其麦”诗句,可是,面对这种“秋冬种之,经岁乃熟”的外来麦子,我们的祖先却无所适从,连名字都反复更改。汉武帝时称为“宿麦”,再仔细打量,从麦苗到麦粒都与大麦形状相似,只是麦芒略短,麦粒略圆,就叫小麦吧,还叫过麸麦、空空麦。又为怎样食用长时间作难,千万年间形成的粒食习惯,误导着人们,放在杵臼捣也不是,搁在蒸笼蒸也不是,置于铁锅煮也不是,分明能闻到它的清香,做成麦饭,煮成麦粥,却难以下咽。麦子虽好,不会做也不会吃呀!人类的肠胃往往是驱动历史车轮的动力,于是石转磨出现了。将岩石凿成圆形,分阴阳两扇,一上一下,分别凿出人字形沟槽,下面一扇不动,中间竖起一根铁轴,上面一扇带孔,麦子缓缓流进两扇磨盘之间,随着磨盘转动,雪花般落下,一遍遍磨过,一次次筛箩,麦子截然分为两部分——面粉和麸皮,面粉加水和匀,便如同女娲手里的泥巴,魔术师手里的道具,揉、搓、捏、擀、抻,可蒸、可煮、可炸、可烤,魔幻般变出形态各异的面食,飘出令人陶醉的麦香。
简单粗糙的石磨,带来的是一场肠胃革命,《王祯农书》说:“神农尝百草别谷,丞民粒食,”就是说,从炎帝时期开始,华夏先民们开始粒食。按考古发现,华夏先民的粒食习惯更早,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在长达一万多年的时间里,华夏先民的肠胃已被粒食征服。小麦来了,面食来了,从味道到口感都好得令人陶醉,他们渴望更多的面食,如此,又改变了作物种植,麦子开始摇曳生姿,顶着针一般的麦芒,开疆拓土,占据了北方的大部分田野。麦子那鼓胀的颗粒,仿佛饱满的面颊,带着神性的微笑,牵动了北方人的神经,征服了北方人的味蕾。
至今,没人能说得清楚被古人称为硙的石转磨是谁创造发明的。古人有个约定俗成的习惯,若哪种器物说不清发明人,一律归之于鲁班。鲁班又称公输般,这位战国时代的能工巧匠,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是个神一般的存在,他已不是一个人,而是集体智慧的象征。石转磨对于古人来说,是个化腐朽为神奇的神器,“公输般作硙”,先秦史官一句话,就说清了石转磨的发明人。
石转磨虽是石头的,却是铁器时代的产物,那根固定在下部磨盘中央,连接两扇磨盘的铁轴,阳物一般,代表了铁器的坚挺,有它在,磨盘才能缓缓转动,石器才去掉呆板僵硬,脱去原始,灵动起来,带上生动的韵律。
转动的石磨让人类第一次可以借助外力加工粮食,牛被套上了,驴被套上了,马也赳赳然拉起磨盘。它们本来应该在田野中拉犁,在大道上拉车,在疆场上驰骋,突然有一天,被牵进一座简陋的房子,蒙上双眼,在暗无天日的黑暗中,不停地转圈,身旁,石磨嘤嘤作响,飘来麦子的清香,想伸嘴过去吃一口,却被一根木棍抵住了头颅,只能嗅而不见,近而不得,无休无止地围着石磨转,从大汉到大唐,从大宋到大清,日月轮回,改朝换代,它们始终围着石磨转,被吆喝着,鞭挞着,等被掀去眼睛上的障碍物,已过去漫长的两千多年,馒头、面条、饼子和各种花样翻新的面食,占据了北方人的肠胃,连离不开米饭的南方人也跃跃欲试。
我们这一代人是石转磨的最后见证者,也是石转磨的终结者。我出生在晋南一个叫韩家场的小村,1949年前,全村不足百口人,有三盘石转磨。在村人嘴里,石转磨还是古代称呼,叫硙子,磨面叫硙面,磨坊叫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