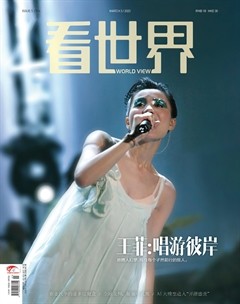几个月后再回头看,莫音根本不能断定自己究竟是否曾走进了一段“关系”。她与对方有过十分亲密的瞬间:每天晚上打电话;一起看了很多电影;吃了几十顿饭;一起旅游、爬山和游泳。他会在她受委屈的时候牵紧她。可当莫音询问对方两人是什么关系,他总是回答她:只是朋友。
“我们明明比朋友亲密太多”,莫音开始反思两人之间的相处。实际上,她们真正联络的时间,大多只存在于夜晚11点过后。有时会聊天到凌晨三点,有时候甚至到第二天早上。那阵子,莫音格外沉迷于这些“独属于彼此的时间”。
这种沉迷于与对方“相恋”的短暂时空,在今天有一个专有名词,叫“situationship”。两个人可以牵手、拥抱和亲吻,却从不互相确认关系。
去年上映的电影《好东西》里的男性角色“胡医生”,就是擅长建构这种“situationship”的模范角色。
“Situationship”像是一种类似曾经流行的“海王/海后”“渣男/渣女”的说法。从词义上,把它理解为一种“情境性关系”是合适的。关系参与的双方,并不必然抱持着绝对的功利性目的,而是与恋爱一样,也有着对情感和心灵的依赖。
只不过,所有极似爱情的瞬间,都只能发生在固定的情景和时空内。恋爱关系里的承诺、陪伴,都不是构成这段关系的必要元素,它们甚至可能是禁区。
在2023年将“situationship”收录进年度热词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对该词的解释,是“非正式浪漫关系”。双方互不干涉、互不制约,也不存在与彼此相关的长远打算。关系可能不明不白地开始,也随时可能不明不白地结束,而游戏唯一的规则,就是彼此都要深谙并接受这一点。
在今天,我们不断反思而非追求爱情的真谛,试图拨开浪漫主义的迷雾。对自我的追逐,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和防备,都在重塑亲密关系的形态。
而当我们选择进入“情景(situation)”,爱情究竟是发生了,还是流失了?
龙卷风恋人
去年,在东京工作的杨雨在约会软件上认识了同样来东京找工作的欧洲人A。两人交往了一个月的时间,A的温柔、细腻和黏人,带给了杨雨“前所未有”的恋爱感,慢慢习惯他的存在后,杨雨觉得,自己和这个人“深度绑定”了。
不过,从开始到结束,虽然与A做了很多情侣会做的事,但两人始终没有互相承诺过是“男女朋友”。出于某种忐忑和回避,杨雨没有直接问A他们是什么关系。A同样不会直面这个问题,但他答应杨雨,“这段时间只和我一个人交往”,也就是“1v1”。
他告诉她,她是他的“lover”。
杨雨心里“咯噔”一下,“‘lover’在中文语境里更多是‘情人’的意思,而不是恋人或爱人”。

“除了我之外,他可能还有其他暧昧对象,但我从来没有资格去质问他。他把我当成倾诉对象,但当我真的遇到困难,我却没有立场去找他。”
杨雨当然期待A能找到工作留下来,但她也知道,亲密关系在对方的价值排序里很靠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