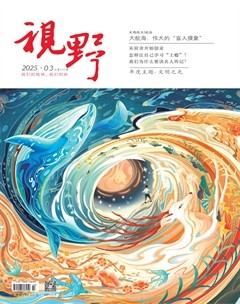在威尼斯,大运河的东头就是望不到边的亚得里亚海。
1271年,马可·波罗从这里出发,穿过陆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24年后,才从海上回到家乡。在热那亚监狱,由他口述、狱友记录成书的便是《马可·波罗行纪》(以下简称《行纪》)。如果把他讲述的地名串起来,就会发现两条重要的驿路,和今天倡导的“一带一路”几乎一模一样。
不过,马可·波罗真的来过中国吗?这个问题,争论了几个世纪,就连他的绰号“马可百万”也一度成了骗子、小丑的代名词。正是这些质疑,让专家们各显其能,从不同角度不断丰富着马可·波罗的故事,至今仍有新的发现。
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
202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中历史教材这样描述马可·波罗,说他“在元朝生活了17年……反映了中国的富庶和先进。马可·波罗游记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世界的极大向往”。这也反映了国人对他的第一印象:一个对于东方无限向往、不吝夸赞甚至有些过誉的西方旅行家。在近年流行的一些网络视频里,他还被扭曲、颠覆为一个文盲、妄人、吹牛大王,“韦小宝”式的人物。
即便在自己的家乡,马可·波罗也常被质疑和讽刺。1324年,70岁的马可·波罗临终时,他的朋友们要求他删除书中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谎言”,并称唯有如此,灵魂才能前往天堂。尽管如此,他的回答仍是:“我所说的,还未及我亲眼所见的一半。”16世纪后,西方传教士大批东来,看到封建专制下日益衰败的明清,远不如《行纪》中描述的富饶,越发不相信此书。
1871年,英国学者亨利·玉尔在其翻译的《行纪》导言里说,马可·波罗遗漏了长城、茶叶、缠足、鸬鹚捕鱼、印刷术、汉字等中国的标志性事物,这是不正常的。
从此,这一悬案将诸多鼎鼎有名的学者卷入其中。最令他们不安的是,在素有“汗牛充栋”之誉的中国史籍内,居然未能寻见马可·波罗的名字和事迹,也就是没“铁证”。一筹莫展时,一个研究生却意外地发现了“孤证”。1941年夏,杨志玖在西南联大攻读研究生,无意间从《永乐大典》的残片中,找到了至今仍是独一份的典籍证据。
那是一份关于元朝驿站的公文,记载了坐船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伊利汗国的三位波斯使臣的名字——兀鲁䚟、阿必失呵、火者;《行纪》曾记载此事,说马可·波罗一家搭乘那条船顺道回国,并将三位使臣的名字写作Oulatai、Apuscah、Coja。马可·波罗还说三位使者最后只有火者(Coja)活着,另两位死于海难;波斯语写的《史集》中,的确只提到火者一人的名字。信息对上了,基本算是“铁证”。
不过,这份公文并未提及马可·波罗的名字。对此,杨志玖的解释是:“此文既系公文,自当仅列负责人的名字,其余从略。由此可想到,他在中国的官职,大概不太高贵,亦不为其同时人所重视。”时逢“二战”,许多西方学者没能及时看到杨志玖的论文。
但令人欣慰的是,大汉学家伯希和用西方史料,印证和支持了杨志玖的结论。20世纪60年代,又有德国的蒙古学家傅海波提出质疑:马可·波罗自称在扬州做过官,并吹嘘自己提供了投石机技术协助蒙古大军攻陷襄阳,前者没有史料可以佐证,后者已被证明是不实之词(《元史》记载,献回回炮的是波斯人亦思马因与阿老瓦丁)。据此,可怀疑“马可·波罗一家长期住在中国”不属实。
已经成为元史学家的杨志玖,为了解释和回击,学了多种语言,写了数篇文章,列出种种证据。然而,风波一浪高过一浪,1997年,大英图书馆东方部主任吴芳思出版《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一书,以畅销书形式,把质疑论升级成了否定论。吴芳思的论据有三:一是中文文献中找不到直接证据;二是书中漏写了许多被视为中国特征的事物,如长城、缠足、汉字、印刷术与茶叶;三是记载失误,如助攻襄阳等。由此,“马可·波罗可能从来没有到过,此书不过是道听途说”。
吴芳思这么笃定,是因为她到过中国。1971年,她第一次来中国。所属的代表团没有去参观名胜古迹,而是参观红旗渠,去公社采访赤脚医生。1975年,她又来北京大学学习一年。和中国学生一样,她每天早上要做广播体操,白天去四季青公社劳动,夜里还要在北京大学挖防空洞。这样的中国,在吴芳思眼中,有一层挥之不去的浪漫。进入大英图书馆后,她开始进行通俗历史写作。
“她的立场源于对古代中国的想象。”北京大学的党宝海教授认为,吴芳思某些证据源于“中国印象”。比如长城,元朝之前,中国确实多次建造过长城。但是,当马可·波罗来到中国时,长城的绝大部分都已成为荒芜的遗址。将长城看成中国的象征,是明长城修筑之后的事。
关于缠足,学者黄时鉴收集了出土的元代女鞋资料,考据认为:元代女子缠足的主流是“窄足”,也就是将脚的前掌与足趾缠窄,而非后世广为人知的“三寸金莲”。直到明代后期,“三寸金莲”才引起来华传教士的注意。
茶叶与汉字在游记中的缺失,也大体可以做相似的解释——马可·波罗来中国时,茶叶还没有在蒙古人当中真正流行开来;马可·波罗一家主要依靠波斯语在华经商,不懂汉语,所以他对汉人的饮茶习俗和汉字缺乏关注。
别看吴芳思的论证在“圈内人”眼里是外行话,但公众却更愿意相信“抄袭者”“大骗局”这类说法。为澄清是非,杨志玖在1999年专门撰写了《马可·波罗在中国》一书,展开新一轮论辩。
“若说是抄自波斯文指南,试问,哪有如此内容丰富的指南书可抄?”对此,吴芳思无言以对。2000年夏,杨志玖在南开大学发起“马可·波罗与13世纪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特邀吴芳思来商榷。然而,剑拔弩张的交锋场面并没有出现,吴芳思说,自己并非否定马可·波罗来华,只是提出一些疑问。
这一轮世界范围内的交流,使真相越辩越明。怀疑论者“迫使”中外学者又举出了大量证据,罗沙比在《剑桥中国史》中评述:“诸如此类的怀疑都已被杨志玖永久地否定了。他最终证实马可·波罗在忽必烈统治时期曾经到过中国。”
“马可百万”是吹牛大王吗?
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已成定论,但《行纪》的可信度仍存疑。毕竟,失实内容有着人为加工或夸大的痕迹。
在2000年这次会议上,吴芳思提交了论文《马可·波罗的读者:抄本复杂性的问题》,这又给学者们出了个难题——《行纪》是如何在流转中被添油加醋的?
《行纪》成书于印刷术流行之前,原始版本早已失传,流传中产生的抄本、翻译本、印刷本近150本,内容也不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