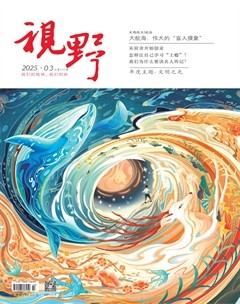中国的村庄里,有没有文学存在呢?有。当然有。不仅有,而且它的文学无与伦比、经典伟大,艺术价值之高,堪为空前绝后。
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的作品放到那个村都显得轻微、渺小,不值一提;世界上多么现代、前沿、探索的作品,放到那个村,都显得陈腐、旧败、传统和落伍;而世界上古老、经典如《荷马史诗》、《一千零一夜》、《神曲》、《唐吉诃德》、莎士比亚戏剧等伟大的传统精华,放在这个村庄,却不仅不显得传统和落后,反而会显得现代和超前。
比如说,现代之父卡夫卡让二十世纪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感叹和敬重。可在那个村庄里,上千年前就传说人生转世、脱胎换骨,如果你应该变为猪、变为狗,但因为走错了门,结果成了人;有一天你正睡着时,神还会把你从人变为猪,变为马。这比格里高尔一夜醒来变为甲虫早了一千年。
我小的时候就知道,那个村庄里有个村人有一双“猫鹰眼”,白天什么都看不清,可晚上什么都能看得到,天色愈黑,他看得愈远。所以谁家的秘密,男人女人的龌龊事,村里的贼又偷村里谁家什么东西了,他心里一清二楚,那双眼宛若村里黑暗秘密的探照灯,这神奇、这魔幻,比马尔克斯的神奇、魔幻不知真实了多少倍。
但丁的地狱、炼狱够传统经典吧,可我们村庄流传的地狱篇、炼狱篇比但丁的还早两千年,比《神曲》中描绘的情节、细节更为惊心动魄,有教化意义。
《唐吉诃德》中的风车大战,形象生动,是西班牙最为形象的精神象征。可在我们那个村庄的传说中(早就有)推磨人与磨盘的战斗——他要用他的力气、韧性和毅力,推着石磨不停地走,不歇地转,直到把石磨的牙子磨平,把石磨的石头磨得消失,让石磨和又粗又大的磨棍一起说话,唤着认输才肯停下推磨走动的脚。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有一个神父布道的情节,在那个情节中,耶稣本人就假扮成最普通的教民在那儿听神父布道,看信徒忏悔。我读到这儿有一种颤栗感。可后来,我看见我们村的人,他们最微不足道的宗教行为,都比这伟大的文学情节更为动人和震撼——
我们村有个七十几岁的老奶奶,她不识字,从未去过教堂,也从未去过什么神庙烧香或磕头。她一生未婚无子,一生默默无闻,种地、拔草、养鸡、种菜、扫院子、打秋果。她活着就如在世界上不曾存在一样,她一生最惊天动地的事,人们也不曾记住过。可是,无论是在中国绝对“无神论”时期的“文化大革命”时,还是开始物欲横流的改革开放时,她每天一早一晚,只要起床、出门,都要站在她家上房屋的窗台前——那窗台上永远摆着用两根筷子绑起来的十字架,她就在那筷子绑的十字架前默默地祈祷和“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