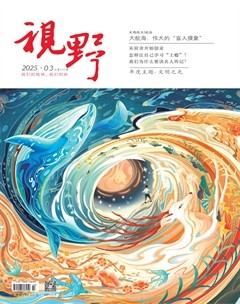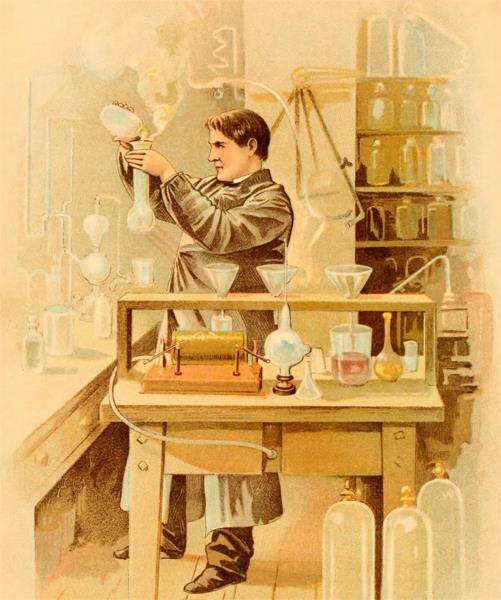
一
春天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百草穿孝。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刀,斩尽世上的男女老少!
以上是单田芳先生常用的一首定场诗。我最早听到他的声音,是1980年电台里播的《隋唐演义》。夏天,正午十二点,阳光耀眼,家家户户都在吃午饭,各家的收音机都在播放单田芳的评书。他讲秦琼卖马,讲程咬金贩卖私盐。他在评书里大量使用象声词,大刀一挥,咔喳喳人头落地。那是我第一次领略到讲故事的魅力。他的嗓音沙哑,听着像是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实际上那时候他正值壮年。单田芳出生于1934年,乳名叫大全子,学名叫单传忠,后来说书的艺名叫单田芳。1979年,他在鞍山电台录制《隋唐演义》,时年45岁。
2004年,我有一个机会去采访单田芳。他当时住在廊坊,在电话里约定采访时间,他说:“你从京津塘高速公路下来,到了廊坊,一打听东方大学城,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那次采访,我印象最深的地方有两处,一是单田芳开头就讲,说他一生经历了四个“朝代”:伪满洲国、苏联红军占领时期、国民党占领时期和新中国。老先生以货币发行来看“朝代”更迭,苏联红军占领东北,在我们看,只是很短暂的一个时期,可他们在那里发行了自己的货币,所以单田芳也把那个时段当成是一个“朝代”。第二个印象深刻的地方,是单田芳对现代题材的兴趣,当时他正在准备说《二战风云》,分为太平洋战场、欧洲战场、中国战场三部分,他打算去欧洲的战场看看。
那次采访过后,我听到他讲的《言归正传》,这是他的一本自传,后来我买到了文字版。2014年,我想再去采访单先生,和经纪人联系,沟通了几次,单先生没有再接受我的采访。我听他讲过几十本书,有袍带书,讲改朝换代的故事,有短打书,讲行侠仗义的故事。他讲《白眉大侠》,讲曾国藩、张作霖,讲这块土地上的风云变幻,讲英雄豪杰如何践行自己的正义法则。
等我对传奇故事的兴趣消退之后,他这本自传依旧有魅力。他从五岁开始写起,母亲王香桂是鼓书艺人,父亲单永魁弹三弦伴奏,一家人在东北各地辗转,只要父母能在茶社演出,一家人就有饭吃。1945年8月,日本人投降,长春市民说,国军要回来了。东北被占领了14年,终于,日本鬼子投降了,东北光复了。老百姓们都盼着过太平日子,可没想到,接下来的是一个多月的无政府状态,伪皇宫门口变成了一个自由市场,全是卖洋破烂儿的,伪皇宫里面也成了垃圾场,地毯被抢走了,所有的玻璃都被打碎了。正殿里有一个水泥高台,那是溥仪接见文武大臣的地方,孩子们一个个站在高台上,大喊“我是皇帝,我是皇帝”。到1945年10月,甲长来通知,去火车站迎接国军。单田芳连夜画了两面青天白日旗,糊在两根小木棍上,早上跟着父亲去火车站。长春火车站外面有成千上万的人列队欢迎,可他们等到晚上也没看到国军的影子。第二天,再去火车站迎接,到了中午,一队队大兵扛着红旗,迈着整齐的步伐从火车站出来,欢迎队伍惊呆了,来的不是国军,是金发碧眼的苏联红军。一辆辆的坦克轰隆隆驶过,士兵胸前配备着轮盘枪,穿着半截的马靴,戴着船形帽。
1946年,东北光复之后的第一个春节,长春老百姓在比较平安的状态下度过。到这年4月,国军来了,进驻长春的是国民党新六军、新一军、新七军,清一色的美式装备。单家在长春的五马路上开了一间北海茶社。一年后,长春局势发生变化,四周枪炮声不绝,东北野战军来了。1948年春节,长春停水停电,东北野战军占领了吉林市,控制了丰满水电站。长春断水断电,粮价飞涨,铁路也断了。这就是长春围城的开始。单田芳讲述他们一家怎么从长春逃出来,在城外的兴隆山,爸爸单永魁向解放军交代——“我不是当兵的,我是个弹三弦的说书艺人。”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单永魁说了一段《薛刚反唐》。
二
人们为什么需要故事呢?故事是有完整的逻辑链条的,我们需要故事,是需要体会到一种意义上的完整性。本雅明有一篇文章叫《讲故事的人》,他说口口相传的经验是讲故事的人的灵感来源,在劳动的氛围中讲故事,这就是一种交流方式,讲故事是一种手艺活儿,每个讲故事的人都会在故事中留下自己的痕迹,就像做陶的人会在陶器上留下自己的印记一样。人们在放松的状态下听故事,内心又想记下这些故事,有对他人转述故事的愿望,这就构成了听故事的人与讲故事的人之间那种纯真的关系。讲故事的人就像智者一样,能讲出自己的人生经验,也能讲出历史的经验、他人的经验、人类的经验,他能让故事的火把生活的灯芯点燃。本雅明肯定没有听过评书,但他的这些话就像是在分析评书一样。
传记是什么?传记就是关于一个人的故事,特别是关于一个人的意志的故事。在学校里,老师会告诉我们,经验是无可替代的,如果你没有第一手经验,那就从别人的经验中学习。老师会推荐我们看大量的名人传记,看他们如何处理危机,如何解决复杂问题。传记邀请我们进入他人的生活,让我们观察他们如何应对世界的变化并做出重要决定,我们阅读传记的那几天就像陪着传主走一段人生路,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会得到一些警告,知道该避开哪些陷阱。老师希望我们从非凡人物的传记中获得灵感和动力,但随着阅历的增加,我们也会在传记中看到那些人怎么处理失败和挫折,看到他们的弹性和适应性,也看到他们的局限,对每一种别样的人生都有同理心,对每一种人生选择都能宽容地看待。我们还能了解传主所处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看他的视野怎样一点点打开,看他如何成长,看他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看哪些东西在推动他。传记还会激励我们做自我反省,我们沉浸在他人的故事里,也反思自己的信仰、能力、价值观和生活选择,我们会看到人生中的动摇、黑暗和狂喜,似乎命运并不只为书中人物所设置,也为我们体会天道的秩序和无常所设置。
1956年大年初一,单田芳在鞍山的前进茶社第一次登台演出,说《明英烈》。这一天演出顺利,挣回来四块两毛钱,什么概念呢?当时大米一毛八一斤,猪肉四毛五一斤,鸡蛋三分钱一个,一天挣四块多钱,将近十斤猪肉。1958年,曲艺团走向文化单位编制,在评定工资的时候,单田芳被评为第五级,每月工资84元。然而,单田芳的信条是“好汉不挣有数的钱”,1962年,他带着妻子走穴,在营口的田庄台,从腊月到正月,除去花销,存下4600块钱。从田庄台到苏家屯,再到盖县,他形容这段单干的经历用了四个字叫“火穴大赚”。江湖艺人最终还是要服从文化管理,单田芳回到了鞍山曲艺团。他经历了“文革”。十几年后,他再次登台,依旧相信“好汉不挣有数的钱”,他相信从爸爸妈妈身上看到的真理,“鼓槌一响,黄金万两”,他相信故事的魅力,他要单干,要走穴,要做一个新时代的江湖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