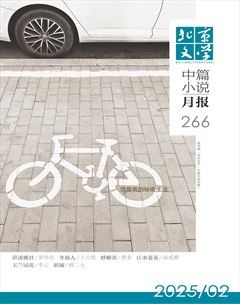北宋元丰二年八月,苏轼从湖州任上被押解到御史台受审。在那个被人们称为“乌台”的地方,一代文豪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劫难?事件的局内人和局外人,从皇帝到狱卒,以及苏轼自己,生前身后又各有一番怎样的自白?或许只有那只无处不在的乌鸦,能印证世人的良心。
题 记
要是世人能辨假,真人何须诉明神。
——百尾生《三梦记》
引 子
关于乌台诗案的案卷,很多人认为它已消失于靖康年间的大火中,但随后浮现出来的案卷证明这种说法并不可靠。据说是御史台一位不知名的台吏从开封逃出时,带上了“真案”,也就是乌台诗案的案卷,一路逃到了扬州。随同案卷一起被发现的,还有一个未完成的话本。这份案卷辗转多人之手,流传至今,而那个话本却不知所终,其作者更是无从稽考。
第一章 起话
在台收禁,听候敕命断遣。
——《诗案·勾摄》
台 吏
史书中,我要么没有存在过,要么只是“一个不知名的台吏”,就像一张沙子塑出的面孔,风一吹,破碎,消失。我也有自己的名字,就像一棵树,一块石头,或者一只鸟,来过这世上。
神咒浪出,不过刹那,我已经活得太久。我只是害怕如果要在死后再来讲这个故事,会完全不一样。
元丰二年八月十八日的那个黄昏,他从湖州任上被押解到御史台。那时他叫苏轼,还不是后来的苏东坡。人们称那里为乌台,是因为森森的柏树之中,有众多的乌鸦,那天它们好像已经消失不见,只有蝉在嘶嘶直叫。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那只是再平常不过的聒噪而已。
那些年,我们几乎忘了寒冷是怎么回事,却没想到转眼就冷得够呛,北方的金国越过结冰的黄河直逼东京城。而我,和很多人一样,像被开水浇了窝的蚂蚁,四处逃命。那时,我随身的包袱里除了乌台诗案的卷宗,还有一个没有写完的话本。
靖康二年,金瓯覆,汴京破。我沿着汴河一路往东水门逃,四处都是火光和浓烟。街道上,那些酒楼、分茶店、脚店、药店、炊饼店,仿佛是长卷中的黑色碎片,带着死亡的腥味和焦煳味,乌鸦一般飞散。御街上的樊楼也着了火,曾经多少个夜晚,彩楼欢门,灯烛相照。而现在,那件写着“天之美禄”的酒旆正尖叫着消失。汴河里漕船的桅杆带着火焰咔咔直响,那些船就像一只只鞋子,缓慢地往下沉。汴河中,一片片灰黑色的尸体一起一伏,仿佛死者仍在奋力泅渡。
奔跑中,我被绊倒,定睛一看,只见一具尸首身着戏服,打扮成秦叔宝的模样。旁边,是一把断裂的朴刀。他浑身涂满血污,脸上那道狭长的伤口仿佛多了一张嘴巴。他的眼睛却睁着,黑豆一般,呆滞而茫然。在他身边,还有几个穿着戏装的人,有的扮成尉迟恭,有的扮成程咬金,还有个女的,扮成了花木兰的样子,都倒在地上。我一开始还以为他们是“六甲神兵”,扫了一眼,才想起他们都是瓦子里唱戏的。
正当我发愣的时候,那个穿花木兰戏装的女人突然站起来,摇摇晃晃地往前走,一只带着火焰的飞箭嗖的一下从空中穿过,正中她的后背。我吓了一跳,包袱散落在地,装着案卷的黑色匣子破开,那个薄薄的话本更是脱了线,几张纸犹如蝴蝶一样向火光飘去。就在这时,一块石头从天上飞过来,砸在我伸出来的手上。
黄昏时,下起了雨。此刻,我在一个离东京城千里之遥的河边小镇想起这些事。陪着我的,只有一条老黄狗,还瞎了一只眼。这些天,我带着它在河堤上走来走去,看着那些烟雾里的松树、无患子树和苦楝子树,听着它的叫声在夜雾中消散,不知道这一天到底是哪一天。
我以前是一个浪子,什么双陆象棋、拆牌道字、六博蹴鞠,都是我的拿手好戏。也因为这个,我才认识了我的娘子。她是“眉寿”酒的“库妓”。别想歪了,虽然挂了个“妓”字,其实只不过为美酒当招牌,卖艺不卖身。即使她曾做过这类营生,我也不会嫌弃,像她这样有情有义的女子,世间哪有多少。我记得初识她的那一天,正是仲春时节,她骑着一匹花斑马,沿着御街从朱雀门往南薰门去,她的嘴角微微翘起,像汴河潋滟的波光。我一下被迷住,一颗心荡悠悠地没了个去处。
我的娘子早已经离我而去,还有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孩子。要承认这一点很难。令我恐惧的是,这些天,她的那张脸好像已经消失,甚至和以前我在栀子灯下见到的女人没有任何差别。在那个年头,要在东京城找一个销魂的所在,只需去找挂着四盏栀子灯的地方,在那上面,无论晴雨,都会放着一顶斗笠。我记得这些,却想不起娘子的面孔。我不停地咒骂自己,但是这并没有挽回我那日益破碎的记忆。她那张脸像是隐藏在河流之下,手一抓,什么也不会捞起。很多时候,我几乎认为她甚至没有存在过,就像话本中的一个角色,只是出于我的虚构。而那个话本,正是我和娘子一起写的。
也正是出于这种羞愧和恐慌,我得尽快把这个故事讲出来。
乌 鸦
如果你们是我,那么也将看到所发生的一切。
那时东京城的一天是这样的:五更相交时,寺院的行者开始敲铁牌子、打木鱼,铁牌当当,木鱼笃笃。随着东京城的各处城门、吊桥和街市依次开放,这个城市好像从一个梦里醒来,又准备进入另外一个梦。
从州桥往南,出东雀门,一直到龙津桥,沿街有很多商铺,商品一年四季花样不断。夏月,有砂糖冰雪冷元子、生淹水木瓜、荔枝膏、梅子姜等等,有的放在乌黑的托盘里,有的盛贮在梅红的匣子中。冬月,有旋炙猪皮肉、野鸭肉、煎夹子、滴酥水晶鲤鱼、王楼前獾儿、脯鸡、现卖的羊白肠、批切的羊头。街坊里的那些妇人,绾着高高的发髻,腰系青花布手巾,笑着打趣,换汤,斟酒,献果子,弄香药。
沿街的饭庄铺子,卖着粥、饭、点心。吃不了的那些大骨头,就用荷叶裹着。街巷里有不少这样的人,打着饱嗝,托着荷叶包,摇摇晃晃地往前走。孩子们拿着梅花包子、蜜饯之类,推搡着,一会儿钻进某个巷子,一会儿又从州桥那边冒出。
瓦肆那边,全是唱曲的、说书的、耍宝的。唱曲的唱得好的人不少,尤其是那个孙三四,重起轻杀,浅斟低唱,唱到得意之处,眉毛总是一挑。说书的人更多,什么烟粉、灵怪、传奇、公案,真是说收拾寻常有百万套,谈话头动辄数千回。南薰门一带,每天有上万头猪进城,却只有十几个人驱赶,人嘶猪叫,和街市上的吆喝声混在一起。那些吆喝声有的高得像铁弦子,刺溜一声,飞得老高;有的拖着尾音,尖叫着,久久不肯消失。很多人不喜欢这个场景,说是乱糟糟的,对于我,却经常一看就是半天。这种古怪的乐趣从何而来,我也说不清楚。
大相国寺开集之日,那叫一个热闹,金山金粉地涌过来。你们不知道在那时,我是多么喜欢对着那些物什,一个个地念出它们的名字:绣作、珠翠、花朵、头面、领抹、冠子、幞头、丝绦、香药、土物、书籍、玩好、时果、腊脯、鞍辔、弓箭……我的舌尖混合着唾液,像一遍遍地品尝着这些注定要消失的秘密。
此刻,红日正恹恹地往下落。当日头越来越接近青晦色山峦的时候,它突地一坠,就像趔趄了一下,掉进了浅灰色的天空。当夜色弥漫,最后的一丝光亮仿佛长蛇分叉的舌头,在黑色的青石板上悄然一舔,倏忽不见。
正是此时,我看见皇甫遵押着那个人进了东澄街御史台的大门。和别的衙门不同,御史台的门是朝北开的,取的是阴杀之意。模糊的夜色中,那个被押的人穿着官服,像鸡鸭一样被绑着,脸上闪烁着疲惫、沮丧和惊恐的表情。他就是苏轼。前些天,在湖州的衙门,中使黄甫遵带着两个兵士将他当场逮捕,二十一天后,他们回到了御史台。在蝉声的嘶鸣中,我听见黄甫遵对着那些人说:我当时站在湖州的公堂上,什么也没说,他都吓得快尿了,不敢出来见我。
黄甫遵身边的一个兵士,长着一副马脸,也觍着脸,带着笑恭维:是啊,大人那时可威风了,苏轼磨蹭了好一会儿,才穿好官服官靴出来。黄甫遵双臂抱在胸前,他的脸上有一道红色的胎记,远远一看,仿佛在流血。
皇甫遵说:直娘贼,那家伙一路上还想着自杀,幸亏我们早有安排,没让他得逞。旁边的兵士也说:那日官船行到太湖,苏轼一下子跳将起来,他们一拥而上,像按一只扑腾的鸡,把他按到甲板上。他们边说边比画,不时哈哈大笑。御史台的人一会儿说大热天办这趟差不容易,一会儿又说,这趟差办下来,日后少不了奖赏。
人群中,我看见一个身着青衣的男子恍恍惚惚,好像在想着什么心事。从他的衣服来看,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台吏罢了。在这个地方,我能叫出很多人的名字,在这个故事中,他们将轮番上场。而这个台吏的名字,就连我这只乌鸦,也不想知道。
这时,我看见苏轼回过头来,结果遭到了一顿呵斥。那个马脸的兵士还扬腿踢了他一脚。刚才那个年轻台吏转过脸来,他的脸被柏树枝丫的影子交错覆盖着,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天已经黑了,黄甫遵带人把苏轼押进了大牢。起风了,我嘎嘎叫了两声。就在这时,一块石头朝我扔来,差点砸中我,我慌忙飞走。
没有一只乌鸦不怕石头。
御史中丞
每一个故事都有一个反派,但是,一个故事不到结尾,谁也不知道谁是怎样的一个人。
去台狱前,我听了黄甫遵的复命报告。没想到名震天下的苏轼遇到事情的第一反应居然是躲。这一路上,苏轼还两次试图自杀,幸亏黄甫遵他们机警,没让他得逞。这次命黄甫遵去湖州捉拿苏轼,还是应该多派些人,一是捉拿苏轼,二是到他家里抄出那些通信和手稿。等我派的第二批人赶到,苏轼家里的人已经烧了不少诗稿、书信和文件。不过,他越是这样,越证明他心中有鬼。
七月初,先是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上奏,说是苏轼到任湖州的谢恩表语涉诽谤朝廷,什么“难以追陪新进”,语多讥讽。何正臣之后,舒亶上奏,在弹劾的奏章中还附有苏轼的诗集,至于借燕子和蝙蝠的争论说事,更是居心不良。我也趁热打铁,上了弹劾状,列举了苏轼的四大罪状。加上国子监博士李宜之的札子,官家很快就下了令,免去苏轼湖州太守一职,捉拿到御史台归案,命我和知谏院的张璪主审。
我叫黄甫遵前去歇息,只带了个台吏随我去台狱。其实,我并不需要去,也许只是黄甫遵的那些话让我有些好奇。月亮是红色的,还带有黑点,挂在天上,像一块烧焦的石头。只要稍微走动几步,就是汗流浃背。我正了正领子,继续大步往前走,跟在后面的台吏说:中丞大人,这都多少天没有下雨了。我瞪了他一眼。
台狱在另外一个院子,顺着旋转的台阶,我下到栅栏边,看见了一个影子。那个影子侧对着我,仰着头,好像在看月亮,有一刻,他举起手,好像要去抓流水般的月光。光线从他的额头上倾泻下来,经过他的鼻子,又流过他似笑非笑的紧闭的嘴唇。我特别讨厌他那种笑容,看起来是在嘲笑自己,又像是在嘲笑别人。他突然转过身来,朝我们这边看过来。我身后的台吏打了个寒噤。我甩了一下衣袖,说:走。台吏跟在我后面往外走,还差点绊倒。没用的东西,我说。
我打发台吏回家,自己留在签书房。这几年,官家交办给御史台的案子一个接一个,像什么祖无择案、李逢谋反案、郑侠案、相州案、太学案等等。每一个案子都牵连甚广,案件中的那些人,轻的罚铜,重的去职,甚至发配到沙门岛,有的还被处以极刑。而当下御史台正在办的案件,除了苏轼这个诗案,还有另外一个大案,那就是陈世儒案。在那个案件中,不仅我会出现,舒亶和何正臣也会出现。这两个大案同时要办,办得好是应该的,办得不好就要受罚,因为办案子而受罚的官员还少吗?这些年,官家专门设局,重修法典,敕令格式,越修越细,各种禁令无所不在。想到这里,我的身体一会儿发热,一会儿发冷。那乌鸦叫得真是让人烦心。
官 家
每个人的故事都会讲上三遍,我的也是。即使贵为天子,我也逃脱不了这种命运。
夜深了,周围的一切慢慢地隐入黑暗,只有眼前的这幅《早春图》除外。在画中,主峰赫然立在当中,俯视着万物,主峰下面是近峰、次峰,松木下面是小卉、女萝、碎石。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看了多久。
元丰以来,我独断乾坤。在这件事上,从熙宁年间,无论是新党旧党,早有呼声,不过意思却完全相反。王安石劝我要“独断”,无非是要借我的权威开路,而司马光那些人是想要我抛掉王安石。
此前,苏轼就不断上书反对新法,熙宁年间的万言书还说什么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此前让他不入国门,已经给了他一个警告,没想到到了湖州任上,还是不改那个臭脾气。上任表上,语带讥讽,李定的奏状说他出言狂悖,真是一点没错。上书我也忍了,为什么要用诗文这种形式,还刊行于世!以前还可以说是冲着王安石去的,但如今,这是冲谁来的?
如今,天下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天下了。北边,西夏、契丹环伺,边事未宁。南边,还有大理、交趾,纠纷不少。内政上,也是官制冗杂,法令不行,苏轼名声越大,越是坏事。以前王安石就反对“异论相搅”,说是要“一道德以天下同俗”,做到“人无异论”。此人不责罚,政令如何推行?
我背负着祖宗的期望,也背负着祖宗的债务,尤其是我那父亲,他好像一直在黑暗中看着我,用他那病恹恹的却不服气的眼神。想起父亲,我总是免不了心酸。
父亲的谥号是英宗,他遭受了那么多的委屈,哪里有什么英武可言!谥号一个字,就是一把刀。至和三年大年初一,本该是一个喜庆的日子,却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以往的大礼之年,会有七头大象在宣德门和南薰门之间的御街走个来回。在宣德门楼前,七头大象还会团转行步,向北舞拜,叫好的“有巴、有巴”声不绝于耳。但是那一年,没有大象,没有焰火,什么也没有。没过几个月,仁宗皇帝大薨。在传遗诏时,父亲惊叫道:某不敢为,某不敢为。后来他还得了病,不能上朝。仁宗皇帝的曹皇后临朝称制,垂帘听政。
这位曹皇后也是个奇女子。她是本朝开国名将曹彬的孙女,本来是要嫁给画家李植,不仅立下婚约,而且已经过门。李植醉心于神仙之道,对她爱搭不理,结果一天晚上,曹氏翻墙而去,没有完婚。这事有段时间传得有鼻子有眼,那些说书人好像就站在围墙下看见这一切似的。后来曹氏被立为皇后,这些流言才慢慢消失。
我之所以记得这些,是因为父亲跟我说起翻墙这个细节的时候,脸上露出的那种暧昧的笑容。传言有时像风中的叶子,没个来由;有时又像水中的石头,言之凿凿。有人说,父亲得病后,出言无状,总是忤逆曹太后,还说什么“太后待我无恩”。这些话当然没人敢在我面前说。那时,我已经长大了几岁,心里清楚我必须装着不知道的样子。
父亲登上大宝只是四年,就撒手而去。那些事情梗在我心里,我不想说,也不能说。以前母后总是笑着说我身体里一定住着一个老人。本朝的大臣也惊讶我那时在王安石面前怎么会如此礼让。我乐意展现出谨慎而老练的形象,我要证明父皇这一支血脉是当之无愧的大宋天子。我的身体里居住的也许还有一个小孩,一个总是盼望着大象的小孩。但是,我决不能让这一点暴露出来。
福宁殿前,风吹丁零,更添一片寂静。祖宗们并没有逝去,他们就环绕在我的周围,注视着我。
第二章 入话
以此撰作诗赋文字讥讽,意图众人传看,以轼所言为当。
——《诗案·供状》
……又虚称更无往复诗等文字……又虚称别无讥讽嘲咏诗赋等应系干涉文字……再勘方招外,其余前后供析语言因依等不同去处。
——《诗案·勘状》
见勘治苏轼公事,应内外文武官曾与苏轼交往,以文字讥讪政事者,该取会验问看若干人闻奏。
——《诗案·御批》
御史中丞
名字。更多的名字,更重要的人的名字,我要的就是这个。
当时官家一下旨,我就派舒亶和何正臣到各地搜集证据。证据并不难找,苏轼在杭州任通判的时候,那里的书商就开板雕印《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从熙宁年间一直印到元丰年间,越印越多,还出了续集。真是妖言惑众,鼓动流俗。除《钱塘集》外,舒亶又找出市面上流通的苏诗“印行四册”。何正臣更厉害,他搜罗到不少尚未刊印的苏轼诗文,包括和他那些朋党之间的往来作品。张璪见了这些“诗账”,大呼:你们还真是下了不少功夫。
当时官家下令让我和张璪一起审问苏轼,我还有些担心,毕竟他和苏轼是同年进士。他本名张琥,后来改名张璪,在陕西凤翔时,和苏轼共过两年事,交情甚好。那时苏轼给他写过一篇文章《稼说》,里面有两句“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甚是有名。不仅如此,苏轼还让他把这篇文章带给苏辙,也算是把他当兄弟了。这两天,张璪真是让我刮目相看。他有时冷不丁地冒出一句话,让苏轼愣半天,那副惊讶的表情好像从来不认识这个人。
这次,苏轼所涉的罪名不小。按照本朝律法《宋刑统》,如果“指斥乘舆”的罪名成立的话,那可是十恶不赦中的第六条“大不敬”罪,“情理切害者”,当斩首;如果达不上“情理切害”,处以二年徒刑。更为重要的是,前者是遇到大赦也不能赦免。从目前涉及的证据来说,牵涉的人很多。这些人收受苏轼讥讽朝廷的文字后,不仅不上报,还阴通货贿,甚至拊掌击节,真是岂有此理。
但这几天,审讯并不顺利。苏轼这人果然奸猾,对所涉诗文,要么避实就虚,要么大事化小,好不容易吐出了几个名字,也都是通判这样级别的货色。像什么旧党的张方平、范镇、司马光等人,提都不提。
对此,舒亶十分愤怒。有那么一刻,我感觉他甚至会扇苏轼几个耳光。按说舒亶也是文人出身,但嘴上总是挂着什么“断柴”“夹帮”之类的话。他在临海当县尉时,有个弓手喝醉了,在县衙里大呼小叫,舒亶用鞭子抽他,那个人还笑,被改为杖脊,还是不服,叫嚷着:有本事把我给砍了。没想到舒亶上去就是一刀,那人的头颅骨碌碌地滚到地下,脸上还留着惊讶的表情。舒亶虽被弹劾,却因此名声大噪。他被王安石看上了,办了好几个大案,像画《流民图》的郑侠的案子就是他办的。
相比起舒亶,另外一个御史何正臣总是阴阴的。说实话,我宁愿和舒亶这样的人打交道,也不愿意见到何正臣笑嘻嘻地迎面走来。但是现在,我可不能这样说。手头上这两个大案,少了谁都不行。
深夜里,我一个人留在御史台,看着那六扇屏风,那是我的前任蔡确大人请郭熙画的。这些年,郭熙真是得了官家的恩宠,皇宫、行宫都是他的画。郭熙的画要比苏轼的画好太多。苏轼画的什么丑石奇树,石头浓墨一团,树也是光秃秃的,七扭八扭,像一只挣扎的手。
蔡确大人赴任参知政事时送了我一句话。他说:资深啊,你接任御史中丞这个位子,有一点要记住,不要恨你的敌人。我当时一愣。蔡确大人是办案子的高手,连相州案那么难办的案子都办下来了,而我却卡在这里。
看来,我得想个办法。其实舒亶此前曾经说过,像程老三这样的货该用的时候还是要用一下。何正臣也笑着点头,摸起了胡须。想到这里,我不由自主地挥了挥手,好像是要把这突然浮上来的一幕赶走,又好像只是为了驱赶那些在灰黑色光线中乱飞的蚊虫。
台 吏
天气太热,空气好像在发虚,颤抖着,发出嘶鸣。我一度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这些天,御史台一直在审讯苏轼,而我负责记录。审讯的声音一会儿远,一会儿近。
知谏院的张璪,御史中丞李定,还有御史何正臣、舒亶轮番上场。他们围着苏轼,不停地问,这句是什么意思,那句是什么意思。听起来不像在审讯,反而像是在开一个诗会。我坐在条案后面,一边记录着苏轼的供状,一边翻着那些作为罪证的书册,手都有些颤抖。以前的罪证五花八门,要么是作案的工具,要么是仵作的验尸报告,或者是受害人的血衣之类,而现在,就是一本本从街面上搜罗来的书册。它们有着如此清白的面孔,又呈现出不为人知的威胁。
苏轼身着囚衣,戴着镣铐,摆动着手,像一棵被雷劈过的树,枝丫颤动,青烟直冒。光斑在不同人的脸上闪烁,一会儿移到李定他们的脸上,一会儿移到苏轼的脸上。就这么几天,苏轼好像已经瘦了不少,颧骨显得越来越高,像岩石一样反光。
我一边记录,一边却在走神。惹上麻烦的不仅有苏轼,还有我。前些天,开封府的两个皂吏找上门来。来的是一老一少。他们问我平时干什么,我一时有些发蒙,没有说话。那个年轻的说:你是牙粘住了?我说:平时在御史台当差,闲的时候,陪着娘子去瓦子看看热闹。那个老的笑了笑说:只是看看热闹?我一头雾水,心里直打鼓。过了一会儿,那个年轻的皂吏又说:你前些天是不是去了平通书坊?
前两天,我确实是几次找过平通书坊的陆老板,但这和开封府有什么关系?我之所以去找陆老板,一是为了讨钱,二是上次印的那个话本,错漏百出。这个陆老板平日里卖书,自己也有几间雕版印刷的作坊。作坊在南薰门那边,我还问过他,为什么要把作坊放在这样一个屠猪的所在,多臭啊。他笑了笑,说我不懂。我寻了几次,都没有找到他。书坊和作坊都关着门,问旁边的街坊,说是前几天还开着,不知道怎么就关了。
两个皂吏在屋子里转来转去,厨房里,有一个竹编的蒸笼,那个年轻的皂吏也用佩刀戳开,好像里面有蛇。到了后来,那个老的皂吏说:你那个《三梦记》呢?
我有些惊讶,他怎么知道《三梦记》?我说:烧了。这话一半是真,一半是假。有一天,我看着那本印得乱七八糟的《三梦记》,想起陆老板那张胖脸,一气之下,扔在铜火盆里,刚烧着两页,却被娘子一把抢起,噼噼啪啪地灭了火。
那个年轻的皂吏说:你恁地是故意的吧?
我说:公人,遮莫和《三梦记》有什么干系?
那个老的皂吏阴笑了两下,说:迟早你会知道。临走时,那个年轻的皂吏扔下一句话:有那个姓陆的任何消息,立马报告。
那天我唯一庆幸的是娘子不在家,她去给庙里读书的小弟送衣裳去了。开封府找我的事,我一直没对她说,说什么好呢?这是她第三次怀孩子了,前两次都没保住。我可不想让她担忧。
那天晚上,我一直想着《三梦记》的事,怎么想也想不出一个所以然来。那只是一个平常的故事,故事讲的是:有一个叫柔奴的市井女子,梦见了一个千里之外的书生。她孤身上路去寻找梦中情人,却在淮河边遇到了水贼。那些水贼是五通神的教徒。在传说中,五通神本形如猿,却可以化为多种体相,冷如黑铁,阳具甚伟,被他们侵害过的女子,往往会浑身痉挛,陷入狂乱的状态。
巧的是,正在此处,她遇见了那个书生,他也被水贼所擒。后来,她抓住一个机会逃生,并到官府报案,官府出动官兵,剿灭了水贼,书生获救。她告诉他梦见的一切,书生却嫌弃她已经被水贼所污。女子伤心投水自尽。她的魂魄荡悠悠一路飘到地府,始终不肯投胎,咿咿呀呀地唱着。阎王听了,派遣小鬼把已经高中进士的书生勾摄到地府来。两人喜结连理,回到阳间过上了好日子。
当时写完已是深夜,我激动地在小院里乱转。那是一个春天的晚上,隔墙之外,有人在叫卖杏花,刚下了一场雨,叫卖声显得很辽远。我忍不住叫醒了娘子,等到故事说完,她像猫一样打了个哈欠,说:那个书生后来就不嫌弃她了吗?
我一愣,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我不嫌弃。
娘子也不觉得我这句话有些古怪,说:好吧。不过名字取得不好。
我一时有些不解,说:什么名字,《三梦记》吗?
娘子说:那个女人的名字啊,叫什么柔奴。
我说:市面上的话本不都这样吗?文奴、俏奴、画奴什么的。
娘子说:奴啊奴的,多难听。
我有些诧异,本想继续说,看了一眼她的肚子,又把嘴边的话咽了回去,说:你说叫什么名字好?
娘子脸上有些愠色,说:花斑马,你是看我怀了孩子才这样说吗?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不叫柔奴叫什么?
娘子笑着说:她哪里柔了?叫苏胜仙如何?那天,她穿着鹅黄的襦裙,光线停留在她的脸上,让她看起来像春天河边的柳树。
听了这话,我也笑了,说:这个好。
她有些不相信,说:当真?
我说:当真。不就是一个名字嘛。
她说:这是名字的事,也不是名字的事。过了一会儿,她叹了口气说,故事都是你们男人讲的。
听了这话,我一冲动,说:要不你来写一个故事?
她一听,又笑了,没说是,也没说不是。
现在想来,我并没有把那个念头当真,娘子也好像忘了那个事,而开封府的公人来找我,更说明那是个馊主意。不过,一个话本能惹出什么样的麻烦?我又没有像苏轼那样写什么朝廷的事。
这样的想法并没有说服我。这天,又是审到深夜,当我穿过院子交接文书的时候,节级程老三匆匆而来,差点和我撞到一起。他骂了一句,甩身而去。这个程老三最喜欢提着一根长长的鞭子在牢房里边走边说:唉,好久没用了。说着,手突然一抖,鞭子啪的一下抽响,吓得那些囚犯直低头,而他却哈哈大笑。这些事都是牢子梁成告诉我的。在御史台,我有时会和他扯扯闲话。他说,如果一个地方流了血,即使经过很长时间,只要用醋浇在上面,那些血痕也会慢慢浮现。说完,梁成突然骂了一句:程老三这个直娘贼。
我呆呆地看着程老三的背影,这一次,他又去干什么?
苏轼会死吗?想他死的人可不少。
节 级
相州案之后,我升为节级。这都算不上是一个官,但是,给我程老三任何官我都不换。
械、枷、纽、锁,多么硬气的名字,我的口腔里弥漫着血气,身体兴奋,好像我面对的是一个个妓女。其实,面对那些女人,我有时毫无感觉,那些令人沮丧的经历甚至让我感到恐惧。很多个夜晚,我走向那些女人,并非是出于欲望,而更像要证明什么。
在台狱,我不需要这么做。这是我的地盘,听着那些喘气、颤抖、号叫,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满足,那些声音让任何瓦子里的曲子都显得造作。看着那些扭曲的面孔,我会情不自禁地扭动起来:这是我的沙书地谜、歌舞百戏、踏索上杆。
御史中丞大人李定一定会骂我狂妄,他是一个书呆子,哪里知道这些。况且他太心急了,粗暴就意味着粗糙。惩罚是一门艺术,不允许任何荒腔走板。在这方面,蔡确大人才是大师,他平时也喜欢写诗作画,我不知道他是怎么习得这门手艺的。很多人以为只要往死里整就行,多么肤浅。这就像写诗一样,在这个行当,只有零星的天才,要成为顶尖的高手必须要有对冷酷细节无止尽的胃口,才能化腐朽为神奇。
办相州案时,大理寺的官员抓了一大批,戴着枷,在日头下暴晒了五十七天。除此之外,蔡确大人还把各种刑具摆在犯人前面,自己带着笑,轻言细语地说这个枷是怎么用的,那个箍上紧的时候脑骨会像杏子一样噗的一下炸开。说完,他还张开手,好像真捏爆了杏子。
当时的御史中丞邓润甫深为不满,上奏给官家,说“蔡确深探其狱,滋蔓不已”。在奏章里,他还说在深夜里,亲耳听到过囚犯发出的惨叫。官家派了三名官员到御史台按验,但是问遍了相州案的数百囚犯,却无人承认,也没有伤口作证。邓润甫只能承认自己“奏事不实”。那些惨叫是真的,相州案的囚犯无人受到拷打也是真的,这事我最清楚不过了。蔡确大人只是轻轻使出一招“移花接木”,就让邓润甫掉到沟里去了。
元丰元年六月,案子结案。去官的去官,降职的降职,坐牢的坐牢。邓润甫被免去御史中丞一职,贬去抚州。最终的大赢家当然是蔡确大人,他从知谏院兼判司农寺升为右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在御史台,他又办了几个案子,很快升任参知政事。他走后,御史中丞就变成李定大人。蔡确大人一定会当上更大的官,而我程老三,做一个节级就够了。
苏轼进来的时候,没有交常例钱。我没有生气,我不需要生气。我对他说:苏大学士,我们会好好照顾你的。说完,我扭头就走。此前,梁成曾经跟我说过,苏轼没有什么钱。听了这话,我倒是笑了。他还真把这里当成修行的地方了吗?另外,我也搞不懂苏轼,他堂堂一个太守,怎么会没钱?不是说写个墓志铭,就能捞上一大笔吗?不过这些天审讯下来,说起苏轼借钱的各种事体,倒不像是假的。他收养了不少孤儿,还把俸禄捐了,建什么医馆,取名为安乐坊。别人安乐了,他自己倒欠了一屁股债。
案子不顺,看到御史中丞大人李定抓耳挠腮,我心里就觉得好笑。这可比蔡确大人差多了,更大的官都被收拾得服服帖帖,怎么到了苏轼,反而没招了呢?在台狱,只有一个人给我惺惺相惜的感觉,那就是舒亶大人。有一次,他说起了断柴、夹帮之类的话,我一听,心里乐坏了,就像一个酒徒听到了“眉寿”酒。
这些话外人一般听不懂。所谓“断柴”,就是做到受刑部位表面好像只是一点瘀肿,里面的骨头其实已经断了。而两块木头夹在脖子上,就叫“夹帮”,厉害之处就在于木头之间的缝隙让犯人生不如死。而“脑箍”是用绳缠住脑袋,用木框框住,这一点和“夹帮”很像,不过一个针对脖子,一个对付脑袋。而所谓“超棍”,就是把犯人的胳膊反绑,让其跪在地上,再用短小的竖木别着,不出半晌,膝盖必碎。
这一次,也是舒亶大人找到了我。我一开始以为也是要来些硬货,但没等我说两句,舒亶大人就打断我,说:这些手段使不得,会留下外伤。
他问我:有没有别的方法?对付诗人的方法?
听了这话,我咧开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