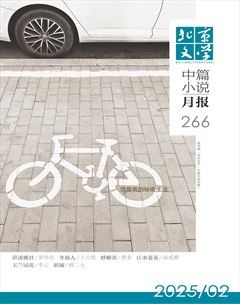古老的瓜洲渡口,见证了世间男女的爱恨情仇——杜十娘的决绝,渔家夫妻的生离死别,现代人的迷惘。那些不堪侮辱投江自尽的女子,那些站在江边寂寞守候的人们,仿佛平行时空下的同一场大寐,他们在逃避命运的途中一次次撞见命运。
一
要不是手头拮据,我是不会接下这个活儿的——写一个舞台剧脚本,关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故事。活儿到我手上估计转过不少于三个人,因为层层剥皮已经没什么油水了,八十分钟的舞台剧本只付稿酬八千多块。
找我的是一个叫徐老师的人,我们并不熟悉,是在一次采风活动中认识的,徐老师具体做什么我也不知道。那次采风他给大家递名片,也包括我。名片上头衔很多,什么会长啊理事啊顾问啊……从名片上我没看出他究竟是做什么的。听说我写小说,他执意要留下我的联系方式,又掏出一张名片让我在上面写下手机号,再将有我号码的名片小心翼翼地放在包的里层。
是部里的活儿,徐老师对我说,政府上下非常重视这个舞台剧。
我会认真对待的,我说。重视就只付八千元——这后半句是我的心理活动,没说出来,毕竟,我也不能和钱过不去。那段时间我真是穷疯了。这么说吧,穷得差点把抽了十几年的烟给成功戒掉。
我是一个严肃文学的作者,我常常这样介绍自己。但这句话的潜台词似乎又在告诉别人自己是个穷鬼,文学与穷困潦倒之间有个隐约的等号。好在每当自己快要挺不过去的时候,就会出现一点转机,接到一些写软文的活儿。有一次是朋友的婚庆公司找我写一份证婚词,给六十块钱我都兴高采烈地答应了。朋友问我以后要是还有这样的活儿感不感兴趣,我告诉他,感兴趣,只要有钱。我知道那个跌到庸俗里的自己,都是为了守护文学圣洁的那个部分。这么一想,突然觉得自己神圣又伟大了不少。
杜十娘的舞台剧将在瓜洲的大剧院进行首演。大剧院是市里重点投资的工程,建在长江边上,两片椭圆形的屋顶如同两只船桨,斜插在江面上,有点振翅欲飞的意思。徐老师两天前带我来大剧院,远观,没进去,他指着大剧院船桨一样的屋面告诉我,就这儿,首演,市里四套班子都会来,这也是你的荣誉。
我没说话。这荣誉当然不是我的,因为舞台剧的署名还不定是谁呢。不过,那不是我关心的,我只关心什么时候付我第一笔润笔费。
徐老师很快就将第一笔稿费打到我微信上了,一千元。收到钱后,一连几天,我都在傍晚时分骑车去瓜洲江边。我想找点感觉。
江岸长满了芦苇,一人半高,要想走到水边并不容易。秋天的江面宽阔不少,芦苇的黄色与江水的浑黄有了一脉相承的感觉,苇花飞扬,呈现出一种蓬勃的姿势。京口瓜洲一水间,自古以来,多少文人墨客从这里往返两岸,李白、白居易、张祜、王安石、欧阳修等等,当然,也包括我将要写的杜十娘和李甲。想到这些,竟生出些许感慨。
这一带江岸线有十多公里,以汽渡为界,东侧为几家船厂,土红色的龙门架一列列排开去,西侧是森林公园,由几段院墙圈住。很多年前我和小越还去里面玩过,没什么设施,只有树和草,但人工修葺的痕迹还是挺重。第一年森林公园搞了场音乐节,貌似挺成功,十里八乡的百姓都来了,有点赶集的意思。火了一两年,突然就没了人气。现在的森林公园又回到野生状态,藤蔓肆意生长,水草蔓延,就连小广场的地砖都有了自暴自弃的放纵,串通好了似的,集体碎裂。
我翻过一道围栏,没走多远发现还有一道,再翻过去,前方又出现一道,顿时感觉自己像个跨栏运动员,当然这比跨栏费劲多了。当我从最后一道围栏上跳下来,便离江岸很近了。
若干年前,芦苇还没这么茂密,有条小路可以走到水边。那时我和小越正读高中,周末偷偷溜出来约会。也不过是在公园里坐坐,或在江边走走。我们之所以选择瓜洲江边,是因为不会遇见人,可以在货轮远去时偷偷拥抱一下。
那时我们还没有懂得恋爱的真谛,以为把两个人的时间重叠在一起就是相恋。岸上白沙堆积,小贝壳裸露出来,江水噗噗地啃噬岸边,我们除了在沙滩上反反复复留下两串脚印外,还不知道再干点什么。有一次,我们在江滩上捡到一枚古币,古币上隐约有一个“万”和一个“通”字,我猜是明代的万历通宝,小越则认为可能只是个游戏币。那个下午,我一直将古币放在手上把玩,好像把玩着时间的某个隐喻。
也是在那一次,我们还发现了一块断碑,半边埋在江沙里,碑上写着“瓜洲古”仨字,“渡”字不见了。
我站在江堤上,与江水之间隔着重重芦苇,江水雄浑,货船缓慢驶过。这几次来都没看见过人,我断定这里少有人迹。是啊,人们要去江边,何不去仪征或六圩,那里的江岸不错,岸边修建有水泥台阶,一截一截延伸到江面。唯独瓜洲这一带,荒凉得只剩芦苇。我正出神,手机叫起来。是小越,劈头就问,写得怎样了?她指的是那个舞台剧脚本。我回说,正在等待开天辟地的第一个字到来。
你就说你还一个字没写呗。说完,小越一阵狂笑。
的确,我还没想好怎么写。已经第四次来到江边了,仍没找到感觉。我想,或许,我并非要找感觉,而是要找另一件东西,断碑。
二
我想把杜十娘与李甲的第一次见面作为舞台剧的第一幕,然后再对各自身份进行交代。当然,这是文学作品里的常用叙事方法,舞台剧更多的是采用线性顺叙。
这是我固执的想法,这么做的缘由是我对人与人的初见颇感兴趣。人生若只如初见,初见是一块浑玉,未经雕琢。我想起自己与小越的第一次相遇。高一军训,我先是在操场上遇见一个女孩,女孩的眼神,以及时刻撇着嘴的神态,都让我感到十分亲切。后来发现女孩和我一个班,鬼使神差地竟成了我的同桌。当然,这样的桥段电影与小说里用得不少,我并非要虚构我们的相遇,事实就是如此,我必须尊重事实。我记得那个夏天小越留给我的感觉,如同一枚青色的桃子。这枚桃子的滋味一直刻在我的心中,每当我们闹得不愉快,只要一想到这枚桃子,我就会原谅所有。当然,我在小越心中是一枚桃子吗?还是另一种果实?不知道,小越说是动物,是狗。我问是什么样的狗。舔狗,我们异口同声地说。
断碑找到了吗?小越发信息来问。我回她还没。
碑是一九四九年二月所刻,新中国成立前,碑上写着时间。记得我和小越还为“二”月还是“五”月揣摩了一阵,后来发现,那凭空多出的两小竖原来是人恶作剧画上去的。
发现断碑是十六年前,那时断碑紧挨着江水,但凡有货轮经过,江水就涌上来,将碑上的细沙冲得干干净净。这十多年江岸又北移了许多,泥沙冲积而成的江岸被芦苇吞没,仿佛芦苇与江水在进行较量,争夺地盘。十多年前发现断碑的位置,应该为现在的芦苇丛。
我打算再走一遍。小越问我,为什么非要找到断碑不可,与你写脚本有什么干系呢?
这么说吧,找到它,就如同找到了脚本奠基石一样的第一个字。我说。
小越在电话那头笑岔了气。
远处有个人影,我连忙挂了电话,从土坡跳下去。
人影不见了,四野寂静。这么多天来,第一次看见人,这让我一阵恍惚,刚刚是不是出现了幻觉?
手机又响了,这回是徐老师,问我脚本完成得怎样。
写了一小部分。我撒了谎。
可不可以先发给他们——他用了一个含混的词:他们。又说,让排练的演员熟悉一下内容,毕竟开年就要演出,时间紧迫。没问题吧?徐老师小心翼翼地问。
有个人——我叫了出来,我又看见那个人影了。
什么问题?有个人?是不是有个人物还没处理好?对方问。
电话已经被我挂断,我看着人影发呆。人影离得很远,偶尔露出肩膀和脑袋,芦苇拂动,如江涛滚滚,将那脑袋推至远处。
再看手机,微信上多了个转账。徐老师发来的,一千元,算是第二笔稿酬。
我继续在苇丛里走,回忆十多年前断碑的位置。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它早被附近的居民捡走了。虽不是什么文物,但可以做个石桌,或者立在门边,成为泰山石敢当。
第二天我没去江边,把自己关在出租屋里憋了一段,这是受第二笔稿酬的蛊惑。然而写得极不满意,便退出来,将文档删得干干净净。
次日再去江边,这回带了把铁锹,向物业借的。我觉得自己有了执念。
小越说,没必要那么认真嘛,找不到断碑就没法下笔吗?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好像自己在跟自己较劲。江水东流,冲积出厚厚的江滩,比起十多年前,江沙厚积,也就是说,那块断碑或许正埋在江沙里。我仔细回忆十六年前的夏天,我们站立的位置,与对岸工厂的烟囱正对着,金山在我们四十五度角的方向,两条直线就能决定一个点的位置,我用锹在地上做着记号,将一条虚淡的线指向苇丛。确认无疑了,便动手开挖。芦苇盘根错节,斩断了几棵芦苇,锹方能下去,沙土有些板结,挖了一阵,白色的江沙有了湿润之气。锹头不时碰到一两个硬物,发出尖厉的声音,再用力,撬出一片瓦来,上有青花线条,看不出年份。
这江岸从唐朝就是渡口了吧,唐朝的瓜洲也是入海口,张若虚大约正是站在此处,才写出那句“春江潮水连海平”的。再然后,宋朝、元朝,直到民国时期,渡口一直络绎不绝。我站在隆起的沙堆上,刚要感慨,却又看见了那个人。我立即向他跑去。
有鸟从苇丛里飞出来,扑棱棱挥着翅膀向着远处飞。我继续拨开芦苇,秋天的芦苇变得坚韧有力,如同一只只手臂拦住了去路,脚踩上去,发出脆骨断裂一样的声音。这样向前走了一阵,觉得不对劲,如果那人走在我的前面,一定也会出现芦苇被踩断的现象或者断裂的声音吧?但芦苇整整齐齐,像无数双手臂勾肩搭背在一起。我退出来,重新找一个入口,就这样来来回回几次,我迷路了,仿佛走进了桃花阵,不对,是芦苇阵,不是我在移动,而是芦苇移动,将我裹挟在原地,寸步难行。
有一阵我感到虚汗淋漓,在我快要放弃时,那个人影又出现了。他背对着我,背有点驼,头发是跟苇花一样的花白色。
嗨——嗨——我开口,风把我的声音倒灌回来。
他走得很快,好像芦苇自动给他让了道似的。如果我的上空有一双俯视的眼睛,一定能看出我和这个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长,芦苇如江水汹涌。此时有两条江,一条是从上游奔腾而来,一条是从岸边铺张过来,后者是芦苇构成的江,比前者更浩瀚、更汹涌。
三
许多日子后,再回忆我和老杨相遇的那个黄昏,多少有点武侠故事的意味。当我在芦苇丛中横冲直撞,突然发现前方一片开阔的菜地,芦苇整齐地将菜地圈在其中。倒是奇怪,菜地并非沙土,而为褐色的肥沃泥土,想必是从别处运来的。地里点了萝卜,红艳艳的,一只只就要从泥土里挣脱出来。正疑惑时,有人在我身后说话了,正是老杨。彼时老杨肩上也扛着一把锹,我们各执一锹对峙在浩瀚的芦苇丛中,这充满张力的画面常在我脑海中出现。
像电影画面。后来我对小越说。
有点《十面埋伏》的意思。小越回答。她总能知晓我内心的一切。
来这儿挖地?画面中的老杨先开口。
我没听明白,摇摇头,又点点头。他放下锹,说,这不是种菜的地方,你要是种菜应该到瓜洲坝头村一带,那儿土质好。
我这才明白老杨把我当作和他一样种菜的了。老杨有八九十岁模样,穿一件灰蓝对襟,背有些驼,脑袋直勾勾地伸向前。他说看见我在这一带转悠几天了。
看来前几天他也发现了我。我告诉他自己来这儿是寻找灵感。
灵感?老杨扬起眉。
要写一个舞台剧,找一点灵感。我说,当然,最主要的是找到断碑。断碑,你知道吗?我用手比画着,这么长、这么宽,花岗岩的,上面原刻有四个大字,瓜洲古渡。
老杨直愣愣地看我,问,这个有什么用?
我迟疑了几秒,心里断定老杨应该是附近的村民,以捡垃圾为生,断碑说不定就是被他捡走了,正等待识货的人出现呢。
跟你写舞台剧有什么关系呢?老杨又问。从老杨的谈吐看,他不像是目不识丁之人。我问老杨,怎么跑到江边这么费事地种地呢?老杨沉默了,半晌才说,大半辈子了。
两只噪鹃在头顶呕啊呕啊地叫着,我们不约而同仰起头。天快黑了,暮色如同帘布倾覆下来。回去咯,老杨说。是说给他听,也说给我听。
他将铁锹扛在肩上,分开苇丛向前走。天色渐暗,我没有跟过去,只看着他的背影逐渐被芦苇和暮色淹没。
晚上我将与老杨相遇的事说给小越,她那边正是清晨,小越说窗外的晨光也是墨蓝色,和你那儿的暮色一样哦。小越常常感叹于此,说时间在我们之间出现的偏差。我说是啊,照耀过你的月光正在照耀着我。
我们继续聊老杨,小越认为老杨应该是个有故事的人,我不赞同。小越向来感性,对人常怀有奇思妙想,这一点倒比我更适合写作。我则认为老杨原本是附近的村民,这些年城市发展快速,吞噬村庄,农民成了没有土地的人,住进了安置房,原来的村里人成了上下层邻居,村庄竖了起来。种不了地,终日不安,于是将房子留给既不是城里人也不会种地的子女们,自己扛着铁锹、锄头,去了郊外。他们在那些围墙圈着却迟迟未动工的工地上开垦出一片菜地。那些长满杂草的院墙边、河岸,都能种出粮食来,只要有泥土,就有希望。
我曾从一个围墙的缺口走进去过,里面真是另一番景象。这些村民白天种地,晚上去小区的垃圾桶里捡饮料瓶子,捡来的空瓶子堆在菜地旁。垃圾桶里什么都有,毛绒玩具、坏锅、断腿的塑料凳子,有时还能捡到一个沙发,运到菜地旁,蒙一块塑料布就是家。老杨应该也是其中之一,只是他没去未建工地而选择了江边,江边安静、地大,说不定还能捡到一两枚古币呢——
小越在电话那头笑起来,说,你以为每个人都能和你一样幸运地捡到古币吗?我反驳,捡到古币的可能性还是挺大的,这里是一千多年的渡口,承载过几个朝代的盐运,别说古币,就是捡个青花瓷器也是有可能的。
对方突然没了声音。视频里,小越不见了,一会儿过后,再出现时手上多了一枚古币。
我说,没想到你把它带到加拿大去了。
小越撇了撇嘴,说,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它代替了你。
我们都沉默,这个玩笑并不好笑。
小越说,杨欢,这可是你送给我的最贵的礼物呢。
我说,这不贵,捡的,网上回收也就五百元。
但它无价,小越更正我,又说,因为它是被你捡到的,所以它独一无二。
我没接话,对于这些饱含感情的语句,我都不知道怎么接住,似乎已经习惯了彼此开开玩笑,相互挖苦和讽刺了。
绳子断了几次,小越说。她将古币在镜头前晃动,古币被一根玫瑰红绳子系着。小越说,它从铜块锻造成铜币的那一刻,是多么神圣,我把它拴在身上,就仿佛拴住了那一刻的时间。
我突然想到古币为万历年间的,正是我要写的杜十娘和李甲的万历年间。
小越扬了扬眉,说,有意思。
是啊,我看着镜头,问小越,有没有可能,这枚古币曾从杜十娘的手上经过……
四
脚本写得并不顺利,要将这个流传几百年的故事完美地搬到现代舞台上,还是很令我头疼的。当初徐老师把材料交到我手上时,有点接力棒的意思,准确地说,是烫手山芋。
我和老杨已经熟悉许多,至少他不像前几日那样躲着我,但我仍然搞不清楚他住在哪儿。若是住在远处的村里,那为何跑到芦苇荡里种地;如果就住在江边,茫茫苇丛还真没发现可以居住的地方。每天天黑前老杨对我说“回去吧”之后,就消失不见了。
好在我并不太关心他的去向,我只想打听断碑的事,或者,在江边走一走,看汽渡来来回回行驶在两岸间。我告诉老杨自己作家的身份,老杨点点头,说,好,拿笔杆子,好。
我每天来这儿,寻得一两个妥帖的句子,再小心翼翼地挪到电脑上去,就像老杨每天从菜地里带回一两把菜一样。老杨住哪儿我不知道,菜地倒是见识过了。一共有四块地,其中一小块地种了红薯,过些时候就要收获了,还有一块地种了水稻,我去看的时候,水稻刚刚割完,稻茬还直挺挺地立在地上呢。老杨说,让这块地歇一歇,等到明年再种。
瓜洲这一带种两季庄稼,稻子割了会种上麦子,来年春天收了麦子再插秧。我觉得老杨不种麦子除了让土地歇一歇,更多的原因是怕被人发现吧。秋天芦苇枯萎后,麦苗却是绿油油的,从远处看,很醒目。老杨在江边种稻这事,让我想起自己的一篇小说《奔跑的稻田》,小说写了“我”的父亲到处找地去种稻,他背着稻种,向西走,再向北走,又向东走,没有一块地可以让他放心,最后,父亲到达海边,在盐碱地上种下了稻谷。小说有超现实的部分,我想表达一个热爱土地的父亲,像夸父追日一样四处寻找一片能够孕育粮食的土地。想到这里,我突然觉得老杨和文中的父亲有几分相似,好像我小说中的人物在现实中出现了。
红薯收获的那天,我和老杨忙了大半天,他负责挖,我负责捡,偶尔我也逞能拿起钉耙,用力凿进地里。晚上回来后,才发觉两条胳膊酸痛,举箸维艰,仿佛一条蛇冷冽地游走在骨头缝里,一直到达心脏,突然在心脏位置用力一咬……
当然,凛冽惊异的感觉并非全部来自胳膊酸痛,还有傍晚和老杨的对话——那时我们已经收好了红薯,坐在沙堆上歇歇,我给老杨递了一支烟,他说自己不抽,却接了过去,歪着脑袋借了火,吸了一口,并不咽下,在嘴里绕了一圈,又缓缓吐出。有货轮经过,长长鸣一声笛。暮霭沉沉,江水浩渺,我突然想起四百多年前的夜晚一个女子的纵身一跃。
曾有一个女人跳进了这江里。我悠悠说道。
老杨突然转头,看着我,暮色里我看不清他的神态。半晌后,他才慢慢说道,有三个人在这个江里。
对话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了。这晚老杨没有对我说“回去吧”,他起身,扛起锹和蛇皮袋,径直离开了。
我在江边又待了一会儿,感到浑身发冷。冷气从身体里不断往外冒,汗毛竖立,不禁打了几个寒战,撒腿便往堤上奔去。
小越说,老杨是个有故事的人。
这不是故事,我在电话里压抑着声音说,三个人在江里,你不觉得他身上有几条命案吗?
小越说,杨欢,我不想跟你争辩,但我觉得是你想多了。说完她便挂了电话。最近小越很忙,她在一所大学的动物实验室里干活,每天和白鼠、豚鼠、SPF鸡、猴子打交道,有做不完的实验。在工作室,小越不用手机,等她下班之后,我还在睡梦中。所以我们只能在早晨或晚上聊一会儿,她的夜晚是我的白天,我的夜晚则是她的白天,仿佛我们行走在错误的时间里。打电话时也不说什么情话,聊一些身边好玩的事,或者网上看来的笑话,我们的笑点和泪点一致。小越说,这叫情投意合。我更正,这是臭味相投。
这夜我没睡着,在床上辗转反侧,回忆这些天与老杨相处的细节——独居、住所神秘、江边种地——无一不指向他有杀人犯的嫌疑。
接连两天我没去江边,第三天,我决定骑车过去,心想不管是有故事还是有命案,我都想深挖一下。如果是前者,说不定是个小说素材;如果是后者——我突然一愣,心想那就深入虎穴,顺藤摸瓜,获得证据,一举拿下。这也将成为日后写作的素材。
想到这些,不免兴奋了起来。
五
再见到老杨是在江边,他正拿着锹将松垮的沙土像螺丝帽一样拧紧在堤岸上。这一处江滩缺了口子,江水在此处打着旋儿。老杨主动跟我搭话,用锹指着缺口说,江水正想从这儿溜走呢。
老杨像个哲人。
杜十娘纵身一跃,跳进江里,你说值不值呢?我想起几天前对老杨的疑虑,便把话题引到“江里几个人”上去。老杨抬头看我,没说话。我问他听过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故事没,老杨说听过,这戏小时候没少听。
百宝箱里的宝贝真多哦,一件件丢进江里,可惜了。我开玩笑说。
杜十娘,恨满腔,可恨终身误托薄情郎……可知十娘亦有金银宝,百宝原来有百宝箱……一件件,一桩桩,都是价值连城异寻常,何妨一起付汪洋……
这是脚本里的一段唱词。
也没什么可惜的,老杨道,钱财乃身外之物,人死了,物还在世上,物比人活得年岁长,怎么能说这些钱财是自己的呢?人才是钱财的过客。
我打量着老杨,觉得他身上有股说不出来的味道。或许正如小越所说,他身上有故事。
老杨从别处铲来一锹土,填在缺口处,土虚浮着,我用脚踩实,渐渐地,我们有了分工,老杨负责运土,我负责踩平。有一处缺口大得出奇,像是巨人打出的哈欠,江水窝在那儿无法离开。老杨找来几只蛇皮袋,去别处挖来沙土,装进去,沙土便有了形状,压肩叠背地填进缺口,江水立即妥帖地向前流去。
这天老杨没有对我说“回去吧”,我也没有早早跨上自己的自行车,而是一步不离地跟在老杨身后。太阳还没落尽,黄昏的金色光芒笼罩着我们。老杨扛着锹,分开苇丛向前,但速度明显慢了,像在等我。走了半里路,拐了个弯,仿佛折回来,我正要发问,老杨又往前走去,这才发现,是转到一条小路上去了。说是路,不过是两片苇丛之间的分割线,由江沙冲积而成,又被芦苇的根挤成尖削模样。
靠近江水的这边,芦苇明显粗壮一些,高高的,像厚重的屏风遮住人的视线,要不是时有货轮鸣笛,谁会想到这是在江边呢?这样走了一阵,老杨突然又钻进苇丛,苇叶阔大,茎秆粗壮,每一株如树干挺立,人撞上去,似要被它弹回来。我正好奇着,发现前方有一汪水塘,水上漾着一只小船,船是用大铁皮桶对半切开,形成两片半弧形。老杨上船,坐在半个弧形里,示意我坐另外半个。此时他手里的锹成了桨,往地上一抵,船便前进了。
一条窄窄的水道将水塘与江面相连,芦苇将水道遮掩得恰到好处。小舟穿过苇丛,驶过水道,猝不及防地,宽阔的江面便出现在眼前,顿时把人的视线撑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