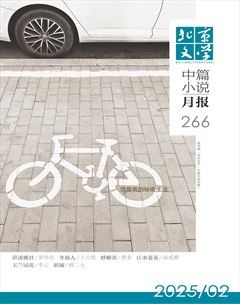一场场煤矿安全事故让孩子失去父亲,妻子失去丈夫,母亲失去儿子。失去至亲的女人们抱团取暖,抵抗寒意。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煤矿往事,尘封的记忆和深眠的魂灵一样,一旦苏醒,皆是血泪沉冤。写好一个煤矿就是写好一群人、一座城市,也是写好一段历史。
一
老庙煤矿一号井矿灯房门前有三棵玉兰树。
玉兰树是春寒料峭时节矿里绿化队来人栽下的,原先,绿化工人是准备栽法国梧桐的,矿灯班的班长朱金莲不同意:“中国人种什么法国树,要种就种中国松。”
当天,绿化队的板车里没有中国松,倒有十来株灰粗杆的玉兰树,矿灯班的人勉强认领了它们,挖坑栽下后,一转月就活了,它不娇气,远没有它宝气四溢的名字那么金贵。
当时,共种下五棵,最后只活下了三棵。
朱金莲说一棵是被宋小春哭死的,那时,宋小春一想到自己丈夫折了的伤心事,就趁着没人扶着树干悄声地哭上一场,还把眼泪鼻涕都抹在树干上。“眼泪不善哩,树哪经得起她这见天见夜的折腾。”朱金莲一见宋小春在哭就会白她一眼,并会对小春说些“我命由我不由天,哭顶个屁用”之类的话,说得宋小春只得收敛她潮湿的哭脸,低着头走向矿灯房的内屋。
还有一棵,陈菲菲坚持说是我尿尿烧死的,陈菲菲说我是死心眼,总是逮着一棵树去尿,“童子尿是药,树天天吃药,那还不得死?”那时的我才六岁,刚随母亲从老家来到老庙煤矿,还没有上学,没上学也没处去,只得跟着好哭的妈——宋小春来矿灯房“上班”了。
朱金莲让我叫她“大娘”,朱金莲的名字是后来才知道的,她大概是淮河以北人吧,口音侉得很,吃饭叫“剋饭”,喝茶叫“喝汤”。她有一副高高大大的身板,大手大脚,红中泛紫的大脸盘上有一双铃铛似的大眼,阔嘴高鼻梁,她总是喜欢穿一双矿上发的翻毛牛皮鞋,走起路来哒哒地响。
陈菲菲让我叫她“姐姐”,妈初始让我叫她“菲菲姨”,她死活不同意:“只叫姐,姨什么姨,还愚公移山呢。”我当然不知道什么是愚公移山,不让叫姨我就不叫,就叫她姐。
大娘一听我叫陈菲菲“姐”,就哈哈哈地大笑,“都二十好几的人了,还老黄瓜刷绿漆装嫩”,姐笑吟吟地向大娘扮鬼脸,一边用拖把拖着地,一边扭着屁股说:“就是姐就是姐!气死你。翠儿叫姐,给你大白兔吃。”一听有大白兔奶糖吃,我自然屁颠颠地跑到她身边,拉着她的蓝色工装衣角,“姐,姐”大叫着,姐那漂亮的眉梢就似喜鹊尾一样上扬了起来,她的长发在她俯下身时,弄痒了我的额头和颈子,蚂蚁咬一样,她会亲我一口,拖着长声地答了一句“哎哎”。
如果,这会儿有矿工来取矿灯或交矿灯,就会有些白脸叔叔和黑脸叔叔起哄说:“翠儿,叫我姐夫,我给你买肉包子吃。”我嘴甜地叫了几声,惹得那群汉子哈哈哈大笑起来,她急忙抄起洗矿灯池里的塑料水瓢,舀起一瓢水向窗外的那群人泼去,窗外那群人四散而去,但没过一会儿又湿漉漉围过来,“叫姐夫,叫姐夫”闹着,这群人中少不了海佬吴和山豹王他俩。
姐这时满脸彤红,鼻尖上急出小汗珠来,转脸皱着快哭的眉头望向大娘:“班长,你看——”
大娘笑哈哈扫一眼窗外,把手里抹布在矿灯案台上“叭叭”抽了两下,发出惊堂木的声音。她收起脸上的笑容,对着窗外的汉子们大声说:“下井的快去屋头晒晒太阳,上井的快去澡堂泡泡澡,再过一会儿,太阳下山了,水也洗臭了,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散了,都散了。”
众人都听她的话,交灯,领灯完毕,分头四散而去。
矿工们走后,大娘会责备姐:“你看你,他们说就让他们说,会说掉你一块肉呀,说句玩笑话儿真能急上眼,还上泼水了,这要是冬天,他们不得冻感冒了,你真冒傻气。”
姐剜了大娘一眼,扭身去和妈一起擦灯去,小声对妈说:“她就会向着他们,好像他们都是她家里表叔二大爷亲戚似的。”
妈只是嘴角咧咧,算是笑笑,也算是接了话。上班不久的妈总是小心翼翼的,生怕惹出什么乱子。
发矿灯是姐的活,收灯是妈的活。大娘只是负责发灯牌,收灯牌。这种分工大概是她仨约定了事,各自干各自的。
干完这些活,姐和妈去洗矿灯池前洗灯,洗那些从井下带回来沾有汗水和煤泥的脏矿灯。这会儿,大娘就会从抽屉里取一支烟和火柴,坐在矿灯房门口的长椅上,抽起香烟来,望着副井旋转的天轮,仿佛陷入了沉思。她把烟抽得很慢,但是,她一口吸得很多,一支烟三五口就抽完了。每次她深吸一口,然后把烟含在嘴里,再慢慢地吐,就像我老家的老灶台。魁梧的她坐在那里,吐着烟,一口烟会被她吐得很悠长,丝丝缕缕的,有时以为她口中烟吐完了,她却一抬头嘴唇轻启,又一缕烟淡淡地从口中和鼻孔飘出。她在矿灯牌架上没有灯牌时,才会扔了烟屁股,走过来对姐和妈说:“你俩歇着去,俺来”。说完卷起袖子,露出粗藕般的手臂,双手插进水池的水里,三下五除二地把小山似的脏矿灯洗了。
妈会在一旁用干抹布把矿灯上的水渍抹干,再把矿灯一一地送上矿灯充电架充电。大娘这会儿对妈说:“小春,你去看翠儿去,这里没你事。”
妈只是低头笑一笑,埋头干活,低头间偶尔会轻轻地说:“有她姐看着呢。”
“她呀,自己还没长大哩。”大娘嗔声。
“哎,哎,我就长不大。”姐领我去食堂讨淘米水,回来浇她养的十几盆花,出门也不忘回头怼上一嘴,姐的马尾辫一颠一颠的,好看得很。
大娘回她:“长不大,精怪”。
后来,我就叫陈菲菲为“精怪姐”了。
每个下井的矿工都有一个矿灯牌,长方形铝片,上面刻着人名、队名和班名,铝片头打了孔,人名用红漆描过,醒目得很。矿工下井前取完灯,灯牌挂在矿灯牌架上,证明他下井了,上井后交完矿灯,取走他的灯牌,说明他已上井——这灯牌其实也是报平安牌。
姐教我数数,就是从数矿灯牌开始的,我数架上的灯牌是二百二十三个。
大娘说:“翠儿数得不对。”
妈也说:“不对。”
我问姐,姐姐见她俩这样说,就悄声:“不对。”
她仨好像都在逗我玩。
这就让我糊涂了起来,接着再仰头数,还是二百二十三个,翻来覆去数了大半个上午,还是那个数,于是我就委屈地大哭起来,因为数错了就得不到姐奖励的大白兔糖了。
姐见我哭了,就把我抱起来朝里屋去,姐的包就挂在里屋墙上。那是一只橘黄色圆形桶状包,是一种塑料材料制成的,上面印着“上海”两字,还有高楼图案。这些当然不是我要关注的,我关注的是包里装着的大白兔奶糖。姐把一捧大白兔糖放在我手掌上,边帮我擦眼泪边说:“你是对的,没数错。”
妈也跟过来:“没错,没错,你数的是对的,别哭了。”说完,妈的鼻翼就有些抽动起来,我知道她见不得我哭,便急忙刹住了哭腔。
大娘走过来看看我,叹了一口气,从口袋掏出一枚矿灯牌递给我:“翠儿,别哭了。来,来,给你个灯牌玩。”
我接过她递来的矿灯牌,一把攥在手心里,好似怕她后悔要回去。回家后,我才看那牌上写的是20号,姓名三个字,我不认识,让妈认。妈只是流泪,没说话。后面刻的班组字,我也不认识,但不敢问妈了。
当晚,妈哄我睡觉时,劝我把灯牌还给大娘,她说:“这灯牌是你大爹的。”
大爹是谁呀?妈没告诉我。灯牌就算是大爹的我也不打算还她,我想一直珍藏在自己的枕头里。
妈看我不还矿灯牌,就叹了口气,在箱子里拿出一枚相似的矿灯牌给我:“翠,这是你爸的,大娘的东西你要还人家。”我把爸的灯牌握在手里,没有看妈的表情,合上眼一下就睡着了。在梦里,我朝不远处的爸爸奔跑,两个灯牌在胸前发出清脆悦耳的铃铛声。
自从知道爸爸折在井下后,我就暗下决心要当保护妈妈的男子汉。我虽然是个女孩,我想等到自己长到和姐那样高时就会变成男孩的。我从不惹妈生气,我知道妈扶着玉兰树悄悄地哭,就是想爸爸了。
窗外白玉兰树刚栽下去,大娘说玉兰树要过三年才会开花。此时,它枝杆茁壮,绿叶肥厚,怎么看怎么不像是能开花的树。
栽树那年应该是1991年,前一年1990年是马年。后来我才知道马年是个灾年,那年秋天,老庙煤矿发生了特大矿难,共牺牲了七位矿工,我爸爸位列其中。
二
我妈宋小春是顶替我爸的岗,来到老庙煤矿当矿灯房女工的,待我长到十八岁,也可以到煤矿上班当工人。
这是矿上的规定,也是当时的优抚政策。每个牺牲矿工的家属可到矿上上班当工人,不过,女性不能超过三十五岁。妈那年三十二岁,她带着我离开了水乡泽国来到了这皖南山区老庙煤矿,算是公家人了。
舅舅的小船在薄雾里划着,把我和妈送到去城里的渡口时,妈伏在乌篷船帮上抽泣,舍不得离开水乡到陌生的地方去。村里送行的人们劝说道:“别哭了,都当工人了,还哭个么子……”仿佛,当了工人,日子就有盼头,爸爸就会回来似的。
我一开始不太喜欢这个叫“老庙煤矿”的地方。
这里的山水没有我家乡的美,四周虽有丘陵和高山,但望山跑死马,我们没去过。
近处有两座黑色的山,比不上我家乡的四顶山,四顶山四季绿色,各种花不分季节比着赛地开,这两座黑山寸草不生,只是黑着脸,仿佛谁欠它钱没还似的。
这两座山一座叫煤山,一座叫矸石山。
煤山不高,每天在长,也每天都在消瘦,长的是矿井里向煤山吐出的煤,消的是运煤汽车把煤运去城里什么地方去了,听说去炼钢,后来才知道,老庙煤矿的煤炭燃点低,只适合给水泥厂和民用。矸石没人要,那时没人去开发它,就任凭它天天地向空中长去。圆锥形的矸石山,好像一座巨大的坟茔。
矿山其他地方也是黑乎乎的,如果刮大风,煤山和矸石山上的浮煤四处飞扬。一天下来,人总会满鼻子满眼都是黑煤,当然,头发里和耳朵眼也塞满了煤灰,辫子自然也会结死结。我让妈帮我剃个平头,男孩子的那种,妈不同意,姐也不同意。如果我剃了平头,姐的编辫子技能就无处发挥了,她每天都会把妈给我编好的辫子打散,重新梳好,然后扎出不同样式的辫子,每天不同样儿。有一次她在我头上辫了十二根细辫子,说这是“古兰丹姆”新疆辫,还说下次给我买个新疆小花帽戴上,我就是电影里的小古兰丹姆了。
谁是古兰丹姆我不知道,只知道见到我的阿姨叔叔们都说我漂亮,像一部电影里的什么人,我很受用,从此不提剃平头的事了。那天,她还带我到卷扬房、压风机房给那里的女工阿姨看,把我当成她的精湛的工艺品展示。妈美美地笑,大娘也笑,不过她不忘怼姐:“看,看把你能得不行……”
这里也没有家乡的大湖,听说翻过大乌木山有一条叫长江的大江。近处只有小山塘,看着这些小山塘,我心里想,小澡盆的水池不够我游的。
当然,我最不喜欢的是在这里少有玩伴,仅有七八个没有上学的矿区孩子,还欺生!一次他们和我玩斗鸡,那群孩子没有一个斗过我的,于是他们就不按规矩出招,把我推倒在地。接着他们四哄而散,站在远处唱着自编的童谣:“一吆喊,二吆喊,没爹的孩子吃饭没有勺,没爹的孩子拉屎不用纸……”
我躺在地上,不愿起来,呆呆地望着蓝天和白云。我看见一群鸟排成人字形向南飞去,一只落单的鸟在歪歪斜斜地追赶,刹时觉得脸上如蚯蚓般缓缓地爬出两行热泪,不知是为那只鸟还是为自己,我伤心地大哭一场。半晌,爬起身来,向煤山和向矸石山爬去。
我每天只能去妈妈的矿灯房“上班”。到这里“上班”也要注意躲着区长和矿领导,他们说矿灯房是矿山的“安全重地”,不允许有小孩到这里。有一次,大娘就怼那个结巴区长说:“你一号井也没有幼儿院,孩子小,放哪儿?你说说,俺看赶明儿送你家去合适得很,这可中?”
结巴区长涨红脸,抖着嘴唇半天才开口:“随……随……你的……便。”
姐在一旁笑着把矿灯递了过去:“大区长快下井去,人行车的电铃都在催你了。”
结巴区长夺过矿灯,头也不回地走了。
身后是大娘和姐的爽朗笑声,妈只是低头吃吃地笑着,见大人们高兴,我就骑着竹马从灯房嗒嗒地冲出来跑到门前小广场。
我喜欢矿灯房里的矿灯架充电的声音,二十四小时都发出“嗡嗡嗡”的响声,仿佛那里住了几千只蜜蜂。其实,那些矿灯还真是有光的蜜蜂,在井下,它们被矿工顶在头上飞。
到矿灯房,我可以看到白脸叔叔和黑脸叔叔们,白脸叔叔都是要下井的,而黑脸叔叔却是刚上井的。
有时我会走到副井边,望着白脸叔叔坐上人行车向井下滑去,看到黑脸叔叔被人行车驮上来,深井好像是个染筒,人白的放下去,回来就是黑的,如老家染坊染蓝锭布一样,神奇得很。老庙的深井是斜井,我长大后才知道,在淮南淮北煤矿还有竖井,竖井上下井是坐吊罐,斜井的上下井乘的是人行车。人行车三四节,一节大概能坐二十人,人坐好后,放人行车的叔叔发个信号给卷扬室。卷场女工就开动卷扬,把人行车的人和物放下井去。那斜井巷顶上有一路向下的航灯,灯一路向下渐次变小变淡。我知道白脸叔叔到那最深处去“演戏”去了,演的一定是包公戏,一个个变成了大黑脸。
我第一次看到黑脸叔叔们一起走过来,如看到一群黑金刚,漆黑的脸上只有眼仁是白的。他们咧嘴向我笑,露出白森森的牙,在黑脸映衬下,一个个甚似要吃小孩的怪兽。我吓得扑在大娘的怀里哭了起来,只有大娘宽厚的胸怀才能保护我,那时弱小的妈是不行的。也就是那天我闻到大娘怀里有一种特殊香味,那种香好像我在哪里闻到过,但一时又想不起来。
“你们快滚蛋,吓着孩子了。”大娘骂着那些故意吓我的黑脸叔叔们。大娘骂完,他们还是围着我不走,还用黑手指摸我的脸。大娘说我:“翠儿,别怕别怕,你爹过去也是这样的。”
这时,黑脸叔叔中有位高个子叔叔走过来说:“别逗孩子了,她是赛张飞张老大的娃。”他这一说,众人慢慢收了笑容,沉默着向澡堂走去,留给我的是一队黑松树似的背影。
“赛张飞”就是我爸在矿工上的名字,他的大名叫张友田。后来我知道矿工们都有自己的别号,比如刚帮我解围的黑脸叔叔叫山豹王。
在矿灯房待久了,我就不再怕黑脸的叔叔了,还跟他们熟悉起来,山豹王、海佬吴、窑神杜都成了我的朋友。
山豹王不太喜欢说话,只是喜欢和姐聊天。姐忙着发灯没时间和他聊,他领完矿灯喜欢到矿灯房的山墙边晒太阳,眯着眼睛望着忙碌的姐。他坐在矿灯盒上抽烟,总不忘要拿一根烟给大娘。大娘接过来夹在耳朵上,要不就放在桌子的抽屉里,她不忙着抽。
山豹王见我怯怯地站在妈的身后探着脸望他,就朝我招招手。妈把我推了一下,算是鼓励。我大着胆子走向那个有一双豹眼的男人。他一把将我搂在怀里,用生硬的胡子扎我的脸,用他熊掌一样的大手,在我的腋下挠痒痒,我被他逗得哈哈大笑起来。他又把我高高扔向空中,或在将落地时接住我,或把我扔给窑神杜,窑神杜接过来,又把我抛给海佬吴。我仿佛是他们这群汉子的球,被抛在空中传来传去,我在空中有了一种久违的飞翔感,仿佛回到爸爸第一次把我举起的时光。
妈妈、大娘和姐起初害怕我会被他们失手摔坏了,但见到我哈哈大笑,大娘就制止了妈的大呼和姐的小叫,任由我们“疯”去。
从此,我交了这些和爸一样大的大朋友。他们各有吸引我的地方,其他人我暂不说,只说山豹王吧。他有一柄精致的小刀子,说它精致,是因为它翡翠绿的刀柄上镶嵌着两颗红宝石,刀子十分锋利。他总是把它别在腰带上,下井也带着,好像井下有野兽等他去捕似的。他叫小刀子为“小攮子”,他会用小攮子在煤精石上刻出个生龙活现的小动物来。他曾送我一个煤精石刻的豹子头,那只豹眼凸出,豹嘴大张,豹牙森立,似乎能听到它怒吼。我拿给姐看,姐说:“山豹就是手巧,你让他给姐也雕个。”我很喜欢这个豹头,把它放在床头边,半夜醒来看到它,我就不怕黑夜的黑了。
我让山豹王再雕一个,我说这是姐让你雕的。山豹王问:“她真的说让我雕?”我点点头:“骗你是小狗。”山豹王伸出小拇指和我的小拇指玩了个“打钩”游戏,他咧咧嘴笑笑,又问:“那她要雕个啥?”雕什么姐没告诉我,我抬头望望不远的玉兰树,想着姐喜欢花,就说:“雕朵玉兰花给姐吧。”山豹王抬头也打量下玉兰树说:“这花好雕,只是……”说这话时脸上露出了为难的表情。我说:“你不会不雕了吧?反悔了?我去告诉姐去……。”
“别,别,一定雕,不过我得先找到煤精石。”山豹王拉着我胳膊急着说,后来他告诉我煤精石可遇不可求,有人在井下干了一辈子也没见过它,“煤精石是黑色的软玉,黑色的金子,成精了一样,不好找。”其他的块煤一下刀子就裂开了。当然我认为他是骗我,许多年后才知道他说的是真话。
为什么要雕玉兰花?因为玉兰花被大娘和姐说得神奇,说它春天里没长叶儿,就先开了花,花期还很长,洁白洁白的。还有不长叶就开花的树,这个世界真是千奇百怪。
我曾问姐:“你见过玉兰花吗?”姐侧过脸来答道:“我们毕业时去南京春游曾看到过,真的很美。”
“它长什么样子?”我问。
“就是那样子……”姐一下不知怎么比画玉兰花形状,跺着脚说。
“到底什么样子?”我追问。
“就,就,就那样子嘛?急死我了……”姐还是比划不出来,鼻尖又冒汗了。她鼻尖常常冒汗,一是急了,二是她肚子疼。
“你不会拿个东西比划一下不就行了吗?看你活人还叫尿憋死。”一旁的大娘看到姐急躁的样子说了她一句。
姐被大娘这话点醒,环视一下左右,快步走到矿灯架边上,取下一个矿灯拧下灯头,卸下白亮亮的灯盏,竖立着给我看,大声说:“就,就这样,就这样子的。”
见我睁着大眼睛望着灯盏,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用手拍拍起伏的心口说:“我的亲娘呀,差点被你这个小丫头片子问住了。”
其实,我还是不知道她说的灯盏和玉兰花有什么直接联系,只是她连她的娘都搬出来了,也算是尽力了。听大娘和我妈私下说,姐三岁就没娘了,她娘跟一个来矿里采购煤的老板跑了,扔下她和她下井当矿工的爹。
姐人前从不说娘,正如我人前不说爸一样,心中都有一个结痂的伤口,揭不得。
如果玉兰花就是这灯盏的样子,那它的香味又是怎样香呢?是大娘怀里那种香吗?还是姐姐包里的小铁盒里百雀羚的香?要不然就是妈香皂的香了。
在神思遐想里,我望着窗外的玉兰树,它还没有矿灯头粗,还要等上三年才能长大开花。三年有多长?正如矿井有多深一样让我发蒙,不过三年后,我该九岁了,到那时爸爸一定离我会越来越远了,想到这,我反而不想让玉兰树长大开花。
三
姐喜欢在灯房里养花,她种有十多盒花。为什么不是盆而是盒呢?是的,我没说错,姐的花都养在废旧的矿灯盒里。
开始她的花总是养不活,姐很是懊恼,对着盒里枯了的花斥道:“不知好歹的,给你施肥给你浇水,给你晒太阳喝露水,把你当成爹伺候,你还是死了,没良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