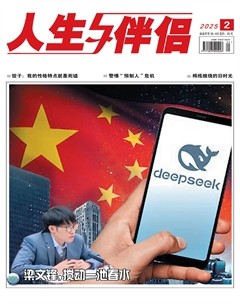漫画家朱德庸很少使用电子设备,2024年11月,他来大陆做新书宣传时,被媒体的阵仗吓了一跳。“几乎所有采访都要求视频化。访谈的过程中,灯光和机器对着我,我没办法像过去那样,喝着茶、跷着腿,瘫在沙发上与人聊天,从一开始似乎就已经变成表演了。”
稍感欣喜的是,他见到了许多读者。在出版商眼里,这是图书市场中的受众。“其实没有人知道市场在哪里,大家永远都是瞎摸索,瞎猫碰到了死老鼠,火爆之后就会有人想要复制,可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他知道,在自己面前的,是一群“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抽象的概念与数据。
返程时,朱德庸略显疲惫。在“以玩的心态度过了几天”后,他再次回归更习惯的生活之中。他不应酬,不交际,几乎不出现在公共场合,只是每天窝在家里,和太太与猫相处,想创作时画上一会儿,感到疲累就出门散散步。几十年如一日,比起抛头露面,他更爱“偏安一隅”。
听闻这次采访会以文字的形式呈现,朱德庸说自己很开心。在电话的那头,我也能明显感到,他的语气松弛而和缓。我们从他的新书《一个人的人生未爆弹》开始讲起,聊了聊他眼中的爱情、童年往事以及这些年累积下来的情绪。
他很明白,时代终究是变了,人们关注的那些事物也是如此。交谈时,他常会提到一个关键词“大背景”。他说自己始终徘徊在“大背景”的边缘——以局外人的视角来观察,似乎更容易发掘某些恒常存在的命题。
“爱情就像鬼,人人都谈论它,却从来没人真正见过”
25岁那年,朱德庸画出成名作《双响炮》。年轻的他并不能完全厘清动机,在彼时的他眼中,那不过是一次专栏约稿,一份正常的工作而已。如今,他业已成熟,突然有一刻,他明白过来,他想要做的是“把中国人婚姻的那一床棉被掀起来,让所有人看看棉被之下,到底在发生什么”。
从幼时起,他见过“无数人的婚姻状态,父母的、亲戚的、邻居的……他们都拥有婚姻,却用最荒谬的方式来呈现婚姻”。这是朱德庸所不解的,他没有花费太多时间,一股脑儿地画完了一幅幅作品。
《双响炮》迅速走红。这位尚未被更多人知晓的作者,被大家想象成一个老人。人们不禁好奇:“究竟是什么样的老头儿,受尽了婚姻之苦,才能把这些画出来呢?”朱德庸鲜少接受媒体采访,他只是躲在画的背后,继续观察着社会里的爱情新动向。
在《双响炮》走红六年后,《涩女郎》问世了。据朱德庸回忆,那是台湾地区女性主义高涨之时,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他发现,“人们只是把它当成时髦、先锋的事情,她们懂得要解开枷锁,可发觉钥匙不对,或者解锁方式不匹配,真正想形成成熟的观念,距离还非常遥远”。
他画了四位女性——“结婚狂”“万人迷”“女强人”“天真妹 ”,从名字上就已经反映出每个人不同的个性。朱德庸借她们的生活,表达了对工作与爱情的种种思考,但外界对此仍有误读,认为作者一定是个深谙恋爱之道的情场老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