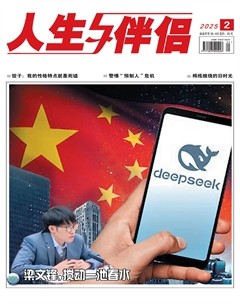出走
我的上一份全职工作,还是在北京做媒体记者。当时,我二十六岁,头脑一热,就辞了工作。
回头去看我当时的决定,与其说是不想上班了,其实是没法继续生活在北京。
1989年末生的我,按部就班地在三线小城读书升学。本科读了新闻学,大四在北京实习,之后便留在首都做媒体记者,一路算是顺风顺水。公允地说,我的工作对我来说相当友好:弹性工作制,不需要坐班—这很适合我的个性。我是自主性很强的人,跟坐班相比,居家办公时我的效率更高。
但工作不是生活的全部。从三线城市初到北京,我经过大城市带来的愉悦。但当新鲜感消失,我陷入迷失。北京的庞大与拥挤让我不堪重负,我感到渺小而孤独,不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
我清楚地记得,有天傍晚我骑着奶油色的单速自行车经过下班高峰期的三里屯,小心翼翼地在占满自行车道的汽车缝隙间穿行,突然一下子失去平衡,摔倒在一辆汽车的挡风玻璃上。正在我试图弄明白发生了什么、有没有受伤时,面前出现一位气势汹汹的五六十岁女人,她对我破口大骂,怪我摔在他们宝贵的汽车上。兴许是还没从摔倒了的震惊中缓过来,我一言不发地踏上自行车,更加小心地顺着缝隙往家移动。到了家,坐在写字桌前,我才感到愤怒不已。女人言行中的鄙夷和歧视让我觉得又怕又恨。我理性地提醒自己不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但我无法阻止溢满全身的一种“我不属于这里”的感觉。我既不认同她的行为处事和背后的价值观,也无力改变这一庞大的社会现状。决定在拥堵的北京骑自行车出行不过是我微不足道的反抗,经过这件事后变得很不愉快,我害怕重演那一幕。
雪上加霜的是,十多年前的北京正值空气污染最严重的时期,爆表的PM2.5值和空气污染指数经常登上新闻头条。这给我带来的精神压力和焦虑无需多言,我的身体也开始出现各种不致命但很恼人的问题,譬如身上出小红点,医生说是湿疹,但做了各种检查却找不出原因,开的药也不管用。
在逃离城市环境的驱动下,机缘巧合,我接触到攀岩运动,立刻就爱上攀岩的方方面面。
2014年,攀岩运动还不像今天这么流行,北京也只有几家小岩馆,跟今天干净、漂亮的现代化岩馆没得比。攀岩的人群,也主要以野外攀岩人为主。
当时,我最期待的便是周六早上六点背着户外大包骑车去亮马桥,到跟面包车师傅约定的地点与攀岩朋友汇合,一起包车去白河攀岩。从北京到白河,不堵车的话大概两个小时。到了攀岩的地方,从车里钻出来,伸展一下四肢,深深吸一口山里的新鲜空气,我感觉又活过来了。这里没有城市里熙熙攘攘的车流和人流,只有鸟雀、绿树、蓝天和岩壁,我感觉跟回家了一样自在。在荒野里,我感到更舒服放松。
我们一般在白河的农家院“德来之家”住一晚,周日爬一天后再回城。我很喜欢周日早上跟攀岩朋友们一起慢悠悠地准备早餐,用爱乐压煮咖啡,聊天说笑,这给我一种久违的社群和归属感。
攀岩运动本身也让我多年来第一次体会到心流状态。在岩壁上,我完全专注于每一个动作,彻底忘记了周围的环境和时间,百分之百地生活在此地和此刻。
攀岩的人总想爬新的岩壁,就像吃货总想尝试新的餐厅。我内心里打破既有轨道、尝试新事物的冲动破土而出:我向往去见识世界各地的攀岩地,探索自己在攀岩上的潜力。在职业上,我也感觉需要变化。工作以来,我一直有很强的“冒名顶替综合征”,对自己所写的东西感到心虚。一方面我感觉自己不如同侪有天分,也不比别人更努力;另一方面,我觉得自己一直是他人生活的旁观者,我渴望以第一人称去经历这个世界。我当时的工作是报道中国兴起的科技行业,我撰写那些实现巨大商业成功的产品和公司的故事,采访创造了产品的人和团队,但自己则既不懂商业,也不懂技术。我更想写写自己在场、亲身经历的东西。
现在回头去看,我不过是想行使那个年龄段年轻人的使命罢了——去探索和尝试。有些人在大学毕业后给自己一段限定的时间去探索,我的成长环境从未提供这一选项。
从小到大,读大学一直是大人给我定的目标,似乎读了大学、顺利找到大城市的工作后,人生就会幸福美满。我走完按部就班的那一条线性路径后,发现摆在面前的路不过是我所在这条路的延续——它下面的站点是存钱买房、结婚、生孩子。我对这个看得见的未来感到恐惧,渴望那些隐藏在黑暗中的未知路线。那时候,“万能青年旅店”乐队的一句歌词经常在我的脑子里回放: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那时我未必理解这句歌词的本来含义,但我能清晰地看到自己,如果顺着这条路往下走,会在某个时候崩塌的结局。
那一年春节,我第一次没回安徽老家过年,而去了云南石鼓攀岩,接着又去大理跟一个攀岩朋友碰面。我因此接触到一些住在大理的人,他们的自在和悠闲让我大开眼界,也让我看到了离开北京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