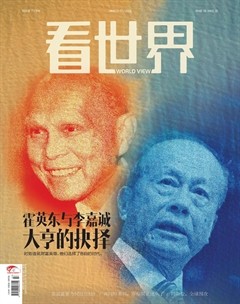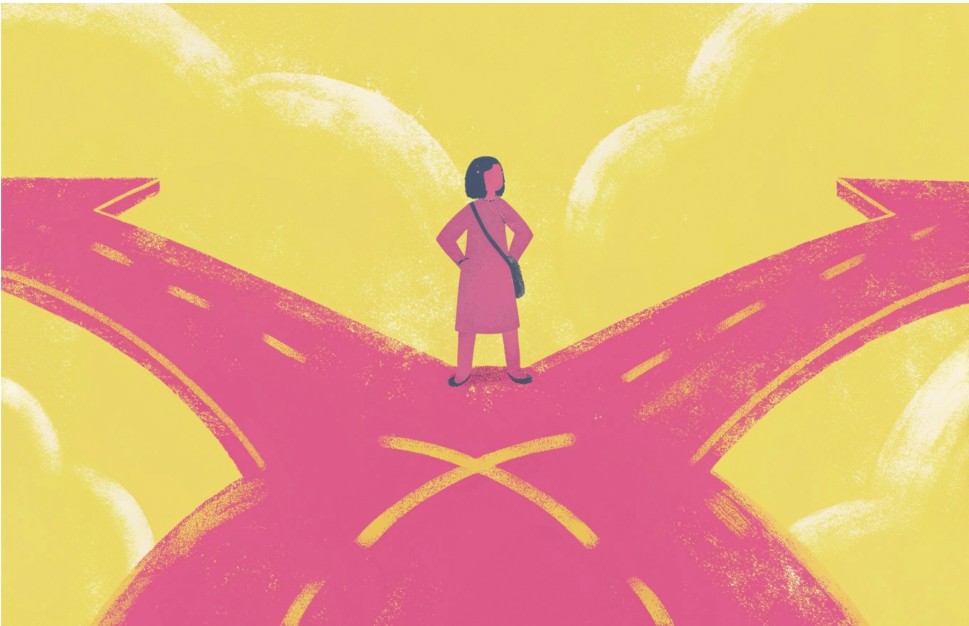
去年底,柚子决定给自己找点自由的“体力活儿”。
她主动到社区群里发“自荐”,并如愿做了一天收纳工,还认识了一个保洁阿姨,商量以后一起接活儿。这一份零工,让柚子在一点点收拾房间的过程中,有了与过去的脑力工作不一样的获得感。
类似的现象,正在更多年轻人身上蔓延。
上学、毕业、找工作,似乎是每个人生活必经的轨道。而当轨道出错,生活陷入动荡的循环,刚刚踏入职场的年轻人要如何选择?
“临时工”“零工”,这些属于“70后”“80后”的名词,在今天有了新的化身—“灵活就业”。不止是单纯地贩卖劳动力,当代年轻人,在信息时代,持续寻找着属于自己的新“零工”。
近日,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和智联招聘联合发布了《2024中国新型灵活就业报告》,报告提到,新型灵活就业的供需规模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份额呈扩大趋势。而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中国灵活就业人员就已经达到2亿人左右。
统计数字背后,年轻人在多种“零工”里探索属于自己的道路。有人因为无法接受低时薪,最终回到公司全职上班;有人学会了以前从未接触过的技能,也因此找回在职场被挫败的信心;还有人同时打着多份零工,遵循“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原则……
而不论未来如何选择,他们真正在寻找的,是一个复杂问题的答案:对于自己来说,工作到底意味着什么?
离开轨道的年轻人们
2017年,再次辞职的砂砂选择了离开一线城市,回到自己的老家—山西省的一个小县城。
这个选择背后是她在工作中积攒的痛苦。砂砂本科就读于中文系,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文案。2015年,她在一家互联网公司撰写各种测评稿件。工作不久,刚上班的热情劲儿过了,她开始经常性地拖延。领导要求每周五交稿,砂砂总是拖到周日的凌晨,然后熬一个通宵把稿子赶完。
“其实最后写出来是什么东西,我都没有印象了。”她熬过两三次通宵,感觉自己的脑子像浆糊,很难受。拖延状态也让砂砂陷入焦虑,后来,她每天早晨都起不了床,下班后一走出公司,就开始哭。
类似的焦虑、拖延与崩溃,也延续到她的第二份工作中。工作中的困难和压力时常让她情绪不稳,最后一次崩溃是因为失恋,第二天上班,她迟到了很久,“别人都找不着我”。在此之后,她不得已提出了辞职。
小一也经历了反复辞职。2019年毕业至今,她已经换过5份工作,其中工作时间最长的也不到一年,最短则只有两三个月。
她原本有一条看似通畅的轨道。在小一父亲的规划中,她大学要选择经济学专业,将来就可以去做会计工作。那时的小一还很懵懂,也没有太多的自主性,没怎么思考,就按照父亲的设想填了志愿。
这条路走得并不顺利。做电商客服,她常常发错货,即使为此赔了不少钱也没有改变。做审计工作时,她会反复检查很多次,仍然会犯很多低级错误。她也常常在工作中分心,白天的工作拖到晚上11点、12点才开始。到了深夜,如果遇上不懂的问题,小一不好意思去麻烦同事,拖延与焦虑叠加,她一边工作,一边扯自己的头发。
转行并不容易。既定轨道上的人要脱离轨道,找到新的方向,需要经历诸多波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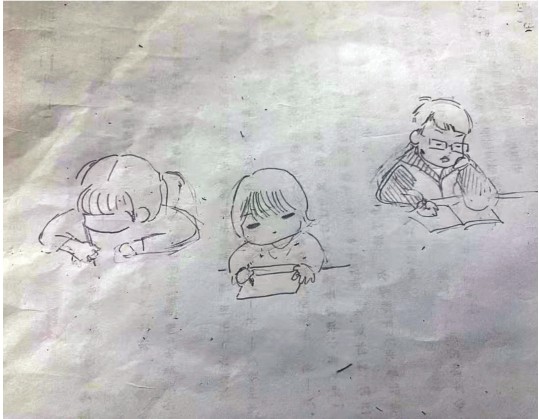
小一曾尝试去找工作不顺的原因。因为从小就粗心大意,也常常走神,她怀疑自己是ADH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